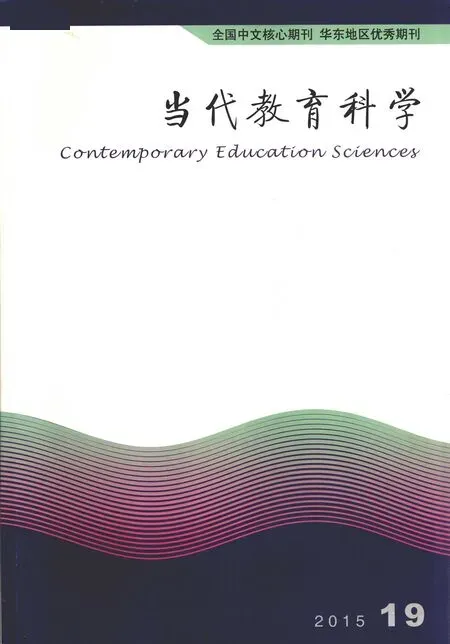大學排名與高校教學地位之殤**基金項目: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學會研究課題“大數據時代研究生教學質量監測機制研究”(項目編號:C-2015Y0414-011)、江蘇大學第十四批大學生科研立項項目“江蘇省高校教學質量評價監控機制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
●萬 姝 王佳佳
大學排名與高校教學地位之殤**基金項目: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學會研究課題“大數據時代研究生教學質量監測機制研究”(項目編號:C-2015Y0414-011)、江蘇大學第十四批大學生科研立項項目“江蘇省高校教學質量評價監控機制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
●萬姝王佳佳
摘要:備受追捧的大學排名使本已式微的高校教學變得更加弱勢。大學排名在資源分配上的重要導向以及教學指標在大學排名體系中的邊緣化,使得高校教學很難受到應有的重視。這種現象的出現源于大學排名的組織者對大學功能的理解存在偏頗、高校教學難以量化評價的特性,更源于利益相關者對大學排名的盲目熱捧。為了改變大學排名對高校教學造成的負面影響,需要轉變大學排名理念,通過引進第三方評價平臺提升教學在大學排名指標中的權重,促進高校教學回歸本真。
關鍵詞:大學排名;高校教學;弱勢地位
萬姝/江蘇大學教師教育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高等教育學
王佳佳/江蘇大學教師教育學院副教授,教育學博士,研究方向為教育哲學、教師教育
自1983年《美國新聞與世紀報道》發布了第一個大學排名之后,大學排名活動在高等教育領域迅速升溫并得到了蓬勃發展。目前已有超過45個國家有國內大學排名,同時出現了11個世界大學排名,且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長。大學排名活動在“引導學生擇校、促進大學競爭、引導教育投資流向、吸引社會公眾關注高等教育”[1]等方面起到了重要影響,已經成為我國高等教育評估領域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引起了政府部門、高校、用人單位、學生及家長等利益相關者的高度關注。大學排名對高等教育資源分配、高校生源和聲譽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教學作為高等教育領域人才培養的具體體現和關鍵環節,本應在大學排名中占據重要地位。然而,當前的大學排名卻過分偏重于高校科研成果尤其是論文發表數量的評價,對教學這一原本應占據重要評價指標的體現卻遠遠不夠。高校教學評價在大學排名體系中被邊緣化,難以受到應有的重視,使得本已式微的高校教學地位變得更加弱勢。
一、大學排名與邊緣化的高校教學
隨著大學排名的不斷發展,世界各國出現了數量眾多且類型多樣的大學排名體系,動態地反映出了各個大學的發展規律和發展潛力。按照排名組織者的不同,可以將大學排名體系主要分為三類:一是以政府機構主導的大學排名活動,例如中國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進行的高等教育學科評估、德國“高等教育發展中心”(Centre for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CHE)發布的“CHE大學排名”等;二是以新聞媒體為主的民間機構組織的大學排名活動,如美國《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發布的“美國最好的大學”排行榜、加拿大《麥克林》發布的“加拿大大學排名評價”以及由英國高等教育咨詢機構QS與其他排名機構合作共同發布的“QS世界大學排名”等;三是由高校專家學者等個人及團隊參與研制而發布的大學排名,包括上海交通大學劉念才等發布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ARWU)、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武書連等人所在的大學評價課題組發布的“中國大學評價”(即武書連排行榜)等。
不同類型的大學排名體系的評價理念各有側重,在不同的方面發揮著重要影響:以政府主導的排名能夠為政府提供高校在科研實力等方面的直接參考數據,從而根據大學在排名中的表現與名次,有選擇地給予不同程度的教育資源分配;以新聞媒體為主導的大學排名作用在于為公眾提供高校關于大學聲譽、科研實力、資源配置等方面詳實而豐富的信息,從而幫助公眾了解高校實際情況和綜合實力。但整體而言,大學排名的影響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大學排名對高校教育資源分配具有引導作用。排名靠前的大學能夠獲得數量可觀和質量上乘的教育資源,包括師資力量、招生比例、碩博士點批準、重點學科批準以及撥款等。社會團體和個人也更容易受大學排名因素的影響,向排名靠前的大學提供更多的民間教育資金。其次,大學排名影響高校的生源質量和生源數量。國內高考考生和家長在進行擇校時十分看重大學排名提供的有關信息,參照大學排名對不同高校進行定位,并更傾向于選擇名次靠前的高校就讀。[2]同時,大學排名對國際招生市場尤其是對法律、醫學、商科等特定學科招生具有重要影響,[3]排名靠前的高校更容易帶來申請人數的增加。[4]這就導致質量優異的高考考生和國際學生更容易流入排名靠前的高校,對高校生源質量和數量的構成產生影響。再者,大學排名對高校聲譽產生影響。良好的大學聲譽作為大學重要的無形資產,是大學在高等教育領域獨一無二的優質資源。大學排名的先后直接影響學校的社會聲譽和社會形象,排名靠前的大學更容易獲得社會公眾的認可。
大學排名成了影響生源質量和高校聲譽的重要因素,成了決定高校物質、資金、學術等方面資源分配多寡的“天平”。而與此同時,大學管理者對大學排名的理解產生了偏差,急功近利地希望取得成績,以高校在大學排名中的名次彰顯高校的綜合實力,導致了大學管理者對大學排名的過度追逐。部分大學的管理者將學校發展的決策過程和戰略規劃與大學排名指標直接掛鉤,以推動大學排名作為高校發展的重要目標。例如,美國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校長將該校的發展戰略明確定位為“使該校成為世界前三名研究型大學之一”;[5]日本的東北大學(Tohoku University)也宣布計劃在未來十年進入“世界前30名一流研究型大學行列”。[6]同時,高校管理者根據大學排名指標體系的權重決定大學在教學、科研及社會服務等方面的資源分配和先后發展順序。當前許多高校如河北工業大學、中南大學等[7]根據現有大學排名指標著力提升科學研究的資金分配,通過重獎SCI論文發表的教師等方式提升論文指標數量。這種有方向、有方法的竭盡全力改變大學排名中某一項或某幾項指標,最終提升當年學校在大學排名中的名次,這已經成為當前許多高校的通行做法。[8]大學排名對教育資源分配的導向作用應體現出大學在教學、科研、管理、社會服務等各方面的功能。然而,當前的大學排名卻普遍存在著重科研、輕教學,重數字評價、輕質量評價等現象:
一是從設計理念上看,當前的大學排名體系分布中科研排名多,教學排名少。大學排名體系中包含了多個僅針對高校科學研究方面進行的排名,但卻少對高校教學質量單方面進行的排名。例如,上海交大世界大學學術排名以及臺灣高等教育評價中心(HEEACT)的世界大學科研論文排名等均以科研成果和學術產出作為排名指標。同時,即使是以高校綜合實力進行的大學排名也更傾向于考核高校科學研究方面的成果,而忽略對高校教學質量方面的考核。例如,“QS世界大學排名”以及“中國大學評價”等一系列大學排名旨在評價高校的綜合實力和整體發展水平,但在實際排名過程中更傾向于對高校科研成果及學術產出等方面的評價。
二是從指標權重上看,當前的大學排名指標體系過分偏重對高校科研的評價,高校教學處于邊緣化地位,并未占據大學排名指標體系的重要權重。例如,由中國教育部開展的“高等教育學科評估”指標體系中,衡量“科學研究”的評價指標包括了“代表性學術論文質量、代表性科研項目情況”等7個二級指標,而用于衡量“教學”的評價指標僅為“教學與教材質量”1個二級指標。[9]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副刊)發表的“THE世界大學排名”的評價指標中通過“研究”和“論文引用”兩個一級指標評價科學研究的情況,權重高達62.5%;反之,“教學”這個一級指標的權重僅占30%。[10]2013年網大“中國大學排行榜”指標體系中,對科研成果的評價包括了“學術資源”和“學術成果”兩個一級指標,其權重總和占42%,但其評價指標體系中缺乏對高校“教學”方面的評價。
三是從評價方式上看,當前大學排名體系在有限的教學指標分配上,更重視對人才培養方面進行數字評價,而忽略對高校實際教學質量的評價。多數大學排名在有限的教學指標分配中,僅以“生師比、高級職稱教師的比例、學生的考試成績、畢業率”[11]等數字指標衡量高校人才培養的情況,缺乏對高校教育教學過程中的實際教學質量及教學情況進行評價。例如,由武書連團隊發布的“中國大學評價排行榜”指標體系中,通過“本科碩博士畢業生數、本科生就業率、新生錄取分數線、全校生師比、本科研究生教學成果獎”[12]等二級指標對高校人才培養情況進行評價;“QS世界大學排名”的指標體系則通過“生師比”、“企業雇主評價”兩個一級指標來評價大學的人才培養情況。這些大學排名的指標體系僅停留在對高校人才培養的數字化評價,并沒有從高校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效果等方面評價高校的實際教學情況和教學質量。
二、高校教學緣何在大學排名中“失落”
(一)排名組織者對大學功能理解偏頗
教學作為高等教育領域人才培養的具體體現和關鍵環節,本應在高校發展和大學排名指標體系中占據首要地位。但受歷史傳統和現實功利主義的影響,排名組織者對大學功能的理解產生偏頗,普遍認為大學功能的重中之重在于科學研究,[13]忽視了教學作為大學最本質的使命。大學排名的組織者之所以對大學功能理解產生偏頗,一是源于世界一流大學特征的影響。現如今的世界著名大學大多是研究型大學,其一流大學的聲譽往往是源于其強大的科研實力,包括碩士博士點、重點實驗室的數量、課題項目申報情況、獲得國際重要獎項人數等方面。[14]當科研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核心指標”[15]時,自然受到排名組織者的厚愛并將其作為大學排名的評價理念和方法邏輯,以科研繁榮作為大學繁榮的重要標志。二是排名組織者看中科研活動為高校帶來的經濟效益。高校科研地位的高低和科研成果的多寡決定了其獲得政府專項撥款和社會資助的走向。[16]當大學排名的組織者看中科研成果為高校帶來的經濟效益時,由他們所設計出的大學排名指標體系自然更加偏重對科研成果的量化考評,導致其評價指標體系出現了“重科研、輕教學”的現象。三是源于利益相關者對教學的看法和態度影響排名組織者對大學功能的理解與判斷。以教學活動為代表的人才培養職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因為其效率低、回報慢等無法引起政府職能部門、大學管理者、社會公眾等群體的重視,從而影響排名組織者對于大學功能的理解和判斷。
(二)高校教學難以進行量化評價
大學排名多以量化指標對高校教學、科研、管理、服務等方面進行評價,使原本模糊不清或不易比較的高校基本因素以簡潔的數字方式呈現出來。然而教學本身的特點決定了其很難以大學排名的量化指標進行評價。一是源于教學活動是一個連續性的過程。“大學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復雜系統,其教學質量的好壞是長期發展、積累的結果,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17]教學作為一個連續性的過程,無法在短時間內表現出明顯的變化,也很難采用具體的可操作方法進行評價。二是源于教學行為的特殊性導致其很難用量化方法進行評價。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由教師個人和學生群體共同構建的教學行為和教學風格等很難進行統一測量,不同教師之間甚至同一教師在不同時期的教學活動也難以進行量化比較。[18]而科研產出作為數量指標,很容易通過教師發表的論文、承擔的科研項目獲得相關數據,從統計意義上明確界定并加以量化考評。由于教學活動及教學成果本身所具有的連續性和特殊性等特點,導致很多大學排名體系只能在各項辦學硬件資源或成果獎項等指標數值之間進行比較,無法體現出大學在教學方面長期的積累和傳承。[19]排名組織者需要考慮到大學排名活動的操作性和便利性,在對大學教學評價尚未找到簡單明了且易于量化的科學操作方式、無法獲得客觀的數據支持教學質量的比較之前,他們僅能從教學能夠量化的部分,如“生師比”、“企業雇主評價”等方面進行比較籠統的評價,而非是對教師教學水平、教學方式、教學效果等高校實際教學質量,以及對于教風、學風、教師的工作態度與情感投入、學生對于教師教學質量的滿意度等教學因素做出科學、客觀、準確的教學評價。
(三)利益相關者對大學排名的盲目熱捧
大學排名的初衷在于通過其科學的評價指標和評價方式診斷大學在教學、科研、管理、服務等方面存在的優勢、問題與不足,以此作為高校不斷改進辦學質量和辦學水平的“方向標”與“參考系”。然而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大學排名卻備受高校管理者等利益相關者的盲目熱捧,導致大學的發展完全以大學排名指標為導向,偏離了原先的發展軌道。政府部門將大學排名作為評價現有高校質量的一條捷徑,從而根據大學在排名中的表現與名次,對不同類型和層次的大學區別對待,有選擇地給予不同程度的教育資源分配。高校管理者則瞄準大學排名這一資源分配的“指揮棒”,根據大學排名指標權重決定高校在教學、科研以及社會服務等方面的資金投入和先后發展順序,在學校建設和各項政策的制定上以大學排名指標體系作為決定因素,[20]以期迅速提高高校在大學排名中的名次。這種盲目地對大學排名熱捧不僅使大學發展呈現“高效性、可計量性、可預測性和可控制性”[21]等特點,還導致大學排名“扭曲大學的辦學行為、左右大學的辦學水平”[22]等現象的出現。利益相關者對大學排名的盲目熱捧,以提升大學排名作為高校的戰略目標和發展規劃,根據大學排名指標體系決定高校科研、教學、服務等活動的先后發展順序,使大學陷入追逐以科研發展為目標的單一大學模式的惡性競爭中,迫使大學“喪失了真正的學術文化,忘記了大學最本質的教學使命”。[23]
三、大學排名中高校教學地位的扭轉與出路
(一)轉變大學排名理念,正確定位排名功能
排名組織者對于大學理念及其承擔職能的理解影響了大學排名的理念設計和指標構成。為了扭轉這一局面,排名組織者需要轉變大學排名理念,明確高校發展的職能定位。“大學理念是大學發展的內部邏輯,代表著大學的品位和精神,反映了大學的理想、追求、信念,體現著大學組織的共同價值。”[24]高校承擔了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等職能,其中人才培養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職能。排名組織者在對大學排名評價體系與評價指標進行設計和制定時,需始終明確將高校教學質量作為大學最根本的使命,堅持以大學的核心學術標準和大學的學術使命作為大學排名指標體系構建的重要因素。同時,排名組織者應根據我國大學發展的實際情況,考慮高校教學與科研的發展現狀,適當提升對高校教學質量的評價,以改變大學排名指標體系中“重科研、輕教學”的權重分布。
對于政府部門和高校管理者而言,應辯證地看待大學排名的結果。高校管理者在面對大學排名時,應理性對待大學排名中數字之間的差別,將大學排名結果作為認識、了解大學信息的渠道之一,防止出現對大學排名結果的過度追逐。同時,高校管理者需要關注大學排名在教學、科研、社會服務等方面多元化評價功能,根據大學排名中詳細而豐富的指標體系獲得直接的參考數據,幫助高校管理者和大學學術人直觀面對教學在高校發展中的弱勢地位,從而制定相應措施提升教學地位,提高教學質量。
(二)構建第三方評價機制,提升教學指標權重
為改變以往大學排名中“重科研、輕教學”的指標權重分布,解決大學排名中高校教學質量難以進行量化評價的問題,可以采用美國等國家實行的大學排名方式,構建具有客觀公正性和專業權威性的第三方教學評價機制,為大學排名提供教學評價指標的數據支持。通過構建第三方教學評價機制,一是平衡大學排名中教學與科研指標體系的權重。以第三方教學評價機制中的評價結果作為大學排名中高校教學質量評價指標的數據支撐,適當提升高校教學質量在大學排名指標體系中的權重,從而促進大學排名由“重視科研評價”向“重視教學評價”轉移,引導高校管理者關注高校教學活動,改變教學資源分配比例,實現高校教學的優先發展。二是實現大學排名中教學質量的量化評比。通過構建第三方教學評價機制,以科學、客觀、量化的高校教學評價方式,對高校教學內容、教學方式、教學效果等教學情況以及高校教風、學風、學生滿意度等教學因素進行評價。排名組織者通過引進第三方教學評價機制中對高校教學質量量化評比數據,關注高校教學過程中的實際教學質量及教學情況,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以往大學排名中僅以“生師比、學生成績、畢業/就業率”[25]等數字指標衡量高校人才培養的情況。例如,以美國“評師網”(ratemyprofessor.com)為代表的第三方教學評價機制以細化評價指標、量化教學排名等方式對高校教學質量進行評價。[26]美國“福布斯大學排行榜”通過引用“評師網”的教學質量評價結果做為大學排名中教學評價指標的數據支持,[27]從而提升大學排名中教學評價指標權重、實現高校教學質量的量化評價。
(三)尊重教學特性規律,回歸高校教學本真
教學活動的延續性和教學行為的特殊性使得高校教學無法在短時間內表現出明顯的變化。這就要求我們根據教學的特點,在尊重教學特性與規律的情況下對教學質量進行評價,從理念更新、資源分配、制度設計、教學獎勵等不同方面促進高校教學的發展,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高校管理者和建設者需要始終將教學工作視作高校工作的生命線,改變高校教學資源和資金分配方式,加大對高校教學方面的資源投入。例如,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和其他獨立基金會投入大量資源支持本科教育和教學專業發展;[28]美國俄亥俄州、田納西州等州將大學公共資源投入到教學和學習上,以期提高高校教學地位。二是高校需加快改進教師評價方式,建立多元化教師評價體系。高校在進行教師聘用、職稱評定、獎金發放等需力圖平衡教學與科研地位,建立以教學、科研、人才培養、社會服務等評價指標的多元化教師評價體系;三是建立穩定可行的教學獎勵和薪金補助制度,著力提升高校教學地位。高校可仿照國內外先進經驗,通過設立“首席教師崗位”或“優秀教學獎”等獎項,定期評選教學成果突出或具有貢獻的教師等方式,從而建立高校教學獎勵和薪金補助制度,[29]以資金獎勵和名譽獎勵等方式吸引教師關注高校教學、著力提升高校教學地位。當高校始終將教學作為其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活動,在尊重教學特性的前提下對教學質量進行評價,教學才能穩固在高校發展中的中心地位,創造重視教學的學術氛圍,讓高校回歸教學本真。
大學排名作為推動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力量,旨在動態地反映大學的發展規律和發展潛力,從而引領高校的全面發展。然而,當前的大學排名更多的是發揮了對高校科學研究這一單方面的推動作用,忽視了對高校教學、管理、社會服務等方面的促進作用。我們應始終堅持以大學的核心學術標準和大學的學術使命作為大學排名理念與指標體系構建的重要因素,通過大學排名中科學的評價指標診斷出高校在教學、科研、行政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優勢、問題及不足,以期為高校管理者提供改進高校綜合實力、推動高校整體提升的參考意見和策略,從而實現大學排名引領高校全面發展的本真價值。
參考文獻:
[1]董秀華.對我國大學排行實踐的回顧與思考[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2,(4).
[2]樂國林,張麗.大學排名對高校影響的社會學分析——基于布迪厄場域、資本理論的探析[J].現代教育科學,2005,(3).
[3]張旺.大學排名對高等院校的影響[J].高教發展與評估,2012,(1).
[4]Marguerite Clarke. The Impact of Higher Education Rankings on Student Access,Choice,and Opportunity [J].Higher Education in Europe,2007,(32).
[5]University of Minnesota. Advancing the public good: transforming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into a world-class research university[EB/OL].www.academic.umn.edu/provost/reports/dec2007update.pdf.
[6]A.Inoue. Plan 2007-Rap Map to Becoming a World Class university[EB/OL].http://www.bureau.tohoku.ac.jp/president/open/plan/ Inoue_Plan.pdf.
[7]李文兵.我國大學排名研究綜述[J].高教發展與評估,2007,(4).
[8][17]林曉青.大學排名方法的局限與改進[J].教育研究,2009,(11).
[9]教育部學位中心.2012學科評估結果[EB/OL].http://www. cdgdc.edu.cn/xwyyjsjyxx/xxsbdxz/277134.shtml.
[10]THE.THE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EB/OL].http://www. timeshighereducation.co.uk/world-university-rankings/.
[11][25]李文兵.大學排名的合理性訴求及其困境[J].江蘇高教,2009,(6).
[12]武書連等.2010中國大學評價[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4, (4).
[13][22]王英杰.大學排行——問題與對策[J].比較教育研究,2008,(10).
[14]高艷.從世界大學排名看一流大學建設[J].中國電力教育,2014, (35).
[15]宣小紅等.大學排行評價指標體系的比較研究[J].教育研究,2007,(12).
[16]羅燕.大學排名:一種高等教育市場指引制度的構建——新制度主義社會學的分析[J].江蘇高教,2006,(2).
[18][21][23]代蕊華.高校的教學、科研及其評價[J].高等教育研究,2000,(1).
[19]騰珺,屈廖健.反思高等教育排名重塑世界學術格局重塑世界學術格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高等教育排名與問責:善用與濫用》述評[J].比較教育研究,2014,(7).
[20]劉堯.大學排名機構也需規范引導[N].中國教育報,2014-04-01(2).
[24]孫華.大學之范:理念與制度[J].現代大學教育,2015,(2).
[26]Davison E.,Price J.. How do we rate? An evaluation of online student evaluations [J].Assessment &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2009,(1).
[27]Wikipedia.RateMyProfessors.com[EB/OL]. http://en.wikipedia. org/wiki/Rate_my_prof.
[28]Fairweather J..Beyond the Rhetoric: Trends in the Relative Value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Faculty Salaries [J].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2005,(4).
[29]吳洪富.大學教學與科研關系的歷史演化[J].高教探索,2012,(5).
(責任編輯:馮永剛)
- 當代教育科學的其它文章
- 中美高校服務學習的比較與啟示**基金項目:山東省高等學校學生教育與管理研究項目“服務學習——高職院校學生教育管理創新實踐研究(項目編號:2013B009)的研究成果之一。
- 我國臺灣地區海洋教育體系建設及對大陸地區的啟示**基金項目:青島市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項目“藍色規劃背景下青島市中小學海洋教育研究”(項目編號:QDSKL1401026)的研究成果之一。
- 公共教育服務的供求矛盾及其調節措施**基金項目:肇慶市社科規劃“促進肇慶市公共服務產業發展對策研究”(項目編號:14ZC04)的研究成果之一。
-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研究
- 立足學校的課程整合研究**基金項目:山東省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課題“省級教師教育基地教師教育模式創新研究”;濱州學院重大課題“普通本科院校職前教師培養模式研究”。
- 翻轉課堂的“翻”與“不翻”:基于文化視角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