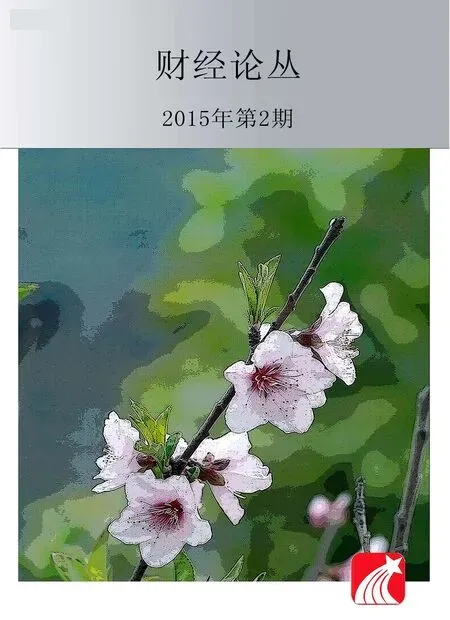法律環境差異與區域保險不平衡——基于我國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研究
初立蘋,劉兵勇
(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上海 200433)
一、引 言
同其他金融服務業一樣,保險業不僅從數量上已成為金融機構全面發展的重要部分,而且在質量上因風險與不確定性的增多已變得更加重要(Outreville,1990)[1]。我國保險業從1979年恢復經營以來,保費收入年均增長超過20%,成為國民經濟中發展最快的行業之一。2012年全國保費收入1.55萬億元,全球排名第四,然而保險深度和保險密度相對較低,同年我國保險深度約為3.0%,不到世界平均水平6.5%的二分之一,保險密度約為179美元,僅為世界平均水平656美元的四分之一,與發達國家相距甚遠。我國雖然已經是保險大國,但還不是保險強國。而且保險業在高速增長的同時,也面臨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造成地區間保險發展不平衡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實現地區間協調發展?這些問題一直是我國保險業關注的焦點。
關于保險業發展區域差異的影響因素,經濟發展水平無疑是重中之重,已成為保險經濟學界的共識(徐為山、吳堅雋,2006)[2]。此外,陸秋君、施錫銓(2008)[3]認為人口素質、年齡結構、居民金融資產、社會保險水平等的不同也會導致區域保險差異。誠然,這一影響因素是多方面的,正如欒存存(2004)[4]將影響保險業的增長因素分為三大類:一是社會文化結構和法律法規等因素;二是保險的替代因素,如社會保障等;三是經濟發展狀況等因素。由于第一類因素大都難以量化,已有研究主要是從后兩類因素展開。
然而,保險業是對外部政策比較敏感的行業,極易受國家司法制度的影響,法律層面詮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已成為許多實證研究的焦點(Esho等,2004)[5],而且保險包含著風險的合法轉移,保險合同的價值取決于法律規則及實施、裁定解決沖突的效率及立法過程的穩定性和完整性(Ward、Zurbruegg,2000)[6]。近年來,很多學者開始研究制度因素,尤其是法律制度對保險發展的影響,而且多數文獻認為,法律制度的國際差異有力地解析了國家之間保險發展水平的差異,但是少有文獻從這一視角研究一個國家內部的不同地區間的保險發展差異。正如李春燕(2013)[7]所指出的,我國保險業發展的非均衡在一定時期內因區域保險發展環境的差異必然存在,因此,本文試圖從法律環境角度解析我國地區間保險發展不平衡,以彌補這一領域的空缺。
本文主要貢獻在于:(1)本文是國內首次從法律環境視角量化其對地區保險發展不平衡的影響,豐富了已有關于保險發展不平衡的研究,也進一步完善了“法律與金融”這一領域的研究;(2)由于非壽險業和壽險業對經濟的作用機制有所不同,本文將其分開進行研究,有助于解析法律環境對不同保險業的影響;(3)考慮到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將法律環境對非壽險和壽險發展的影響與經濟發展水平聯系起來;(4)本文選用三階段最小二乘法(Three-Stage Least Square,3SLS)處理內生性問題,對經濟學領域中普遍存在的內生性問題提供了可供參考的有效解決途徑,也保證了得出的結論更加可靠、更有說服力。
二、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
我國保險業發展迅速,已經成為區域經濟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推動力,但是保險業發展的區域差異卻較為明顯(陸秋君、施錫銓,2008)[3],而且區域保險消費的不均衡發展已經成為制約我國保險業更好地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之一,應當引起足夠的重視(趙進文等,2010)[8]。許多學者認為,經濟發展水平是引起區域保險發展差異的最重要因素。保險發展是否會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趨同而趨同?這個問題既是保險產業理論研究的基本問題,也是監管當局制定區域發展政策的重要依據,更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
關于這一問題,主要存在兩種觀點。一種是比較樂觀的,如吳祥佑(2009)[9]研究表明區域保險業發展水平會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趨同而趨同;另一種觀點則表示悲觀,如肖志光(2007)[10]認為區域保險市場發展水平不會由于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趨同而必然出現趨同,因為各地區保險市場環境存在差異,它是導致我國區域保險市場發展水平差異的主要因素之一。倘若如此,表明同一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之間保險發展水平也可能存在較大差異。
我國保險業的發展過程中,制度特別是法律制度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La Porta等(2008)[11]指出,法律制度決定了法律規則和監管準則的設定。法律制度會對經濟發展水平以及金融市場的發達程度產生影響,其中包括對保險業發展的影響。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健全的法律制度是維護和推進交易的唯一必要條件。法律制度通過提供合約的執行機制使得勞動分工和交易得以進行(張維迎,2001)[12]。保險合同是整個保險業務的起點,維系著保險業務雙方當事人的權責義,而且其附合合同屬性(孫積祿,2007)[13]雖然節省了訂約成本,但其負面效應也是顯而易見的。因而保險業在發展中需要良好的法律環境來矯正因保險合同屬性所引致的負面效應。
關于法律環境對保險業發展的影響,已引起不少學者的關注。Syverud等(1993)[14]指出美國的法律體系是促進其保險業發展的重要因素;Beck和Webb(2003)[15]采用68個國家在40年間的面板數據進行研究,發現法律起源很好地解釋了壽險消費差異。然而,法律環境對保險發展的影響在同一國家的不同區域有無差異?這一問題少有提及。而且由于地方保護及市場分割造成的“諸侯經濟”(沈立人、戴園晨,1990)[16]使得我國地區間呈現出類似于“跨國研究”設計框架的背景,以各個地方為研究對象探析法律環境與保險發展之間的關系,將更有實際價值。
我國各省的法律環境存在很大差異,主要表現在:(1)同一法律在各地的實施效果和執行效力會因各地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而有所不同;(2)各省的地方性法規及相應部門頒發的規范性決議、決定、命令等在內容和形式、數量和質量方面存在較大差異;(3)因經濟發展水平會影響法制健全程度,而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差異較大,進一步加大了地區間法律環境的差異。而且,Beenstock等(1986)[17]指出,隨著收入水平的提升,人們對壽險的消費需求也會增加,但增加幅度在國家之間差別很大。這表明在我國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各地保險需求應存在一定差異。
經濟發展水平既影響保險需求,也影響法律體系的建設;同時,法律環境也會對保險業的發展產生影響。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地區,法律環境對保險業發展的影響會有差異,且法律環境這一杠桿效應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會有所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非壽險業和壽險業也存在較大差異,主要原因在于非壽險的主要功能是風險轉移和賠償,具有短期性,非壽險消費著重通過其分散風險的經濟補償功能影響經濟增長(趙進文等,2010)[8];而壽險主要履行金融中介職能,具有長期性(Ward和Zurbruegg,2000)[6],壽險消費更多地作為強制儲蓄的手段實現收入在時間和空間的再分配,通過資金融通功能拉動經濟增長。非壽險與壽險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不同,經濟發展對它們的影響也可能不同,甚至會影響法律環境的杠桿效應。
本文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經濟發展水平相同的區域,法律環境完善的地區保險發展顯著好于法律環境不完善的地區。
假設2:法律環境對保險發展的影響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不同,即與較低經濟發展水平相比,較高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之間的保險發展差異受法律環境的影響會降低;這一效應在非壽險業和壽險業之間存在差異,呈現不同的關系。
三、數據來源與研究模型
(一)數據來源
本文基于1999-2011①由于市場化指數的數據僅到2011年,為了保持數據的一致性和可比性,本文選擇將2011年作為數據結點。年的中國省際面板數據進行研究,選用保險密度②保險密度(保費收入/人口數)是在保費收入的基礎增加對人口因素的分析,考慮了人均水平,能夠比較真實地反映各地保險市場發展的實際水平。以保險密度來度量保險發展水平,原因如下:(1)該指標為絕對數指標,與本文所選用的解釋變量的量綱保持一致;(2)保險密度未考慮經濟因素,而保險深度(保費收入/GDP)在保險密度的基礎上已增加了對經濟因素的考慮,因此保險深度不適用于分析經濟發展水平對保險發展的影響。來衡量保險發展水平。考慮到非壽險業和壽險業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機制不同,將保險密度進一步分為非壽險密度和壽險密度,這部分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保險年鑒》。法律環境③法律環境主要是法律意識形態及與之相適應的法律規范、法律制度、法律組織機構、法律設施所形成的有機整體。本文選用樊綱和王小魯等(2011)[18]的市場化指數中的“市場中介組織的發育和法律制度環境”這一指標量化地區的法律環境,主要是由于該指數包含律師、會計師等市場組織服務條件、行業協會對企業幫助程度等內容,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當地的法律環境。、金融業競爭、消費者保護數據來自樊綱和王小魯等(2011)[18]所著的《中國市場化指數》。其他數據,如經濟發展水平、社會保障水平、城鎮化水平、金融發展水平、兒童負擔系數、老人負擔系數等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中國人口年鑒》。
(二)研究模型
為了檢驗假設1,需要驗證法律環境是否確實影響保險發展水平,以保險密度來度量保險發展水平,將待檢驗的模型設定為:

其中,Nondensityit表示不同地區不同年度的非壽險密度,Lifedensityit表示不同地區不同年度的壽險密度。Legal為法律環境指數,選用市場化指數中的“市場中介組織的發育和法律制度環境”指標作為代理變量,該指數越大,表示法律環境越好,是正向指標。Income為經濟發展水平,用人均可支配收入來量化,為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均值。
Xit由一系列控制變量組成,因非壽險和壽險的影響因素不同,模型(1)和(2)中的具體變量有所差異。具體的,根據已往的文獻,模型(1)考慮五個主要影響非壽險密度的因素,包括金融發展水平(Finance),用當地存款數額占當地GDP的比重表示;金融業競爭(Competition),衡量保險業競爭,作為保險價格的代理變量;消費者權益保護(Consumer),衡量對消費者權益的維護程度,用以度量保險產品與其他產品之間的消費替代關系;教育水平(Education),指接受大專以上教育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社會保障水平(Welfare),指人均社會保障支出;城鎮化水平(Urban),為城鎮化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
類似地,模型(2)中選用的控制變量,除了金融發展水平、金融業競爭、消費者保護、教育水平和社會保障水平外,還包括兒童負擔系數(Children),為受撫養的兒童占處于工齡階段的人口比重;老人負擔系數(Older),為受撫養的老人占處于工齡階段的人口比重。
對于面板數據回歸分析,我們首先根據Hausman檢驗和Breusch-Pagan檢驗來判別是固定效應(Fixed Effect,FE)還是隨機效應(Random Effect,RE),如果無法取舍,則同時使用這兩種效應模型;其次,為使結論更加可靠,我們也選用可行廣義線性模型(Feasible General Least Square,FGLS)對參數進行估計。
進一步地,為了檢驗假設2,需要對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分類,衡量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下法律環境對保險發展的影響,為此,我們將待檢驗的模型設定為:

其中,Category表示經濟發達程度,是以經濟發展水平Income來劃分的。具體來看,如果經濟發展水平較低,該變量取1;處于中等水平,則為2;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則為3。其他變量的含義同上文保持一致,這里不再贅述。
此外,內生性是一個重要問題。關于保險業發展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一方面,經濟增長是影響保險需求的主要因素,這一點已經達成共識(徐為山、吳堅雋,2006)[2],當然其他因素也會影響到保險業的發展水平。另一方面,許多文獻探討了保險業增長是否促進經濟增長的問題,大部分學者的答案是肯定的,如Ward和Zurbruegg(2000)[6]。為控制潛在的內生性,建立聯立方程組,設定如下:

為得到聯立方程組的參數估計,我們使用三階段最小二乘法(3SLS)。一般來說,相比兩階段最小二乘法,三階段最小二乘法多一次修正誤差,比二階段的估計更加精確。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法律環境與保險密度的檢驗結果
為了測度法律環境對保險密度的影響,基于模型(1)和(2),分別采用固定效應模型(FE)、隨機效應模型(RE)和可行廣義線性模型(FGLS)回歸分析,結果見表1。
表1顯示,無論是非壽險業還是壽險業,法律環境Legal的系數始終顯著為正。具體來看,對于非壽險業,在FE和RE回歸中,Legal的系數均為11.065,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這說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法律環境每提高一個單位,非壽險密度平均將增加11.065元;在FGLS中,該回歸系數為7.911,同樣在1%的水平下顯著。類似地,對于壽險業,法律環境的回歸系數在FE和RE中為35.633,而在FGLS中為29.697,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這也說明法律環境對壽險發展存在著顯著的正效應。為此,在表1的回歸中控制了經濟發展水平后,法律環境Legal對保險密度存在著顯著的正效應,支持假設1。
關于控制變量,金融業競爭Competition,在非壽險密度回歸中顯著為負,說明激烈的競爭可能導致惡性競爭,擾亂原有的市場秩序;但在壽險業中是正效應,歸根于壽險業的長期性,競爭程度的提升,不斷滿足投保人的需求,促進了壽險消費的發展。消費者權益保護Consumer,始終顯著為負,這可能導致其他方面的消費與保險的消費之間存在替代關系。教育水平Education的回歸系數基本上顯著為正,表明隨著教育水平的提升,人們對風險管理及長期儲蓄的理解有所增強,逐步重視保險的作用,進而帶動保險需求,這與Beck和Webb(2003)[15]一致。社會保障水平Welfare,對非壽險業的影響顯著為正,這主要是由于隨著社會保障水平的提升,民眾的生活更有保障,有額外的資金購買非壽險產品;而對壽險的影響為負,這歸咎于社會保障與商業壽險之間有著明顯的替代關系,這與Browne和Kim(1993)[19]一致。兒童負擔系數Children,僅在FGLS模型顯著為負,其他并不顯著,而老人負擔系數Older恰恰相反,且是顯著為正,這與Beck和Webb(2003)[15]基本一致。其他控制變量不顯著,不再贅述。

表1 法律環境與保險密度的回歸結果
(二)經濟發展、法律環境與保險密度的檢驗結果
我們檢測法律環境對保險密度的影響是否因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而不同,回歸結果見表2。不難看出,Legal的回歸系數依然顯著為正,與上文結論保持一致,Income亦是如此。為了測度因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而影響法律環境與保險密度的關系,同時考慮簡便性,引入了Legal與Category的交互項。我們發現:(1)對于非壽險業,Legal*(Category=2)的回歸系數是-3.435,且在10%的水平下顯著,說明與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相比,經濟發展中等水平的地區其法律環境每提升一個單位,非壽險密度下降3.435元。進一步發現,Legal*(Category=3)的回歸系數是-7.169,說明與較低經濟發展水平相比,在較高經濟發展水平下,法律環境對非壽險密度的影響顯著下降,而且對經濟發展處于中等和較高情況下的回歸系數-3.435、-7.169進行差異測試,得出二者之間的差異在1%的水平下顯著,這進一步表明,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法律環境對非壽險密度的影響顯著下降,但依然是正效應。(2)對于壽險業,法律環境對壽險密度的影響不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始終為49.530,說明法律環境顯著地影響壽險密度的變化,即在控制其他因素后,法律環境每提升一個單位,壽險密度增加49.530元。

表2 經濟發展、法律環境與保險密度的回歸結果① 限于篇幅,表2和表3只匯報主要變量的回歸結果,其他控制變量不再列示。
(三)內生性檢驗
經濟發展水平與保險密度之間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本文選用三階段最小二乘法進行檢驗,結果見表3。
(Ⅰ)和(Ⅱ)是模型(5)和模型(6)的回歸結果,用來處理非壽險業和經濟發展之間的內生性問題。依據表3,對于非壽險密度而言,Legal的系數顯著為正,與表1和表2的結果一致,支持了假設1,而Legal*(Category=2)和Legal*(Category=3)的回歸系數分別為-5.514和-4.727,且分別在1%和10%的水平下顯著,進一步檢測這兩個回歸系數之間的差異,發現兩者差異不顯著,這與表2中的結果有所不同。由于表3是經過內生性處理后的結果,更加可靠,本文傾向于選擇表3的結果。我們認為,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法律環境對非壽險業的影響有所下降,經濟發展水平與法律環境對非壽險密度的影響基本呈“L”型關系。同時在(Ⅱ)中,Nondensity的系數顯著為正,這也說明兩者高度相關,處理內生性極其必要,這與趙進文等(2010)[8]的結論一致,我國非壽險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正向拉動作用已非常明顯。

表3 內生性檢驗的結果
(Ⅲ)和(Ⅳ)是模型(7)和模型(8)的回歸結果。同樣,Legal的回歸系數依然顯著為正,且Legal*(Category=2)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這表明與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相比,經濟發展水平中等的地區其法律環境對壽險密度的影響顯著下降;而Legal*(Category=3)的回歸系數不顯著,表明法律環境對壽險密度的影響在經濟發展水平處于較低和較高階段之間無差異。不難發現,經濟發展水平與法律環境對壽險密度的影響呈現“U”型關系。同時在(Ⅳ)中,Lifedensity的系數不顯著,這與徐為山、吳堅雋(2006)[2]保持一致,壽險業到底能否促進一國的經濟發展還沒有定論,而Legal的系數是顯著為正的,說明法律環境的完善有助于經濟發展,這在一定程度上與La Porta等(2008)[11]的研究吻合。
綜上所述,對于非壽險業,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法律環境對非壽險密度的影響有所下降;對于壽險業,這一影響取決于經濟發展的具體階段,基本上支持假設2。
五、結論及建議
基于我國區域保險發展不平衡的現狀,以1999-2011年我國31個省(或直轄市)為樣本,探究法律環境是否顯著影響非壽險和壽險發展。基于上文的實證結果,得出如下結論:第一,法律環境對非壽險密度和壽險密度均有顯著的正效應。第二,經濟發展水平與法律環境對壽險的影響呈“U”型關系,對非壽險密度的影響呈“L”型關系。第三,采用三階段最小二乘法(3SLS)對聯立方程組進行回歸分析,得到的結論與上述基本一致,即法律環境會影響保險業發展。
針對我國目前的區域保險發展不平衡問題,提出如下建議:第一,不斷完善保險相關法律制度,為當地的保險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和制度保障;第二,各級各地政府應想方設法地拉動經濟增長,為保險業的發展提供財力上的保證與支持;第三,加大宣傳力度,提高民眾的保險意識,不斷開發保險業沃土,使保險業更好地發揮經濟“助推器”和“穩定器”功能。
[1]Outreville J.F.The economic significance of insurance marke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1990,57(3):487-498.
[2]徐為山,吳堅雋.經濟增長對保險需求的引致效應[J].財經研究,2006,(2):127-137.
[3]陸秋君,施錫銓.中國保險需求區域差異研究[J].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08,(4):15-19.
[4]欒存存.我國保險業增長分析[J].經濟研究,2004,(1):25-32.
[5]Esho N.,Kirievsky A.,Ward D.,Zurbruegg R.Law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property-casualty insurance[J].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2004,71(2):265-283.
[6]Ward D.and Zurbruegg R.Does insurance promote economic growth?Evidence from OECD countries[J].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2000,67(4):489-506.
[7]李春燕.我國保險發展的空間非均衡及極化研究[J].財經論叢,2013,(2):64-70.
[8]趙進文,邢天才,熊磊.我國保險消費的經濟增長效應[J].經濟研究,2010,(增刊):39-50.
[9]吳祥佑.我國保險密度空間收斂的實證研究[J].財經研究,2009,(9):111-120.
[10]肖志光.論我國保險市場區域均衡發展[J].金融研究,2007,(6):181-191.
[11]La Porta,R.,Lopez-de-Silanes,F.,Shleifer A.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legal origins[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forthcoming,2008,46(2):285-332.
[12]張維迎.法律制度的信譽基礎[J].經濟研究,2002,(1):3-13.
[13]孫積祿.保險合同法律性質分析[J].比較法研究,2007,(2):135-142.
[14]Syverud K.D.,Bovbjerg R.R.,Pottier S.W.,Witt R.C.On the demand for liability insurance:comments[J].Texas Law Review,1993,(72):1629-1702.
[15]Beck T.and Webb I.Economic,demographic,and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life insurance consumption across countries[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2003,17(1):51-88.
[16]沈立人,戴園晨.我國“諸侯經濟”的形成及其弊端和根源[J].經濟研究,1990,(3):12-19.
[17]Beenstock M.,Dickinson G.,Khajuria S..The determination of life premiums:an international cross-section analysis 1970-1981[J].Insurance: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1986,5(4):261-270.
[18]樊綱,王小魯,朱恒鵬.中國市場化指數[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1.
[19]Browne M.J.and Kim K.An international analysis of life insurance demand[J].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1993,(60):616-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