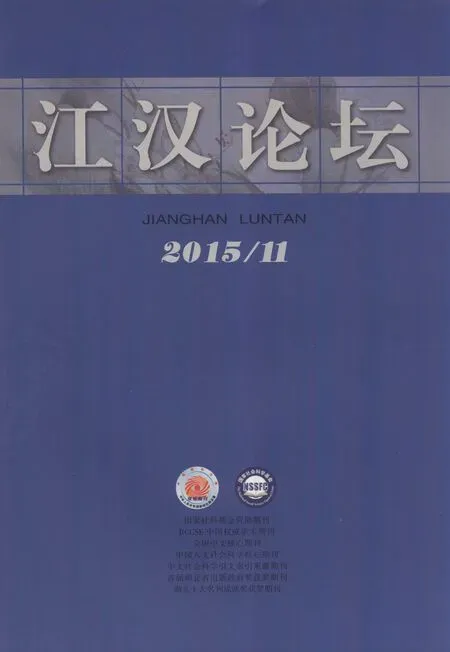試論朱子對儒家道統的禮學實踐
崔 濤 韓金燕
儒家道統論包括 “道”與 “統”兩個方面,“道”是就義理觀念層面來講的,而 “統”則是就道的傳承譜系而言的,它是儒家傳道統緒的 “歷史性”呈現,我們這里談朱子的 “道統”,主要指后者。朱子是宋代道統論的集大成者,學界對其道統論不乏討論,但目前這些研究多著眼于道統觀的形成、發展及爭論等歷史層面,未能將此問題置于朱子學本身特有的哲學視野中加以考量,難免忽略了朱子作為一位理學家對道統所持有的特殊態度。我們認為,朱子對道統持有一種強烈的實踐態度。這種實踐態度與觀念化、主觀化相對應,指向對一種歷史的真實性的踐履與論證,而這與朱子學特有的禮學實踐精神及其理氣論密切相關。
一、道統的禮學實踐問題及其學術背景
道統作為儒家對傳道譜系的認定,呈現為一個歷史性的人物序列,這個問題自韓愈首次提出道統說就已談及。那么,何謂道統的實踐問題呢?對應于 “道”作為理的存在, “統”作為歷史性的存在,本應該是實在的,但儒家的道統與佛教的法統不同,并不存在一個嚴謹的、歷史的師承次第,所以也就不具有現成的歷史真實性,其實在性往往取決于不同儒家對它的認可程度,并無一個客觀的衡量標準,由此也就決定了不同儒學對道統的不同主張。韓愈提出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的統緒 (《原道》, 《韓昌黎先生集》卷11),宋儒多無異議,但他們又多并不承認韓愈得了道統。伊川尊明道為道統正宗,朱子也認可二程為道統傳人,而陸象山卻不認可二程,也不認可朱子,只以自己為真正得道統者。宋代功利派儒家如陳亮、葉適等對道統則又有自己的看法。在如此眾說紛紜的情況下,儒家所謂道統其實嚴重缺乏實在性、統一性,反而呈現出相當的主觀化、觀念化特征。這在其他儒家未必是多么重要的問題,但在朱子則成為一個亟須解決的時代課題。
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朱子倡導道統論的時代,也恰是宋學空疏流弊日益明顯的時代,不但程朱一系空疏之風一直非常明顯,而且與朱子理學對應,又有陸象山心學的崛起,朱子一向認為陸學近佛,空疏不實。在這種情況下,朱子無法眼看著他極為重視的道統論日益陷于主觀爭議中,便強烈地希望借助禮學實踐來解決這一問題。為了更清晰地理解這一點,下面簡略分析一下朱子對宋學空疏流弊的批評。
儒學在宋代以理學、道學肇起,它以張揚本體論補足了傳統儒學在形上學上的缺憾,并使儒學在與佛學的對峙中得以復興,所以宋儒對形上的 “天理”、 “太極”等哲學范疇大多特別鐘愛,這也造成了宋儒為學喜好空談天理、心性的不良傾向。這種傾向在宋代理學中大致有兩種表現,一種是空談天理本體之高妙, “只講理而不講禮”;一種是“以為有理就自然能合于禮”①。它們在二程一系中都有表現。前者可以游酢、呂大臨為代表,游氏主張為學 “非必積日累月而后可至,一日反本復常,則萬物一體,無適而非仁者”,朱子批評其說 “陷于釋氏頓悟之說,以啟后學僥幸躐等之心”;呂大臨 “專以同體為言,而謂天下歸仁,為歸吾仁術之中”,朱子則抨之為 “不免過高而失圣人之旨”,“非有修為效驗之實” (《論語或問》卷12)。后者可以謝良佐、尹焞為代表,二者也都有 “以理易禮”的毛病。朱子評謝氏 “然必以理易禮,而又有循理而天、自然合禮之說焉,亦未免失之過高,而無可持循之實” (同上);而尹氏謂 “禮者,理也,去私欲則復天理。復天理者仁也” (《論孟精義》卷6),朱子則評其說 “然其以理易禮,而遂以復禮為仁” (《論語或問》卷12)。朱子認為游、呂、謝、尹諸說都終不免以 “天理”架空禮文之嫌。其實,空談心性是宋代學者的通病,朱子早年為學也曾 “務為籠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于小”②,后至同安為官,受李侗 “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 (《朱子語類》卷110)之教,方才轉變風氣。也正因朱子親身經歷了由高談妙道到著眼精微日用的轉變,他對當時理學中的這種不良風氣才看得更清楚。朱子早年學問空疏之弊大致比較近于前一種傾向,這一傾向極易流于與佛道為鄰,陸象山心學主張 “脫略文字,直趨本根”,從某種意義上講,也可以看作是宋代理學這種傾向的一個必然的邏輯發展,所以朱子終其一生抨擊陸學為禪學,以其學空疏無實③。
針對當時 “以理易禮”的時代流弊,朱子以“克己復禮為仁”作為儒家仁學的要義,認為 “克己”與 “復禮”相輔相成,不可偏廢,他說:“‘克己復禮’,不可將 ‘理’字來訓 ‘禮’字。克去己私,固即能復天理。……惟是克去己私了,到這里恰好著精細底工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見得禮,便事事有個自然底規矩準則。” (《朱子語類》卷41)作為下學工夫的 “禮”在他看來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它既是上達 “仁”的橋梁,也是檢驗 “克己”的 “規矩準則”。朱子說: “禮即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行跡之可言;制而為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④可見,他并不是一般地反對 “禮即理”的觀點,而是認為一旦取消了“禮”, “理”也必將落空。在這個辯證的層面上,朱子又有 “禮是體”的觀念,弟子問: “先生昔曰: ‘禮是體。’今乃曰: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似非體而是用。’”他回答說: “公江西有般鄉談,才見分段子,便說道是用,不是體。” (《朱子語類》卷6)朱子這里并不是將 “禮”等同于形上本體,但他認為體、用不可單以形上、形下分, “體是這個道理,用是他用處” (同上),所以對應 “人做處”這個 “用”, “禮”自然是“體”。朱子認為陸象山講 “體”太過空談, “江西人說個虛空底體,涉事物便喚做用”,而他則認為“合當做底便是體” (同上)。在他看來,沒有“禮”這個節文, “理”這個形上本體也會空無著落。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同樣作為宋代思想家,朱子具有更強烈的禮學實踐精神,他對觀念層面的“理”持有更嚴謹的禮學實踐態度、反對空談的作風。
由此反觀朱子的道統觀,依其明道務要踐禮之論,儒家道統又豈可流于議論爭執,成為主觀無實之說?統緒既不能明確,道統說亦何由成立?所以,朱子對于道統并不滿足于對傳道內涵的揭示,針對儒家道統實在性、統一性缺失問題,他不僅努力甄別道統譜系,更特別致力于對統緒的禮學實踐——他不僅從觀念上樹立起道統譜系的人物序列,而且以書院祭禮的形式將這個統緒予以確立,并賦以實在的宗教性體驗,使之得到社會現實層面的廣泛驗證與認可。朱子對于道統的認真程度在同時代鮮有能及,通常我們多從樹立道統正宗的角度去看待他在道統論上的鍥而不舍,但這種看法未免過于偏狹,因為除此之外,這個問題更與朱子的禮學實踐態度及其對當時儒學風氣的研判密切相關。在特別警惕宋學流于空疏的時代流弊,又非常注重“復禮”實踐的朱子看來,道統之爭已不是一個單純的觀念性問題,而是一個亟須從實踐層面去加以解決的工夫問題。
二、朱子對道統的禮學實踐
朱子對道統的禮學實踐是借助書院祭祀的形式完成的。如上文所談,朱子主張以 “復禮”的態度落實儒家道統的歷史真實性,所以,他對書院祭祀所持有的態度也與當時一般士大夫有所不同,他所設立的書院祭祀實際上承擔著對儒家道統禮學實踐的任務。當然,朱子在書院祭祀上的這種用心也經歷了一個過程。
在中國古代,學校是習禮的地方,而禮之重者莫過于祭祀,所以學校為彰顯師道,一直有祭祀活動, 《禮記·學記》: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漢代以后,因為儒學的興盛,學校祭祀又逐漸演變為以孔廟為主要場所,相沿成制,到唐代從國子學到地方府、州、縣學也都設有孔廟,而學校的官方性質則決定了這些祭祀活動都是由官方主持的。到宋代,這種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于官學衰微,民間書院大量興起。書院是民間性質的學校,受官方學校悠久的祭祀傳統的影響,大多從創始之時也設有祭祀活動,像宋初的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等都是如此。和早期官方學校祭祀類似,書院祭祀的對象也主要包括先圣、先師及先賢⑤。在宋代,一些理學家像周敦頤、二程、胡安國等,也逐漸成為官方學校及書院的祭祀對象,朱子對此非常重視,這從他留下的大量 “祠記”、 “堂記”不難看出⑥。不過朱子對祭祀理學人物的重視遠非一般意義上的尊重先賢,他對此懷著深厚的崇尚道統的宗教性情懷。
淳熙七年 (1180)朱子主持白鹿洞書院祭祀,祭祀對象尚只限于先圣、先師,但他的道統情懷經歷了十余年的孕育,至紹熙五年 (1194)竹林精舍(后稱滄州精舍)落成舉行祭祀時,終于演化成為一場以 “道統”為核心的禮學實踐活動。據載這次祭祀相當隆重,朱子本人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新書院告成,明日欲祀先圣先師,古有釋菜之禮,約而可行,遂檢 《五禮新儀》,……先生終日董役,夜歸即與諸生斟酌禮儀。雞鳴起,平明往書院,以廳事未備,就講堂禮。” (《朱子語類》卷90)此次祭祀在宋代書院祭祀中具有非常特殊的性質,因為雖然它表面上只是一次書院新成、祭祀先圣先師的活動,但從周敦頤、二程、邵雍、司馬光、張載、李侗這個從祀名單看,它顯然非同一般,有著朱子的特別用心。肖永明先生指出,從學術淵源上考察朱子對此次從祀名單的安排并不足以揭示竹林精舍祭祀的實質, “朱熹通過李侗、羅從彥、楊時而上接二程,屬程門的四傳弟子,但將周敦頤、二程、邵雍、張載、司馬光并祀于書院,所考慮的顯然并非這種學統上的繼承關系,而主要是……出于一種道統意識”⑦。這無疑是正確的。先前學校、書院祭祀理學人物,大多只是從一般從祀或紀念的角度考慮,并未特別與當時儒家內部的道統爭議相關聯,而朱子則以 “復禮”的實踐態度,從道統論的高度重新整飭了當時的一般書院祭祀活動。他在書院祭祀中這樣嚴肅地規正道統譜系,當然是為了確立儒家正統道脈所在,但同時這更是他基于儒家道統譜系實在性、統一性缺失的憂患意識而做出的禮學實踐行動。
這里必須指明的是,朱子通過書院祭祀來證實道統之緒這種創造性舉動與他對宋代士庶如何祭祖的長期思考是密切相關的。
宋代是一個儒學復興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傳統禮法制度進一步崩塌的時代。 “經過唐末五代的大動蕩,到宋代,士族和庶族間的界限在現實和人們的觀念中都基本消失”⑧。傳統的嚴格等級禮法對世俗現實喪失了實際的參考價值,但百姓在日用層面對禮之節文的需求卻仍然存在,這使當時民間參雜佛、道儀式的冠婚喪祭等俗禮得到迅速發展,對傳統禮法造成了巨大沖擊。這在理學家們是不能無視的,與儒學復興相呼應,在民間禮法的規范性方面,他們也由此展開了一場角逐。傳統禮法無法完全適應民俗需要,那么改革、創新就勢在必行。據吾妻重二先生 《朱熹 〈家禮〉實證研究》一書考證,朱子的 《家禮》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在繼承了前代諸如二程、司馬光等人的禮儀革新成果的基礎上,完成的一部士庶通用的儀禮書。他指出:“朱熹在構成 《家禮》冠婚喪祭的四禮當中,尤其對祭禮有著特別的關注。而朱熹搜集整理有關家族(宗族) ‘祭禮’的古今文獻,編纂 《古今家祭禮》,便是由于這個原因。”⑨《古今家祭禮》一書完成于淳熙元年 (1174),比朱子舉行竹林精舍祭祀早二十年,據此我們認為,朱子將道統與祭祀相結合以落實道統之緒的禮學實踐態度,應該是受了他長期思考士庶祭祖禮的深刻影響。這一點也可以從書院道統祠祀與家廟祭祀二者間的結構關聯中得以印證:

從這里不難看出,在家廟祭祖與書院祭先圣二者之間有著明顯的對應關系,祭祖的條件是有宗脈傳續,而祭祀先圣的條件則是有道統的傳承。所不同的主要在于前者傳續所依賴的是祖先之氣,也即血氣的延續,而后者傳承所依賴的則是圣賢之氣,也即精神的承續。如果說前者目的在于 “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 (《禮記·祭義》),以便在同一始祖、同一血脈的感召下,實現宗族的團結凝聚;那么后者則正如朱子所說, “禮先圣、先師于學宮,蓋將以明夫道之有統”⑩,因為在同一圣師、同一統緒的鼓舞下,同樣可以令后世學子對弘揚道統的使命有所領悟,從而實現群體認同的目的。這種對應性顯示出,朱子在思考如何通過書院祭祀實現對道統的禮學實踐時,對祭祖禮的長期關注成為其最直接的參考資源。如同祭祖禮不僅僅是祭祖,它要求宗脈正統的存續作為條件,道統祭祀也不僅僅是祭先圣先師,它還要求正宗統緒的傳承作為支撐?,所以朱子并不認為任何先賢都可以作為從祀對象,他說 “配享只當論傳道” (《朱子語類》卷90)就是這個意思。這樣道統正如宗脈,在祭祀中就被彰顯為一種猶如血緣的維系之脈,也要求一種純正性,可稱之為 “道脈”了?。這就不僅要求價值觀念繼承上的純粹性,同時也要求精神情感上更為深刻的關聯。朱子所以對于道統祭祀之禮異常的認真、考究,也正因為他 “認為釋奠儀式的準確無誤以及祭祀人員的恭謹嚴肅是能夠與祭祀對象進行精神溝通與交流的必要條件”?,這反映出他對于道統祭祀的強烈的宗教性情懷。這種彰顯 “道脈”的含義在竹林精舍祭祀之前的一般學校、書院祭祀中是沒有的,而由于這種缺失,在那些祭祀活動中,祭祀對象、從祀者與祭祀者之間顯然存在著某種斷裂感,是非常不完善的。朱子并沒有因為宗子對祭祖權的不容爭議而提示后世祭祀先圣先師也應該考慮權屬問題,但他的確在竹林精舍的道統祭祀中通過對道脈實在性、統一性的禮學踐履,聲明了程朱一系的正統性,這卻是毫無疑問的。
三、朱子對道統禮學實踐的理氣論闡釋
眾所周知,祭祀的對象是鬼神,那么,朱子參考儒家傳統的祭祖禮,通過書院祭祀來實踐他所確立的道統的可靠性,就必然要涉及到一個問題,他對祭祀鬼神的理氣論解釋,能否在合理解釋祭祖禮的同時,也滿足他在道統祭祀方面的創新?
朱子是以他的基本哲學觀念的 “理氣論”來說明祭祖問題的,他認為理、氣不可分, “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 (《朱子語類》卷1),但理與氣又不同,氣雖虛卻是實有的,而理只有形而上的意義,并無形質, “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不可以聚散言也” (《朱子語類》卷3)。這樣撇開性理問題,談到人的生死,就只是氣的聚散。他贊同 《易傳》的說法,認為 “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 (同上),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便是生死底道理” (同上)。那么,祭祀先祖如何可行呢?朱子說: “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然其氣雖已散,這個天地陰陽之理生生而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而子孫之精神魂魄自有些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里也。” (同上)他認為祭祖的可行性在于有 “感格”之理,雖然人死魂魄之氣即散去,但散去的陰陽之氣仍可以通過祭祀重新聚攏起來。
當然,朱子認為感格是有條件的:其一,被祭者需有子孫后人;其二,他以誠敬之禮來祭祀。二者缺一不可。首先就前者來講, “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禮記·大傳》),在祭祖禮中宗脈的延續起著根本的作用。朱子不止一次強調過這一點,如說: “但有子孫之氣在,則他便在。”(《朱子語類》卷3)又說: “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 (同上)血緣性的宗脈傳續是祭祖禮成立的基本前提,所以朱子說: “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個血脈貫通。所以 ‘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為這氣不相關。” (同上)祭祀鬼神需要祭祀者與被祭祀者之間存在相關性,以祭祖禮而言,這種相關性即 “血脈貫通”,也即血氣相應。其次就后者來說, “祭祀主敬” (《禮記·少儀》),誠敬本為祭祀的要義所在。朱子所以強調這一點涉及到時人對鬼神的態度。儒家一向有 “敬鬼神而遠之”的說法,朱子又以陰陽變化解釋魂魄問題,所以當時也有人對鬼神的有無頗為懷疑。如有人問朱子: “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真有氣來格也?”朱子說: “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云車擁從而來,又妄誕。” (《朱子語類》卷3)如此看,朱子認為孔子所謂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論語·八佾》)并非虛談,所以誠敬是必須的。只是他并不認為鬼神如一般世俗人所想象的那樣有形質可言。
在如上對祭祖禮的詮釋中,顯然第一點非常容易對朱子論證書院道統祭祀的合理性帶來障礙。這里至少有兩個問題需要解決:其一,祭祖的感通之理既在于血氣相應,而在書院祭祀中道統譜系的人物之間并無這種血氣的貫通性,祭祀感格又依據什么而成立?其二,祭祖的前提是被祭者有后世子孫在,這意味著一脈相承的宗脈的連續性,即便道統祭祀自有感格依據,其譜系人物并無代代相承的連續性可言,這又要如何解釋?這兩個問題都明顯指向道脈的實在于理氣論方面的可論證性,如果不解決難免令道統祭祀在理論上陷入被動。
針對前者,朱子在 “公共之氣”的預設下提出了 “氣類相應”、 “祭其所當祭”等觀點。祭祀如只論血氣相應,難免捍格有局限,所以朱子突破了祭祖禮中只講血氣相應的說法,有人問: “‘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至於祭妻及外親,則其精神非親之精神矣,豈於此但以心感之而不以氣乎?”朱子回答說: “但所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 (《朱子語類》卷3)朱子在這里從陰陽之氣 “本從一源中流出”的角度,重新解釋了感格的條件。 “從一源中流出”的氣,被朱子定義為 “公共之氣”。人問: “上古圣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朱子說: “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 (同上)無論一般人還是圣賢,甚至萬物之氣,皆同出一源,“這個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物皆得之” (同上),從這個意義上,天地萬物其實都是 “公共之氣”,如此天地萬物間也就無不存在感通的可能。如此道統祭祀中祭者與被祭者的感格問題就好解釋多了。但這樣一來,也還是有問題,那就是感格可能性太過寬泛,又要如何確定祭祀中感格的秩序呢?換言之,如何保證不同祭祀中祭者與被祭者之間總能一一對應,而不至于發生紊亂呢?就此朱子提出了“氣類相應”、 “祭其所當祭”之說,他說: “子之于祖先,固有顯然不易之理。若祭其它,亦祭其所當祭。……如天子則祭天,是其當祭,亦有氣類,烏得而不來歆乎!……今祭孔子必于學,其氣類亦可想。” (同上)這樣無論是何種祭祀,雖然感格的前提都是 “公共之氣”,但由于感格的氣類不同,在 “祭其所當祭”時相應的對象也自然不同,皆會井然有序。后學祭祀先圣,乃出于道統傳承,其氣類自然就在道業上存在著感應。如此道統祭祀中祭者與被祭者間的感格難題就基本得以解決。
但道統譜系的非連續性仍是個問題,宗脈依血脈傳續得以綿延,道脈沒有師門次第傳授,又有時代間隔,要如何維持傳承?針對這個問題,朱子借助儒家 “祭祀主敬”之義,特別強調了 “心”在祭祀中的作用,又進一步提出了 “動心達氣”、 “行道傳心”等說法。他說: “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 (同上)朱子這里談感格之理,除了涉及 “氣類相應”,又特別提出了 “心”的作用,認為 “心”在實現祭者與被祭者間的 “氣類相應”上起著關鍵的作用。朱子此意在為道統的合理性提供更為有利的論證,因為對于祭祖、祭天地之類,“氣類相應”都是非常實際的,祭祖有血氣相應,祭天地有名位相應,唯獨道統祭祀的 “氣類相應”指向令人頗感虛玄的 “道”、 “學”,對應精神領域的 “氣類相應”,就不得不強調 “心”的作用了。他說: “神之有無,皆在于此心之誠與不誠”(《朱子語類》卷25), “人心才動,必達于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想感通” (《朱子語類》卷3)。此即所謂 “動心達氣”之說。誠敬之心對祭祀之氣的感格有著如此大的作用,后世學子進于道業,期于賢圣,以誠敬之心祭祀先圣先賢,感格來享豈非當然之事?在朱子看來,這其中當然也自有 “祭其所當祭”之理。朱子強調 “心”在道統祭祀中的重要性并不僅僅在于支持 “氣類相應”說,還在于彌補道統非連續性的缺憾。朱子道統論有 “人心”、“道心”的分判,認為 “其覺于理者,道心也;其覺于欲者,人心也” (《朱子語類》卷62),維系道統傳承的當然是 “道心”,道心是至誠通于天理的顯現,所以,朱子結合道統祭祀中的誠 “心”之義,又進一步提出了 “行道傳心”之說,他說:“圣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圣賢之道,傳圣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朱子語類》卷3)圣賢之道的傳承依賴于 “傳心”得以維系,那自然是沒有時代、師承等方面的局限的,朱子在 《滄州精舍告先圣文》中講 “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也即此意。這樣一來,朱子就不但順利地詮釋了道統祭祀中感格之理,同時也彌補了道統傳承非連續性的缺憾問題,為道統的禮學實踐從理氣論上也作了深入的論證。
綜上所論,我們可以看出,朱子所以帶著儒家的禮學實踐精神切實地去踐履道統祭祀,并對此予以深入的理論論證,乃是因為在他來看,道統絕不只是對于一種傳統基于價值判斷的個人抑或學派的主張,也絕不只是一種主觀的觀念性存在,其傳承的實在性、統一性就體現在道統譜系上,而這一點則只有通過道統祭祀的禮學實踐才能彰顯出來。我們今天通常將學術傳承與道統傳承加以區分,將前者視為一種歷史事實陳述,而將后者視為一種基于價值判斷的理念建構?,這當然是對的,但不容忽視的是,這種看法只是我們從今天的立場對道統現象做出的一種評判,并不能將之視為歷史上道統論者本人的實際觀念。如果不了解這一點,我們在對朱子道統論的研究中,就難免忽視其對道統所持有的特殊的宗教性情懷。朱子曾不止一次感慨時人祭祀先圣先師徒具儀式,缺少與圣賢感格溝通的誠敬?,這種感慨是與他深厚的道統情懷密不可分的。在這種禮法的宗教性情感層面,他的弟子也與之保持著高度的一致,也將道統領會為確實無疑的事實?。而正是這種深厚的道統情懷才使得朱子及其后繼者們執著并致力于道統的宣揚,最終使朱子道統說成為宋代淳祐以后學校、書院祭祀的主流觀念。
注釋:
① 牟堅: 《朱子對 “克己復禮”的詮釋與辨析》,《中國哲學史》2009年第1期。
② 趙師夏: 《延平答問跋》, 《朱子全書》第1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354頁。
③ 當然朱子并不是認為心學不是儒學,也不是認為心學沒有工夫論,而是認為心學講發明本心,就心上用功,其工夫論嚴重缺乏形下的可落實性,必然流于空洞。陽明后學之流弊恰是很好的證明。
④ 《答曾擇之》, 《朱文公文集》卷60, 《朱子全書》第23冊,第2893頁。
⑤ 《禮記·文王世子》: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圣、先師。” 《禮記·祭義》: “祀先賢于西學。”
⑥ 如乾道四年 (1168)作 《建寧府崇安縣學二公祠記》、淳熙三年 (1176)作 《建康府學明道先生祠記》、淳熙四年 (1177)作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等等,參肖永明: 《儒學·書院·社會——社會文化史視野中的書院》,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376頁。
⑦ 肖永明: 《儒學·書院·社會——社會文化史視野中的書院》,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377頁。
⑧ 楊志剛: 《中國禮儀制度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頁。
⑨ [日]吾妻重二: 《朱熹 〈家禮〉實證研究》,吳震等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32頁。
⑩ 《信州州學大成殿記》, 《朱文公文集》卷80,《朱子全書》第24冊,第3806頁。
? 從這個意義上講,朱子在竹林精舍所樹立的祭祀形式已遠遠超出以往任何學校、書院祭祀先圣先師及先賢的意義,這種旨在彰顯道統傳承緒脈的祭祀,應該稱之為“道統祭祀”才是最合適的。由于這種道統意識的深入人心,后世才有以 “道統祠”之類命名的儒家祭祀場所出現,如 《名儒言行錄》卷4載楊繼盛 “因買東山超然堂基,立書院,祀歷代圣賢,名曰道統祠”。明代正德年間所建的晏公祠,原本叫作 “道統廟”,也是儒家道統祭祀的場所。而古代四大書院之一的嵩陽書院至今猶存有道統祠。
? 清代汪晉征 《還古書院祀朱文公議》: “書院祀先賢,所以正道脈而定所宗也。……凡講學之區,皆當祀朱子以定道脈之大宗也。” (《休寧縣志》卷7,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299頁)此即以朱子在儒學道統中為正統,猶如宗族血脈中之嫡傳大宗。
? 殷慧: 《朱熹道統觀的形成與釋奠儀的開展》,《湖南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3期。
? 《滄州精舍告先圣文》, 《朱文公文集》卷86,《朱子全書》第24冊,第4050頁。
? 如陳捷榮先生說: “道統之緒,在基本上乃為哲學性之統系而非歷史性或經籍上之系列。” (陳捷榮:《朱學論集》,臺灣學生書局1982年版,第17頁)
? 如 《信州州學大成殿記》: “熹惟國家稽古命祀,而禮先圣、先師于學宮,蓋將以明夫道之有統,……非徒修其墻屋,設其貌象,盛其器服,升降俯仰之容,以為觀美而已也。” (《朱文公文集》卷80)又 《朱子語類》卷3: “今行圣賢之道,傳圣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謾為之!”
? 如黃干 《朱文公先生行狀》說: “道之正統待人而后傳,至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周程張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 (《勉齋集》卷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