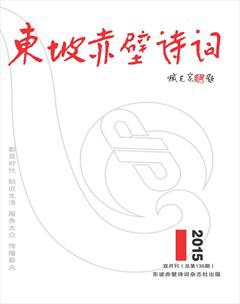擷取田園一葉詩
王小燕
每一位詩人的心里,都有一座詩的神圣殿堂。
其實,詩路卻很艱難。盡管如此,我仍然有信心,要朝這條詩路走下去。我出身農家,長在農村,學生時代在農校學習,長大后又在農業部門工作,一生與“農”字結下了不解之緣。現在已近不惑,估計這輩子也很難做一條跳出“農”門的小鯉魚了,以后還得在農業這條戰線上奮斗。但是,若談及田園,那是我熟悉的一片天。談起田園詩,那是我鐘愛的一塊地。我感覺有話可說。所以,就不避愚陋和淺薄,僅就我近幾年寫田園詩的感覺,說點體會,和諸位詩友分享一二。
一是注重時代感。屈指算來,我從農整整20年了,親歷過“農業真難,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的巨痛,也見證過自2003年來,中央連續12年發布1號文件聚集三農的喜悅。這種喜悅是真實的。一點一滴匯聚起來的,是看得見摸得著的。記得寫《辛卯正月赴菊花之鄉福田河建示范茶園感懷》的時候,小雨淅瀝,年味尚濃,我們農業人下到鄉間,籌算著新茶園的新址,為茶農提供多少茶苗,如何管理等各項事宜,遙想遠景,心情舒暢,詩情洋溢。《宋埠良種場甜玉米示范基地行吟》是2012年一次農業采風時的習作。在我們當地,玉米僅是小家小戶的種植,突然之間,見到一片上百畝的玉米地,蔚然成林,很有點小激動。更特別的是,這種甜玉米,口感特好,又甜又脆,熟可吃,生也可吃,農民形象地稱它為水果玉米。它的玉米棒子可以賣,秸桿是奶牛的飼料,也可以變錢,兩樣疊加,效益很是可觀。至于《玉樓春·癸巳初夏武漢茶博》,則是2013年我參加第六屆武漢茶博交會后的歸來之作。那時,麻城福白菊作為唯一的花茶參展,首次亮相茶博會,很吸人眼球。更值得幸運的是,作為一個愛茶人,我品嘗到了來自國內外的諸多好茶,讓人回味無窮。今天,農業變強了,農民變富了,農村變美了,傳統農業正向現代農業發展,鋤頭、鐮刀、扁擔、耕牛“農家四寶”正慢慢淡出我們的視野。插秧機、聯合收割機等農業機械,正向我們轟然開來。但制約農村發展的各種瓶頸問題也不容忽視,諸如農戶兼業化、村莊空心化、農村老齡化現象、最后一公里的問題等等。于是,就有一些反映三農現狀的文字流注筆端。《春旱》寫于2011年,當時,湖北省遭受了罕見的冬春夏三季連旱,我每天向省里上報農情,看著受災害面積一天天增大,心急如焚,卻望天興嘆。時至今日,我依然記得當時那種盼雨望雨祈雨的急切心情。《下鄉雜詠》寫于2013年,反映的是糧食比較效益低的問題。以前,老人們常說,莫想從土里面挖金子。今天,金子更難得挖了,農民種上一畝地,刨去各項投入,收入甚微。好在打工還不錯,可以直接提高農民的收入,然而土地拋荒問題,留守在家的“髻頭老頭蘿卜頭”問題,依然讓人憂心忡忡。
二是注重畫面感。麻城是一個花城,杜鵑、杏花、山茶、福白菊和玫瑰“五朵金花”已小有名氣。所以,我的筆下離開不了這樣那樣的花兒,經常“筆下生花”,如《菩薩蠻·合歡花》《憶江南·花朝看花》《山茶花》。寫《鷓鴣天·杜鵑》時,麻城杜鵑正開得如火如荼,“人間四月天,麻城看杜鵑。”這張名片正越擦越亮。在這首詩里,我將紅色古城和杜鵑花城這兩個點緊密地糅合一起,寫出花的內涵和外延。《菩薩蠻·福田訪菊》是2011年深秋我參加“相約福田河,共唱菊花歌”采風活動時,看到了一朵朵小菊花,密密匝匝地開到天邊,把田野鋪成一片像雪海地美麗場景。菊海里,一群系著碎頭巾、扎著素花圍裙的菊女,手指嫻熟自如地采菊,嬉菊,挑著菊花緩緩地行走在阡陌上。受此感染,我用一個個特寫鏡頭,重現了菊花一開萬畝的磅礴氣勢。菊農們在門口曬著菊餅的喜悅,還有蜜蜂在花間的翩翩舞姿,盡力將菊花之鄉最美的一面展現出來,表達了我對農家自然樸實生活的熱愛,以及對“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閑適愜意的向往。
三是注重情趣感。詩人余光中把人分為四等,一等人,高級而有趣;二等人,高級而無趣;三等人,低級而有趣;四等人,低級而無趣。這個標準用在詩詞上,也是比較恰當的。比如說范成大的60首四時田園雜興,他的每一首詩都是藏著太陽的水,讓人在回想中感受到無限的生活樂趣。受此影響,寫田園風景時,我不知不覺地會浮現出他們的作品,期望用自然清新格調優美的語言,寫出鄉村的風物,期望用獨特的情趣,寫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事。《下鄉雜興》是下鄉后所見所聞所感時的產物,在和農民近距離的接觸中,我盡力捕捉妙趣,展現他們的淳樸、憨厚和良善。《臨江仙·初夏過栗鄉遇古建水閣涼亭》的末尾更多是一種想象。美麗的水閣涼亭讓我想起了《廊橋遺夢》。寫于2013年“六一”時的《童年組詩》里的諸多情趣,更多的是一種回憶,一種穿越。
我學詩也晚,是偶然的一個瞬間,撞進了詩門。有幸的是,透過這扇門,我親自感知到了田園詩歌里那個美好世界的存在。受天分和眼界所限,我的習作還很稚嫩、青澀,語言缺乏錘煉,反映農村疾苦的筆觸不深,小我情調較重,但我一定會孜孜以求,樂學上進,植根田園,寫出更多發散著泥土氣息的田園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