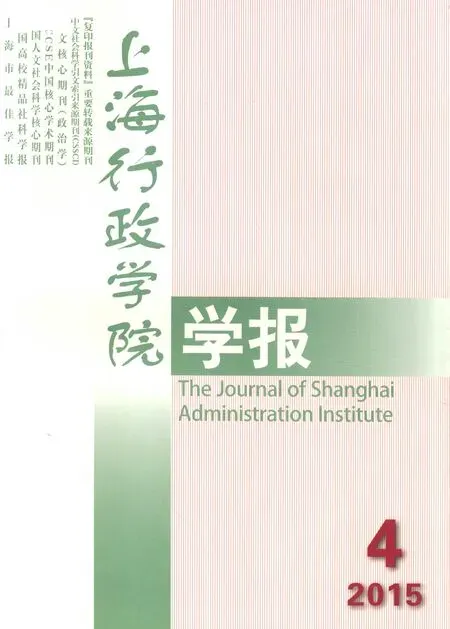從結構性依賴到制度性認同: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發展邏輯*
丁長艷
(上海行政學院 上海 200233)
從世界文明發展進程看,現代化已經從簡單階段進入復雜階段,現代政治風險容易將國家治理帶入更多不確定性中,個人、組織、社會與國家如何實現不同程度的自我保護,個人認同與社會認同之間的關系如何處理,這都是現代國家治理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隨著信息化技術日益滲透政治生活,重塑了權力、權利與民主間的關系,國家治理形態及其結構也發生本質變化。從政治發展角度看,權威理性化、結構分化、政治參與擴大是現代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征,并成功地建立起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認同。從20世紀末到現在,關于市場化與全球化給中國國家治理帶來的現實風險,在理論層面主要有“轉型崩潰論”與“結構適應論”兩種不同爭論。前者認為,局部危機容易導致國家治理的全面問題,就中國的國家治理與執政能力而言,中國共產黨不一定是處在即將崩潰的危險中,但是它卻面臨嚴重的治理危機①;后者認為,中國國家結構仍具有相當程度的彈性與適應性②,兩者聚焦的核心問題是中國國家治理的可持續。
針對上述關于中國國家治理的兩種爭論,轉換成現實問題是中國國家治理模式的轉型與發展邏輯議題,即從緣起于革命年代、定型于改革年代的中國國家治理模式具有典型的結構性依賴特征,能否成功建構國家治理的制度性認同決定了中國能否有效完成現代國家的建構。從應對國家體系的外部風險與解決內部問題兩個角度出發,本文認為,中國日益融入全球治理的進程,越來越需要建構穩定的制度性認同,適應現代國家治理需求的發展趨勢,一個具有“合法性、透明性、責任性、法治化、回應性、有效性”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實現與維護公共利益的基本條件。
一、制度性認同: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發展的一個基本趨勢
現代國家不僅包含對法律的共同認識和一致利益的觀念,還包括蘊含共同利益的政治制度,這些制度賦予共同目標新的意義,因為政治制度是道德一致性與共同利益在行為上的表現,政治制度的形態很大程度上決定國家的治理結構與治理績效。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具有三大基本特點:“以現代社會為基礎,以構成國家的每個人擁有政治平等的政治解放為歷史和邏輯前提;以現代國家主權為核心,以建構全體人民能夠共享并獲得發展保障的國家制度體系為基本的組織框架;以公民權的保障為機制,將社會的全體成員聚合為具有共同紐帶的共同體。”③只有以社會、國家和公民權保障為中心,建構國家治理體系的不同制度層次,并形成一套穩定和有效的制度體系,進而有效地產生穩定而持續的國家認同,才能形成一個有效的國家治理體系。因此,構建以制度性認同為核心的國家認同是現代國家治理的關鍵因素。
從制度性認同蘊含的層次看,現代國家認同主要包含兩類屬性與分層的認同形式,具有雙元結構④:一類是歸屬性的國家認同。指公民對同胞-民族共同體的認同,這是公民文化-心理歸屬的國家/民族認同;另一類是贊同性的國家認同。指公民對國家政權系統的同意、贊同、支持,即公民在將自己視為公民-民族成員的基礎上,基于一個國家“特定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有所肯定所產生的政治性認同”⑤,這兩類認同分別依托于不同的制度層次與制度形式。現實中這兩類認同常會產生緊張關系,因為,“民族國家概念包含著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之間的緊張,即平等主義的法律共同體和歷史命運共同體之間的緊張。”⑥在現代國家治理過程中集中表現為:不同的國家認同需要塑造上述兩類公民身份與公民行為,兩者在不同領域和不同層次的交叉與融合造就了現代國家的治理形態。
第一,憲法體系主導國家生活塑造一種混合型的國家認同。正是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國家對所有的公民都保持開放狀態,使得憲法體系為公民提供政治-法律上的開放性身份,因為,“在多元社會中,憲法表達的是一種形式上的共識。公民們愿意用這樣一系列原則來指導他們的共同生活,這些原則,因為它們符合每個人的平等利益,可以獲得所有人的經過論證的同意。”⑦憲法滲透于國家和社會生活,塑造了形式上與實質上的現代國家。通過憲法體系確認了一種不同于傳統的公民與共同體的新的文化-心理身份,塑造了一種現代意義上的歸屬性國家認同。同時,運行于憲法體系下的一套法律體系也在塑造公民的政治-法律身份,使得公民認同指向一套國家制度體系,依托于憲法體系生成兩類不同身份的國家認同,使得公民對國家的認同趨于成熟和穩定。
第二,政治制度滿足公共需求促成一種贊成性的國家認同。除了憲法塑造混合型國家認同外,政治制度化的過程能否滿足公共需求,很大程度上影響和支配國家認同的實踐效果,“制度的精進與否遂成為合理愛國心與合理國家認同的最佳指標。”⑧因為,制度不僅塑造公民的政治行為,也確認與塑造公民的政治-法律身份,進而生成贊成性的國家認同。這是現代國家認同的制度基礎,相比歸屬性的國家認同,贊成性的國家認同比較容易實現,它已經成功突破民族的心理界限與地域的地理界限,在一個新的公共空間中塑造了一種共同的與平等的政治-法律身份,它基于普遍化的政治制度化過程,將傳統的特殊治理方式轉換成一種現代與平等的國家行為。
第三,國家福利的一體化建設塑造一種歸屬性的國家認同。對于國家而言,公民的政治-法律身份決定基礎層面的國家認同,而歸屬性的國家認同則是一種更高層面的心理認同,不僅取決于國家制度的滿足情況,還需要公民對國家形成結構性的依賴與支持關系,而現代國家福利的一體化建設構建了這種持續性的結構化關系。“一個全面覆蓋而富有成效的國家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將極大地提升公民日常生活的質量和抗擊社會風險的能力,從而強化公民對國家的依賴與信任,推動公民對國家的認同。”⑨因為,從現實來看,建立一體化的國家福利體系能夠實現公民的心理安全與文化需要方面的滿足。
上述以政治-法律的公民身份形成的贊成性的國家認同、以文化-心理的公民身份生成的歸屬性的國家認同兩種類型,貫穿了現代國家治理的整個發展過程,這兩種認同在國家治理層面最直接的表現就是一種制度性認同。因而,對于像中國這一類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構建一體化的、穩定的與系統的制度性認同是現代國家治理的基本方向和發展特征。
二、結構性依賴:中國傳統“政黨-國家”體制的治理邏輯
國家的治理結構與形態取決于時空等綜合要素,在其他條件相同的前提下,國家治理模式決定其政治運行特定的優勢、負荷、困難和挑戰。國家治理模式不是任意選擇的,常與國家的歷史有著明顯的路徑依賴關系,中國國家治理的歷史基礎、轉型條件與現實需要三者共同決定當前的結構形態。中國國家治理涉及三大主要內容:一是現代國家治理的一般性規律與發展特點;二是社會主義因素及其政治體制對中國國家治理的約束;三是傳統文化因素對中國國家治理、轉化與繼承的影響。這三大因素形成一種復雜的結構性約束路徑。但是從決定性程度看未來中國國家治理如何轉型與發展,很大程度上受到傳統“政黨-國家”體制的結構性依賴特征的影響和支配。
中國傳統的政黨-國家體制源于革命的行動和邏輯,并形成對應的集權式國家治理結構。從制度學習的來源方面看,這種傳統的政黨-國家體制是與對蘇聯共產主義體制的模仿與借鑒有很大關系。在蘇聯式的共產主義國家體制中,國家被建構成為一個具有高度權威與權力的政黨領導下的全能主義型的控制體系,通過控制與支配市場、國家、社會、文化等領域的生存與發展資源,形成以政黨領導為中心的一套國家治理模式的支持性結構。“政黨科層、國家科層、國有經濟以及結構內可供攫取和分配的資源、政黨科層與國家科層包括經濟之間的互聯線、可用于更深地融入該結構的結構性反饋”⑩,這種政黨領導國家的政治邏輯在中國國家治理的實踐中主要生成四類嵌入的結構關系?:與國家系統的“政策領導”或“執行合一”關系;與社會領域的“有限控制”與“選擇適應”關系;與市場經濟(主要指國有企業)的“人事嵌入”與“權力支配”關系;對價值體系的“大眾引導”與“選擇收縮”關系。
相當長時期內,這種政黨與不同領域之間嵌入式的支配關系,是決定中國國家治理的結構性基礎與體制性因素。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國家治理行為與模式的改革則是對這一體制進行變革與優化。尤其是拓展到執政黨內部的改革,政黨執政重新制度化是一種全新的嘗試,政治方面進行“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的體制”的政治建設計劃?,這個過程分別在國家發展模式以及行為方式方面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類“發展型政體”?,主要是由于市場經濟的深度發展產生新的社會階層,中國共產黨通過適度開放意識形態領域和增加體制的包容性,與社會經濟領域中的特定群體進行持續的溝通融合,個人與社會組織可以通過國家體制表達利益訴求和在公共政策導向中形成特定的政治偏好,有限度地吸納社會力量。但是另一方面,任何特殊主義和政治化的利益訴求又是受到限制的,從而保持國家的相對自主性,這就分別在經濟治理、社會治理以及國家治理的不同層面,形成了特定的模式與結構。
第一,依賴經濟發展績效的發展型國家治理模式。對于發展型國家而言,合法性主要來自于國家推動經濟發展的成就,從發展策略及其成型模式看,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具有發展型國家的大部分特征。中國依賴改革開放的外部環境與發展機遇,特定階段中形成了依賴經濟發展績效的發展型國家治理模式。中國經濟發展理論,事實上形成了一套實踐性較強的經濟政策適應機制。既突破傳統政黨-國家體制內意識形態的硬約束,也沒有為自己設置特定的制度性框架。在不同區域和不同領域內的經濟發展模式具有高度的靈活性,而且,這些經濟發展模式主要是緣起于靈活的地方政府的創新行為,而非中央政府事先有意識的政策設計?,這是中國成為發展型國家的重要特點之一。然而,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也留下了后遺癥,尤其是政府行為的企業化取向,將官員的政治經濟利益和市場化改革緊密聯系起來,容易形成不正常的政商關系,在現實中表現為區域快速發展與官員腐敗的高度相關性。
第二,有限度吸納社會的監管型國家?治理方式。經濟社會的多元化發展必然產生多樣化、多層次的社會需求和參與需求,面對不同的社會群體時,中國共產黨的影響策略不一樣。其中,新生的社會階層如私營企業主群體是其重要的吸納對象。新社會群體在經濟方面的崛起必然會反映到社會地位與政治待遇方面,參與政治過程,與體制進行合作成為一種常見的形態。因此,處理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治理戰略和策略,需要考慮“作為戰略群體的企業家階層的社會與政治功能”?的現實問題。因為,從建國以來的傳統政商關系看,企業家只有當他們(或許也包括其他階層)被“嵌入”政黨-國家體制中,而不是與之分離時,他們才會感到安全?。針對新生社會階層與社會力量,他們與國家之間是一種適應的依賴與監管關系,因為它們不斷增強的經濟與社會影響力,所以“企業家階層”成為國家體制吸納的重要對象,并在政策與社會地位方面得到優待和享有特定的正式與非正式的參與通道,同時,這種依賴與保護型的體制也更有利于國家對他們進行監管。
第三,有限多元的混合型治理的國家認同模式。上述經濟、社會兩個領域的國家治理過程表明,傳統的政黨-國家體制形成的結構性依賴特征已經發生變遷,既利用原有體制的結構性依賴關系,在經濟與社會領域有限度地進行變革,并逐漸形成新的國家認同模式。同時,這種新模式并未完全瓦解原來的結構性依賴關系,而是形成了一種新的混合型的國家認同模式。一方面,中國的普通公眾因經濟發展績效產生新的國家認同,這種認同能否形成長期與穩定的認同關系,主要取決于經濟發展績效的持續性。同時,這種認同會部分轉化為贊成性的國家認同,但是,要形成一種普遍的穩定的國家認同,還需要相應的支持條件。另一方面,針對社會領域的監管型國家治理方式,公民對國家的體制性依賴與心理歸屬都存在,但是能否通過制度化過程促使公民形成穩定的政治-法律身份,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公眾在文化-心理層面認同的鞏固。
在國家意識形態話語體系中,上述三類領域的國家治理形態,主要是通過強化中國共產黨與經濟治理、社會治理與國家治理的現實關聯性實現的。從體制與現實兩個方面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是優化中國國家治理體系與提升治理能力的核心問題,加強和改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不同時期改革的中心議題。因而,通過怎樣的戰略與策略塑造中國國家治理的新模式,關鍵是如何將基于傳統革命邏輯形成的政黨領導結構、后來高度體制化的領導結構,與現代國家治理之間形成適應性的制度化關系,進而轉化為高度穩定的國家政治認同。從當前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礎來看,盡管革命秩序下的中國國家治理模式正在深度變遷,但是國家秩序賴以生存的核心治理結構仍然完好地保持。中國共產黨通過重新塑造組織系統的“吸收”戰略,形成一個使中國共產黨得以重建、維持執政地位的“適應的非正式機制”的變體?,它依賴于執政黨領導與治理的結構及其治理績效,這種治理邏輯仍是支配當前與未來中國國家治理的基礎與關鍵。
三、制度性認同:中國國家治理的發展趨勢與基本特征
一定階段中,中國國家治理需要依賴經濟治理的績效,但是,從制度性認同的角度看,長期的國家認同依托于優化國家治理體系與提升治理能力,兩者的協調性關系主要涉及三大關鍵性因素:一是國家權力屬性的現代轉變;二是國家權力的體系性與制度化的結構安排;三是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之間的協調性。現代國家發展的歷史與實踐表明,國家治理模式是自上而下分層的,它是在鞏固公民的國家認同過程中走向成熟與完善。這種分層分別形成四種不同類型的國家認同:國家主權與憲法認同層面、文化信仰與價值認同層面、法律和制度認同層面、福利與政策認同層面。對于傳統資本主義國家而言,法律與制度、文化與價值層面的認同要先于其他兩類,其中國家主權與憲法認同早于福利與政策認同,這一類國家認同的建構是一個長期累積的過程。然而,對于處于轉型的發展中國家而言,這幾大要素的構建被容納進同一個時空中,建構整體的國家認同與優化國家治理模式是現代國家治理的一體兩面。
從建構國家認同的角度看,現代國家治理必須是國家制度建設與國家結構體系優化的有機統一。國家結構與國家制度之間的關系是制約中國國家治理的核心矛盾之一。在民主成為國家治理重要目標的前提下,國家制度建設必須要圍繞優化國家結構體系展開?:以提升制度的合理性與有效性,優化國家治理結構體系;同時要通過國家治理結構體系的整體優化,穩定與鞏固國家制度,民主才有可能成為有利的國家治理因素,進而成為正向的治理資源。從優化治理的路徑看,毫無疑問,現實問題——對應性改革措施——系統性頂層設計的邏輯關聯是優化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治理思路?。中國的國家建設主要包括橫向的公共授權體系和垂直的政府體系兩大部分,國家治理體系包括政府和公眾之間、中央和地方之間、中國共產黨和社會力量這三組治理結構之間的關系,在現實中能否形成有效的治理能力,宏觀層面取決于“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大關系的結構化與制度化的現實形態。對于超大規模的中國社會,利益代表的邏輯與實踐過程就是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政治治理結構上要充分塑造與完善各項制度的結構與功能,使政治治理結構與多元的經濟社會治理需求適應,將多元的社會利益轉化為統一的行動。從實踐角度看,當前中國的國家治理已經具備了制度性認同的發展趨勢與基本特征,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意識形態的大眾化與共識性。治理價值的文明化是現代國家發展的基本趨勢,對人類共同體生活與優秀文明價值的追求是現代國家學習的一個重要方面。一般情況下,對于一個正常的國家而言,成熟的民族主義與全球主義的輸入與轉化之間不存在本質矛盾。有選擇地學習與融入以西方國家為表現形式的成熟的“國家產品”,及其背后的人類共同的價值觀,有助于中國更好地融入人類文明與現代化的進程。這并非要將中國政治秩序西方化,而是要在制度治理與秩序建構方面,為變化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國家治理的一般規律。意識形態領域的多元化與大眾化是不可回避的發展趨勢,因為,意識形態領域的建設要兼顧一般發展規律和中國的主體性,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兼顧與均衡二者的關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與國家治理體系、國家制度之間形成契合與支持的關系,價值層面既要凸顯國家治理的主體性,同時,實踐層面制度體系要體現人類的共同價值,因而,意識形態領域內復合式的引導與治理十分重要。
第二,公眾參與的制度化與有序化。因為現代國家的兩大治理主題即發展與秩序的需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正在探索一條更安全的政治改革之路能帶來更多責任、透明度和回應性的制度改革,由此構建更有效、更具合法性的治理體系。”[21]民主執政是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三大目標之一,治理體系民主化與治理結構的透明化是同一過程的兩面。法律通過制度化的渠道與機制保障公眾能分享政治決策權。雖然,治理有效與否和民主之間并沒有直接的相關性,但是要解決權力過大導致的治理失效問題,必須要依賴民主的治理結構與治理過程。民主治理不僅需要擁有共同的制度平臺,還需要基于多元利益和平等的對話協商的機制。以當前中國的公眾參與現狀而言,依托于政治制度與組織構建適應中國國家發展需要的政治治理結構是關鍵。因為,民主政治中有機會參與到協商活動中的行動者接受集體決策,這是合法性的核心,是合法性表達的開端。[22]制度化的公眾參與能夠塑造有序的公共生活,通過民主參與治理的技術手段,不僅能提升官僚體系的理性化程度,也在塑造一種新型的政黨與社會的溝通形態。
第三,官僚體系的理性化與技術化。從制度化角度看,現代化過程中成熟的國家治理模式應該是建立了政治主體與環境之間穩定的制度化關系。中國的國家治理經歷了一個從總體支配向技術治理[23]、從直接治理向間接治理轉變的過程。在行政體制內部集中表現為一種“治官權與治民權分設、上下分治的治理體制”[24]。這種結構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官僚體系內部的彈性與地方創新,但是,也造成了實踐中地方政府或部門主義的權力過大的亂象等問題。權力責任清單的生成是其理性化與技術化的集中表現。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與四中全會決定針對這一突出的現實問題,從重塑官僚體系的權責關系出發,圍繞現代官僚制的理性化與技術化趨勢,通過司法改革啟動以程序主義為中心的官僚制的改革。因為,官僚體系的理性化不僅對界定復雜社會中的利益、決定這些利益的活動戰略發揮重要作用,保障規范公共權力和保障社會穩定在法律方面的公平正義。
上述三大發展趨勢揭示了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過程的發展特征,從實踐層面看,當前中國的國家治理績效不僅依賴國家治理體系內部的協調,更依賴國家、社會與公眾間的復合治理形態。復合治理的特點是多元主體參與、合作的協調關系和權力的多維運行,將中國的政黨治理與政府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等形態有效結合起來,塑造自律型的政黨治理是關鍵。制度性認同主要是通過不同層面的治理結構,實現國家公權與個體私權間穩定的制度化關系。中國在國家層面的建制化進程不僅取決于制度化的基礎,更取決于在治理體系內部形成多元治理主體之間的凝聚力和整合情況。一般而言,處于轉型階段中的發展中國家,對于一種暫時的過渡性政治權威的需要是存在的,關鍵是能否將對權威的依賴與服從關系轉移到制度體系上,形成穩定的制度性認同結構。制度性認同對于國家治理與政治穩定的積極影響已是基本常識,因為這種依賴是最穩定和持續性的。
四、制度性認同發展進程中中國國家治理的價值維度與支持性條件
相當長時間內,中國共產黨與國家、社會和市場之間的關系是主導國家治理的核心因素,它決定中國國家治理的過程。“東亞社會一般都有一個弱小的‘市民社會’:很少獨立于國家或有能力向國家提出要求的有影響和有力量的第二團體……東亞社會確實有走向非個人化的合理性的要求;但在許多方面,這個地區的現代化選擇了另一種路徑。”[25]東亞區域內的國家不可能發展為西方國家的治理模式。不同的國家發展路徑塑造了不同形態的治理體系與治理制度,更確切地講,“制度是社會的游戲規則,更規范地講,它們是為人們的相互關系而人為設定的一些制約。”[26]這些制約性規則是社會與國家層面的普遍性共識,并在國家內部塑造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之間的關系。因而,要完善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內部的價值原則、制度規范與國家認同之間的舊有關系形態,進而重塑與優化一種新的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關系形態。
1.制度性認同進程中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中國維度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成熟的國家治理體系能夠解決國家組織結構與制度之間的協調性問題,即將現代國家與人類的基本價值合理地嵌入特定的歷史、經濟與社會結構之中,并且內化為公眾的日常行為習慣。在中國全面深化改革與推動發展的背景下,深度了解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發展的價值導向、行為變遷及其發展重心,尤其是當前中國國家治理在價值層面需要解決的特殊性問題,它們共同決定了中國國家治理的內在特質與未來走向。
第一,善治原則在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內外的轉化與運用。中國語境中的治理是“運用權威維持秩序以滿足公眾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種不同的制度關系中運用權力去引導、控制和規范公民的各種活動,以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27]通過中國學者們的本土化努力,傳入中國后的治理概念以及變形后的治理理論,成為正在轉型中的中國經濟社會改革的有效治理工具。善治概念的價值導向既為中國的國家治理與政府治理提供了倫理支持,同時,通過社會力量介入國家治理與政府治理的過程,既調整了政府與公眾間的治理結構,也緩和了公眾和傳統意識形態之間的緊張關系。中國的國家治理通過在價值導向方面塑造公民對國家層面的制度性認同,善治原則及其過程提供了一種現實的可能性。
第二,重新制度化塑造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的協調性。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對當前與未來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有明確的發展定位:“必須適應國家現代化總進程,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提高國家機構履職能力,提高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經濟社會文化事務、自身事務的能力,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不斷提高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效治理國家的能力。”[28]從目標、維度與特征方面明確了國家治理有效性、制度治理與治理能力之間的關聯性,同時,突出制度治理的有效性是當前決定中國國家治理能力的核心問題。圍繞現代國家治理的技術層面、民主層面和法治層面的發展導向,從重新塑造執政黨、國家機構、社會力量以及公眾各自的權責體系、以及相互之間新的治理關系出發,優化國家治理體系內部各種錯綜復雜的主體關系,從整體上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治理能力,形成與全面深化改革發展趨勢相適應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第三,塑造一種新政治倫理與建構公民對國家的一體化認同。無論是制度還是思想,兩者結合的方式決定了國家治理的屬性、形態與實踐形式。從國家治理的思想層面看,與現代政治發展契合的價值倫理為國家治理提供了發展導向。這種倫理是政治精英層面對國家治理及其權力的一種整體規劃,“統治的思想與等級化的權力、垂直和自上而下的指揮關系,以及以整齊劃一的方式推行的意志等,與對國家整體性的思考緊密相關。”[29]對國家整體性的思考是建構公民對國家的一體化認同的前提與基礎,新政治倫理的形成不僅依賴于上述重新制度化塑造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間協調關系的結果,而且公民對國家的一體化認同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這種新倫理。同時,建構公民對國家的認同也是塑造新政治倫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推進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新時期,重新制度化的過程塑造公民的政治-法律身份以及文化-心理身份,生成公民對國家持久的政治認同。
2.制度性認同與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支持性條件的培育
當國家治理打上文明模式的烙印時,中國國家轉型的結構對外部環境的反應往往是遲緩的,造成了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適應性難題。只有從國家治理的一般趨勢與中國的特殊內涵兩個角度考察,摒棄國家治理的中西對峙的二元思維,在接受、融通、學習與轉化中,促使中國的國家治理朝著制度化、規范化與程序化方向發展。從科學執政、民主執政與依法執政的三維角度看中國的國家治理,“軸心-外圍”的政黨領導結構與中心治理路徑是中國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特點。國家治理中的制度性認同一般依賴于兩大社會類資本的構建,一是結構性社會資本。通過規則、程序以及慣例建立某種社會網絡,賦予確定的組織角色,促進信息分享,達成集體行動,制定政策,形成對國家的特定性支持;二是認知型社會資本。通過共享的價值觀、規范、信任、態度或信仰等,影響個體的行為選擇,形成對政治體系的普遍性支持。前者依賴于后者的心理與文化基礎,后者又建立在前者形成的制度性規范與認同基礎上。從培育制度性認同角度看,無論是價值導向還是過程結果都需要相應的支持性條件,主要有四大關鍵性因素。
第一,塑造與優化現代公民教育體系。一個成熟的國家治理體系保持其社會、思想與國家的一體性是國家認同的基本任務,“為了使社會成立,尤其是為了使社會欣欣向榮,就必須用某種主要的思想把全體公民的精神經常集中起來,并保持其整體性。”[30]這種整體性不同于革命年代國家與公眾間的關系,也區別于改革之初通過經濟績效塑造公眾對國家的結構性依賴,而是將正在不斷伴隨著經濟社會變遷的公民教育定型化與公共化,將公民對國家的認同引導到穩定的制度性認同框架內。前述官僚體系的理性化與現代公民教育是塑造現代國家與公民關系的一體兩面,沒有理性的公民教育體系,也就難以有效運行理性化的官僚體系。
第二,提供一體化的福利保障體系。當前中國國家治理領域中引發諸多經濟社會問題的一個重要誘因是公民權與公民福利保障缺失。結構性依賴的國家治理結構下,中國國家領域內以政府為主導的治理結構存在主體單一化的問題,導致治理過程容易出現公共權力的權責失衡,國家責任的“缺場”與政府責任的“缺位”十分常見,造成中國公民的政治-法律身份塑造出現困難,難以生成贊成性的國家認同。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建立適合國情的一體化的福利保障體系與網絡,從國家認同層次看,一體化的福利保障體系是公民認同的基本物質條件,為公民的政策認同提供現實基礎,進而才有可能產生制度層面與更高層次的認同。
第三,培育與生成現代理性的公共空間。上述現代公民教育體系只是塑造理性公民的一個必要條件,并非充分條件。對于國家認同而言,治理體系內部的權力結構均衡對公共空間有更高要求。因為,“一種潛在的、參與性的公民對精英的自主施加了有力的限制。這些限制可能變得越來越重要,因為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和文化發展的邏輯要求(呼喚)越來越多樣化的、富有知識的、復雜的、要求嚴格的公民。”[31]公共空間是訓練與培育“公共人”的必備條件,現代國家治理過程提供穩定與暢通的溝通制度與渠道。理性公共空間為理性化政府與公民提供長期聯系的紐帶。
第四,網絡化的治理技術嵌入國家治理。從形式上看,現代國家治理必然也是一種網絡化的治理形態。任何投身于集體行動組織都需要借助其他組織的力量進行資源交換和合作實現共同目標,于是網絡者建立起一種彼此信任和基于規則的互動模式。[32]處于不同社會網絡與政治網絡中的個體,通過現代信息技術被“網羅”成相互交織的獨立主體。既改變了國家治理領域內不同主體的交往關系,也塑造了一種立體式的治理需求網絡,為現代國家治理提供了一種可供利用的技術資源與治理形式。
綜合看,中國從結構性依賴的國家治理走向現代國家治理是必然的發展趨勢,制度性認同是解決中國實踐中的發展問題的關鍵,也是實現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和依法執政的有效治理路徑。鑒于中國實踐中已經出現制度性認同的發展趨勢和局部特征。如何形成一體化的現代國家認同,重塑制度與建構認同是現代國家治理的一體兩面,對于超大型中國的國家治理而言十分關鍵。
注釋:
①Minxin Pei,China's Governance Crisis,Foreign Affairs,Vol.81,No,5,2002,pp.96-109;Minxin Pei,Beijing Drama:China's Governance Crisis and Bush's New Challenge,Policy Brief,No.21,Washington,D.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02.
②鄭永年:《全球化與中國國家轉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沈大偉:《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試》,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
③?林尚立:《現代國家認同建構的政治邏輯》,《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8期。
④肖濱:《兩種公民身份與國家認同的雙元結構》,《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
⑤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6頁。
⑥[德]哈貝馬斯:《包容他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5頁。
⑦[德]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關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國的商談理論》,三聯書店,2003年,第660頁。
⑧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10頁。
⑨李友梅:《社會認同:一種結構性視野的分析——以美、德、日三國為例》,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年,第16-17頁。
⑩[匈]喬納蒂:《自我耗竭式演進:政黨-國家體制的模型與驗證》,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第17頁。
?丁長艷:《現代化轉型中國家治理的風險治理與秩序建構》,《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
?Joseph Fewsmith,The Communist Party in Evolution,paper presented at the 40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of the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er,Hong Kong.January 2003.
?Pempel,T.J.,The Development Regime in a Changing World Ecomomy.In Meredith Woo Cumings ed.,The Developmental State.Ithaca&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
?So,Alvin Y.,Rethinking the Chinese Developmental Miracle,in Ho-Fung ed.,Chin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9.
?Kanishka,Jayasuriya.Beyond Institutional Fetishism from the Developmental to Regulatory State,New Political Economy.2005,10(3),p:381-87.
?[德]海貝勒:《作為戰略群體的企業家:中國私營企業家的社會與政治功能分析》,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
?Bruce Dickson,Integrating Wealth and Power in China: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the Private Secto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Kellee S.Tsai,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The politics of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in China,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7.
?程竹汝:《論政治體制改革的重點與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14年第2期。
[21][美]戴蒙德:《評王長江<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中國治理評論》2012年第1期。
[22]John S.Dryzek,Foundations and Frontiers of Deliberative Governa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143.
[23]梁渠東、周飛周、應星:《從“總體支配”到“技術治理”:基于中國30年改革經驗的社會學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6期。
[24]曹正漢:《中國上下分治的治理體制及其穩定機制》,《社會學研究》2011年第1期。
[25][美]霍華德·威亞爾達:《非西方發展理論——地區模式與全球趨勢》,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6頁。
[26][美]道格拉斯·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頁。
[27]俞可平等:《中國公民社會的興起與治理的變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531頁。
[28]習近平:《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新華網2014年2月17日。
[29][法]皮埃爾·卡藍默等:《破碎的民主——試論治理的革命》,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第14頁。
[30][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商務印書館,1991年,第524頁。
[31][美]賈恩·弗朗哥:《國家:本質、發展與前景》,上海世紀出版社,2007年,第78頁。
[32]Stoker,Governance as Theory:Five Propositions,International Social Journal,Vol.50,1998,p.1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