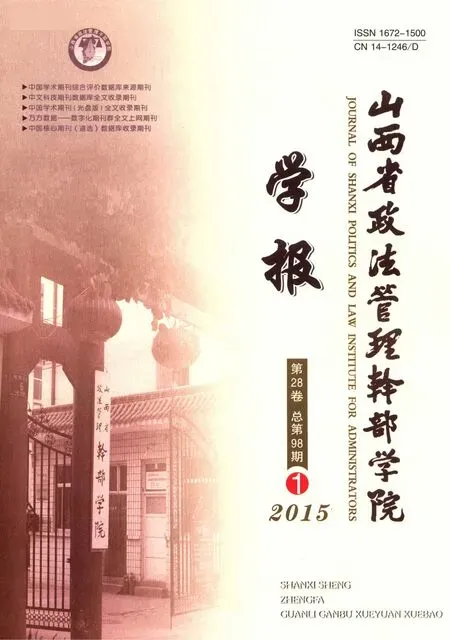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芻議
秦恒娟
(蘇州大學,江蘇蘇州215000)
一、我國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現狀
(一)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不足
2013年《刑事訴訟法》增加了“特別程序”,其中分別規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和當事人和解的公訴案件訴訟程序:在公訴案件中,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誠悔罪,通過向被害人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方式獲得被害人諒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雙方當事人可以和解:(1)因民間糾紛引起,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第五章(侵犯財產權利)規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2)除瀆職犯罪以外的可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過失犯罪案件。此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內曾經故意犯罪的,不適用本章規定的程序。從以上條文中可以看出一些不足和遺憾:首先,對于刑事和解的具體操作過程規定的過于粗糙,和解程序缺乏操作性,這與西方國家主張的刑事和解有較大差異。其次,也是本文的討論重點,刑事訴訟法所主張的刑事和解是一種混合式的刑事和解,并沒有考慮未成年人這一主體的特殊性,本文將對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問題提出初步構想。
(二)實踐與理想的偏差
刑事訴訟法規定未成年人故意犯罪案件適用刑事和解僅限于新法分則第四章和第五章規定的犯罪案件,而且是“因民間糾紛引起”的案件。所謂“因民間糾紛引起”,是指犯罪的起因是公民之間因財產、人身等問題引發的糾紛,既包括因婚姻、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的案件,也包括因口角、泄憤等偶發性矛盾引發的案件。[1]但是根據各地司法實踐經驗來看,未成年人犯罪主要集中在《刑法》分則第四章至第六章。由于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經常發生尋釁滋事、聚眾斗毆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刑事案件,并未被納入刑事和解的范圍。第四章和第五章又限于“民間糾紛引起”的案件,現實是未成年人并不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因而未成年人的行為又很少涉及這一情形。綜上,實踐中未成年人的刑事和解適用范圍要寬于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情形。有些學者的認為,根據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程序中司法權力組織形態的特點,可以分為專門模式與混合模式,專門模式是指和解程序僅適用于未成年人,并由專門機關或部門主持,以適應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混合模式是指和解程序不分對象(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主持機關并不具有專門性。[2]我國現有的未成年人的刑事和解制度是一種混合式的模式,筆者在本文中主張建立一種專門模式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將其與成年人刑事和解區分開來。
二、建立專門化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論基礎
(一)恢復性司法理念
恢復性司法是一種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所有與特定犯罪有關的當事人走到一起,共同商討如何處理犯罪所造成的后果及其對未來的影響。[3]恢復性司法強調對造成的傷害進行彌補,這是恢復性司法的關鍵特征,也是區別與懲罰性司法的關鍵。傷害包括物質損害、被害人心理和相關的傷害、社會不安寧和社區憤怒等,其中,未成年罪犯與被害人和解是目前使用恢復性司法的主要形式。我國司法實踐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對被害人的物質賠償做的較為滿意,但是忽略了被害人的心理補償,因而要倡導恢復性司法理念,糾正加害人的“用錢減刑”的觀念。在恢復性司法中,被告人不是不受懲罰,而是通過補償、賠禮道歉等方式對被告人予以懲戒。與傳統的懲罰性司法相比,恢復性司法更人道,更符合被告人的心理訴求,同時也兼顧了被害人的利益。我國對未成年罪犯一貫采取“雙保護”和“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主張既要注重社會的安全秩序,又要注重保護失足的未成年人,使未成年罪犯能夠重新融入社會。恢復性司法體現了這一要求,并且在促進未成年罪犯融入社會上更勝一籌,從而使我國一貫主張的保護未成年人政策更具現實性。
(二)尊重被害人意志
法律不僅要保護被告人的利益,也要注重保護被害人的利益。在未成年人刑事和解過程中,不僅要注重未成年罪犯的重新犯罪率、使其真正的回歸社會,同時也要關注被害人的利益。眾所周知,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是直接遭受利益損失的受害者。被害人所遭受的損失不僅是在物質上,也有精神上的:物質損失方面,尤其是對經濟困難的受害者而言,物質賠償至關重要。如果一味地對被告人處以刑罰,被告人就會忽視對被害人的物質賠償,認為既然都要遭受刑罰,為何還要賠償他們的損失呢?精神賠償方面,大多數此類刑事案件都是未成年人之間發生的,如果不注重被害人的心理撫慰,可能使未成年被害人出現復仇的想法,逐漸走向犯罪的道路。因而,筆者認為,被害人之所以同意刑事和解,是因為通過刑事和解能最大程度地維護自身的利益,獲得物質賠償,早日擺脫困境。而且通過未成年罪犯與被害人之間的溝通與交流,未成年罪犯以賠禮道歉的方式求得被害人的原諒,兩人冰釋前嫌。所以,從尊重被害人的利益的角度來考慮,建立專門模式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具有正當性。
(三)我國傳統的訴訟文化
中國人歷來注重“以和為貴”,具有長期的厭訟、息訟、無訟的觀念,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正是這一傳統訴訟文化觀念的體現。通過和解程序解決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利益爭端,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與被害人關系的修復,不僅有利于兩家關系的和睦,也有利于和諧社會的建立。
三、對西方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考察
(一)刑事和解的起源
刑事和解制度的雛形始于197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某市的“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兩名年輕人以砸壞窗戶、刺破輪胎等方式侵犯了22名被害人的財產,在緩刑官的說服下,法官讓案件中兩名被告與被害人會面,被告認識到了自己行為帶給別人的損害,隨后積極向被害人支付了全部賠償金,法官對其判處了緩刑。[4]這起案例引起了美國司法機關的重視,逐步制定了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系統計劃,現在已被世界上英、美、德、日等許多國家所采用。
(二)新西蘭的家庭群體會議模式
新西蘭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又稱家庭群體會議,是世界上以恢復為目的適用于未成年人的會議項目代表。家庭群體會議有兩個顯著特征:一是作為法院的替代(只針對未被逮捕的年輕人);二是作為量刑前向法官提供建議的機制。[5]這就意味著家庭群體會議是警察將未被逮捕的未成年罪犯交給法院的前置程序。參與家庭群體會議的成員主要有年輕人、他們的家庭成員、家庭群體和他們邀請的人(如朋友、年輕人俱樂部組織者)、被害人或被害人的代表、被害人的支持人員、警察和年輕人的律師,并且有專門的未成年人司法協調人員負責協調家庭群體會議的相關事務。協調人員主要是經過培訓的社會工作者,由兒童、年輕人和家庭服務部提供并受其監督,是由所有參與會議的人同意作出的決定,或者被未成年法官接受。如果參與者不能作出一致的結果決定或建議,在警察提交的會議中就不得不決定是否或如何繼續,在法院提交的(逮捕的)會議中法官就不得不決定適當的刑罰。
四、我國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構建
根據以上分析,筆者主張建立一種專門模式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將其與現在混合式模式相區分,將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納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中,具體建構如下:
(一)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前
1.適用的階段。根據刑事訴訟法和司法解釋的規定,刑事和解可在訴訟的任何一個階段進行,筆者認為,刑事和解在偵查階段應該慎用。因為在偵查階段,犯罪事實尚未查清,證據尚在收集過程中,如果過早適用刑事和解會妨礙偵查機關偵破案件,打擊偵查人員的積極性,不利于保護國家、社會及個人的合法權益。如果需要適用,應經過檢察機關的批準,否則不得使用。在審查起訴階段和審判階段應積極適用刑事和解,因為在此階段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訴訟各方也基本了解案情,能夠心平氣和地聽取對方的意見,這無疑為刑事和解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平臺。此外,在這一階段通過刑事和解結案,有利于節約司法資源,降低訴訟成本,減輕司法工作人員的壓力,提高工作效率。
2.適用范圍。本文開篇已經說過,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范圍與司法實踐中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適用范圍存在偏差,因而,應當放寬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適用范圍。首先,應取消“民間糾紛引發”的限制;其次,犯罪類型拓展到《刑法》分則第六章,未成年人經常所犯的尋釁滋事罪、聚眾斗毆罪等應加入其中。
(二)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中
1.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主持者。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由公安機關主持和制作和解協議,對于這里的“主持”應如何理解?是作為中立的第三方負責監督與指導?還是由公權力機關積極引導雙方當事人達成刑事和解協議?筆者認為,公權力機關的角色定位是監督者,因為公權力的性質,不宜干涉刑事和解的具體內容,否則會違背刑事和解的自愿性這一前提。我國一直忽視社會第三方在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中的作用,認為社會第三方更具有中立性,能夠取得雙方當事人的信任。這里的社會第三方可以多元化,如社工、教師、共青團、除本案以外的律師等熱心于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的成年人。具體來說應具備以下條件:(1)年齡在18周歲以上,中年人優先;(2)具備一定的社會閱歷;(3)具有良好的溝通能力、法律相關知識、心理學和教育學的知識。此外,要對這些人員進行培訓上崗,關于這一點,我國可以借鑒奧地利的辦法,注重協調人員的專業性以及獨立處理案件的能力。
2.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方式。筆者主張以訴說形式展開,首先,由加害人向被害人闡明自己的犯罪動機,要被害人了解自己的心路歷程,同時由被害人向加害人訴說自己所遭受的損害,使加害方知道自己的行為給他人帶來的負擔,以及自己應負的刑事責任;其次,由雙方當事人的代理人針對和解協議的詳情展開討論。在這一過程中,協調人要負責監督,以及在雙方當事人出現爭執時負責協調解決。
3.豐富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內容。為了改變人們長久以來“賠錢減刑”的觀念,應豐富刑事和解協議的內容,可以以社區服務、公益勞動代替經濟賠償,尤其是針對家庭比較困難的未成年罪犯,更適用這些方法促使其改過自新。刑事和解與“花錢買刑”最根本的界限就在于加害人是否真誠悔罪、賠禮道歉,獲得被害人的諒解,經濟賠償是真誠悔罪的應有之義,但如果行為人確無賠付能力,賠償替代也無不可。[6]
(三)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后
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后,協調人將協議交給辦案的檢察官或法官,檢察官或法官審查當事人的自愿性以及和解協議的效力,并作出相關的決定。同時,公權力機關擔當監督者的角色,積極監督和解協議的履行情況。在刑罰的執行過程中,如果未成年罪犯取得被害人的諒解,并且服刑期間表現良好,有悔改表現,可以作為減刑、假釋的條件。
[1]黃太云.刑事訴訟法釋義[J].人民檢察,2012(8).
[2]蘇鏡祥,馬靜華.論我國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之轉型—基于實踐的理論分析[J].當代法學,2013(4).
[3][英]格里·約翰斯通.恢復性司法:理念、價值與爭議[M].郝方昉,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1.
[4]何 杰.兼顧被害人利益,促進社會和諧——兼論刑事和解制度[J].昆明師范高等專科學院學報,2006(2).
[5]徐美君.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特別程序研究——基于實證和比較的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6]顧海寧.新刑訴法視角下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理念的考略[J].信陽農業高等專科學院學報,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