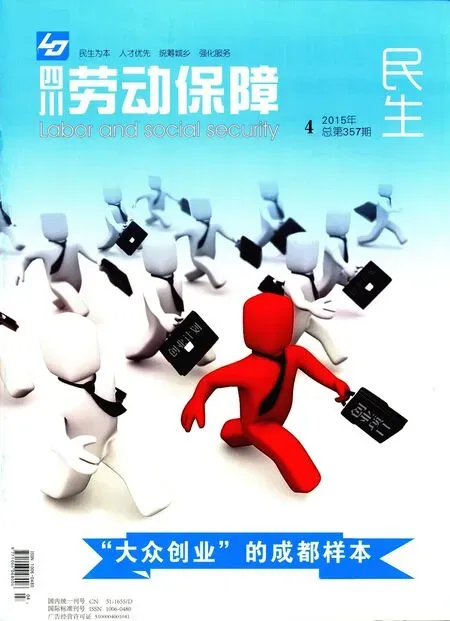微評
農民工工資何時讓總理放心
據新華社報道,前不久,李克強總理在長春市南部新城綜合交通樞紐工程考察時表示,“用工量大的企業跟勞動力富余地方的勞務公司合作,這個辦法好。農民工不遠萬里外出打工很不容易,一定要確保他們按時領到工資。”
總理過問農民工工資發放情況,顯露了體察民情的拳拳心意。但消解農民工被欠薪、討薪難的困境,顯然不能光指望總理過問,而得依賴法律撐腰。今年1月,最高法、人社部等四部門聯合下發《關于加強涉嫌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犯罪案件查處銜接工作的通知》,要求進一步完善勞動保障監察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工作機制。究其意圖,就在于強化落實,這也讓農民工討薪難迎來再破題的契機。
中共中央、國務院日前印發《關于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意見》,提到要健全工資支付監控、工資保證金和欠薪應急周轉金制度,探索建立欠薪保障金制度,落實清償欠薪的施工總承包企業負責制,保障職工特別是農民工按時足額領到工資報酬。
說起來,破解農民工討薪難的法律屏障、制度支點,要做到無罅縫并不容易,但慮及其民生關切度,必須盡快補全現有的短板。尤其是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開局之年的語境中,更要從法律補漏著手,夯實法治基底,為化解討薪難接上“法治”的接口。
央視
讓企業實行年金制有多難
職業年金的好處顯而易見,但目前覆蓋的只是機關事業單位。當然,企業也可繳企業年金,但它只是一種可能性,不像職業年金是強制繳納的。員工能否享受這一福利,有賴于企業的實力和老板的善意。人社部數據顯示,截至2014 年第三季度,全國參加企業年金的職工人數為2200多萬人,不到全國城鎮就業人員的6%。
職業年金制度是國民所需要的養老保障。問題在于,企業年金不能強制,有些企業生存都困難,多一項強制,說不定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提高企業年金普及率,現實的做法是為企業創造條件,鼓勵企業改善員工養老待遇,讓企業有條件有意愿實行年金制度。
中國企業負擔過重是一個老話題。社保就是一個明顯例子。今年全國兩會,有人大代表指出:絕大部分省市企業的繳納比例都在工資總額的40%以上,有的地區達到50%。
中國企業負擔過重,還體現在社保外多個方面。比如我國增值稅稅率為17%,還要承擔大量的非稅收入,如政府性基金、行政收費等。
如何加強頂層設計,從根源上減輕企業負擔,讓企業有更多自主空間,成為經濟體制改革必須破解的題。只有企業負擔減輕了,企業以輕裝上陣獲得更好的發展,企業員工福利提高才有基礎。
中國青年報 謝昱航
官員離職并非壞事
近日,關于公務員離職潮的新聞引起了廣泛關注,又一次將官員階層分化問題納入輿論場的核心。綜合各方輿論,有兩點一致之處:一是認為僅僅靠一組數據就斷言當前公務員離職成“潮”未免顯得草率;二是將公務員離職與反腐敗聯系在一起分析。在充分肯定這兩點結論的同時,顯然還有進一步展開討論的必要。
無論是數量上還是比例上,官員離職都并非成“潮”。正如有評論指出,做離職潮的解讀,只是反映了公眾對反腐的過高期許。當下的強力反腐可以理解為這一副產品的處理方式,的確給一些公務員帶來一定的外部壓力,構成離職的重要動因。但應該看到,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官員群體的分化動機一直是多元的而非單一,反腐壓力只不過在官員離職動機中添加了一個新的因素;另一方面,無論動機如何多元,官員離職首先出于收益比較的考慮。換言之,利益因素應是考察官員離職動機的首要因素。
無論如何,官員離職都是一件好事,是一個進步的現象。因為這種變化預示著,官員這個職業正一步一步地靠近社會結構中和大眾心目中最為合理的位置。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吳波
中國勞動力已不足是個偽命題
據報道,在連續4 年公布我國50歲以上農民工的統計數據后,國家統計局突然暫停公開這一數據,這也將高齡農民工的境遇置于公共視野中。有專家揣測,2014 年我國高齡農民工總量或已突破4000萬。
從高齡農民工的增多,似乎可印證一個常見的說法:中國的“人口紅利”正在消失。從數據上看是這樣的:全國的農民工總量,從2009 年的22978 萬人到2014 年的27395 萬人……在這6 年中,農民工總量以平均3.59%的速度逐年增長。與此同時,50 歲以上農民工從2009 年2803 萬人到2012 年的3969萬人,其絕對數量以12.32%的速度,占農民工總數的比重以7.39%的速度保持增長。
我們該在社會政策上做出什么反思呢?其一,如今社會上流傳甚廣的“我國勞動力已然不足”并非事實真相,若說農民工數量在減少那更不是事實,近年來東部沿海地區的“民工荒”,其實是地方政府的人口政策和就業政策造成的。其二,如果與在家抱孫子、跳廣場舞的城市老人相比,50歲以上的大齡農民工還在干著重體力活掙錢,他們之間差的就是“國民待遇”,是社會保障。而這種情景還在繼續擴散。其三,我國年輕勞動力去哪里了?尤其是80 后、90 后的農民工,數以億計的他們如今在哪個領域就業,我們產業結構調整是否也該把這些因素考慮進去?值得思考。
新京報 唐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