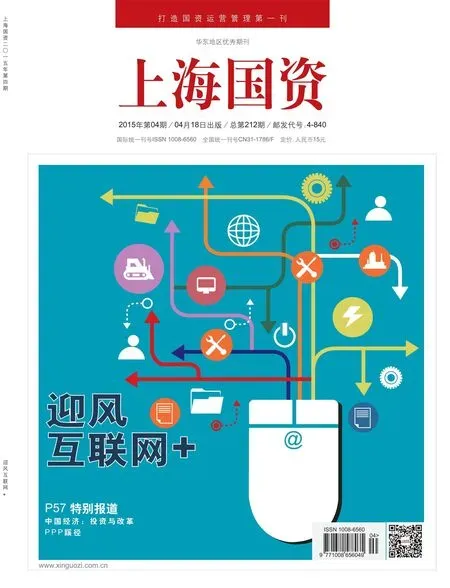“一帶一路”重構全球治理結構
文‖盧鋒
“一帶一路”重構全球治理結構
文‖盧鋒
中國應當一方面在東邊應對美國“重回亞太”戰略,另一方面采取“西進”戰略,作為中國地緣戰略再平衡路徑
今年“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第三部分談到了“把改革開放扎實推向縱深”。報告指出,構建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合作建設。并在第四部分“協調推動經濟穩定增長和結構優化”中指出,把“一帶一路”建設與區域開發開放結合起來,加強新亞歐大陸橋、陸海口岸支點建設。
李克強總理著重強調“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性,此項戰略既與長遠的改革戰略有關又與具體的調結構穩增長的舉措有關。
由于“兩會”的帶動,目前全國31個省市區都積極表示參與“一帶一路”規劃實施,這一戰略有望成為貫穿今年國家和地方工作的一條主線。同時,還應當關注另一件與之相關的事件,即亞投行的組建。這可以理解成配套“一帶一路”所做的一種機制性、機構性的創新和安排。兩者的結合,意味著中國崛起將重構全球治理結構。
改造與重構
“一帶一路”是指中國與亞太以至東北非及歐洲廣大國家和地區互聯互通、互利合作的廣泛概念。“一帶”即中國與經過中亞直至歐洲的古代“絲綢之路”所及區域經濟合作。“一路”即“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涵蓋中國與東南亞、到印度洋以至地中海區域合作。“一帶一路”輻射范圍涵蓋東盟、南亞、西亞、中亞、北非和歐洲,總人口約44億,經濟總量21萬億美元,分別占全球63%和29%。
如果中國能夠通過這一戰略幫助相對落后的地區經濟取得顯著的發展,那么這將是一件具有全球意義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中國借此機會設立了配套的融資機構,即“一行一基”(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的成立。實施互聯互通、基礎設施投資為要旨的“一帶一路”戰略,需要大量資金投入,需要投融資機構支持。
亞投行是政府間性質亞洲區域多邊開發機構,總部設在北京,法定資本1000億美元,中國出資500億美元。截至2015年4月1日,加入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的國家已經增加到31個,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與日本在此事上態度較為謹慎和保守。
絲路基金于2014年12月29日正式注冊,要求“按照市場化、國際化、專業化的原則”組建運作。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資源開發、產業合作和金融合作等與互聯互通有關項目提供融資服務。基金以中長期股權投資為主,類似世界銀行“國際金融公司”(IFC),比一般PE期限更長,或能達15年甚至更長。股權投資基金也可與別的融資模式相配合。例如有一定股本比例后可適當貸款。
盡管這些機構的設立是為了輔助“一帶一路”戰略,但是其同時具有獨立的改善全球治理結構的含義,正因此引起了美國的高度關注,也變成了國際關系的里程碑事件。
美國的保守態度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如果建立了亞投行,客觀上是對國際現有的融資結構的一種補充,但構成了與它相競爭的格局。這是在二戰后國際經濟關系當中非常罕見的現象,特別是與中國相關。這折射出一個客觀的事件,不僅反映出了中國決策層規劃的重要影響力,也反映了中國和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將會改造和重構全球治理結構。
水到渠成
“一帶一路”戰略的學術背景是北大學者提出中國應當一方面在東邊應對美國“重回亞太”戰略,另一方面采取“西進”戰略,作為中國地緣戰略再平衡路徑,加快建設中國主導的“新絲綢之路”。
2013年4月的博鰲論壇上,習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中國將加快同周邊地區的互聯互通建設,積極探討搭建地區性融資平臺,促進區域內經濟融合,提高地區競爭力。”
2013年9月習近平主席訪問哈薩克斯坦首提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設想。
同年10月習近平主席出席APEC領導人會議提出中國愿同東盟國家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同月習主席與李克強總理先后出訪東南亞,提出籌建亞投行倡議。
之后兩年間,“一帶一路”戰略部署及亞投行的籌建迅速開展,2015年2月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在同月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九次會議上習近平主席再一次強調了戰略的重要性及“一行一基”(亞投行和絲路基金)配套的意義。
“一帶一路”戰略具有五大特點。首先是把互利共贏與互聯互通結合起來,寓和平發展理念于“一帶一路”戰略中。第二,把頂層設計與基層實踐結合起來,使得規劃實施具有廣泛切實經驗基礎。中國企業過去十多年中已經在“走出去”上取得了很多進展,所以在此基礎上將原有的實踐進行提煉,并與國家層面其它目標相結合,體現在了新的戰略中。第三,把國內發展與經濟外交相結合,成功調動其國內外各方面參與積極性。第四,是把設計創新與高效執行相結合,展現中國決策層設計、布局、執行力。現在中國決策層在新戰略的推動上,設計和執行環環相扣加速推進,高調地展示了中國決策布局的速度。第五,是把合作建設與機制創新結合起來,為改善全球經濟治理結構務實探索。這一點是亞投行的作用。
那么為何僅僅只用兩年中國在新戰略的推行上就能夠如此卓有成效?中國目前經濟發展階段特有的生產技術能力與宏觀經濟兩方面條件具有關鍵作用。
在生產技術能力優勢條件方面,中國制造+中國建造+中國創造能力巨大。2010年,以美元衡量中國工業制造規模已第一次超過美國,而且中國的工業生產結構與大規模開發階段需求特定契合度更高。
在中國建造上,中國對外承包工程額從世紀初不到100億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1400多億美元。承包工程年末在外員工數已達30多萬人。在中國創造方面,在高鐵、大型設備、工程建造等領域,技術集成創造、產品創造、標準創造能力正在形成和發展。
另一方面,宏觀經濟優勢顯示為中國儲蓄+中國投資+中國儲備。中國總儲蓄規模已達美國和歐盟的總和;中國投資的巨量,也支持戰略的推行;而中國巨大的外匯儲備提供了現行國際貨幣體制之下的國際支付流動性,因此上述兩個條件使得國家的新戰略水到渠成。
提振全球經濟
“一帶一路”的戰略影響和意義主要有兩方面。
一方面的影響為創造經濟增長新動力。目前全球經濟仍處于早先失衡調整過程中,G20調整框架通過宏觀政策協調尋求“強勁平衡可持續”目標效果欠佳,“一帶一路”有助于培育新增長點提振全球經濟。就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要致富先修路,基礎設施是制約增長的關鍵瓶頸。即便是發達國家,也需要更新基礎設施尋求持續增長。對于中國而言,實施新戰略,有助于提升利用中國比較優勢產能,有助于擴大各類配套投資,有助于擴大中國出口(經驗研究結果顯示,控制住各國經濟規模、距離、貿易壁壘等因素后,中國對特定國家ODI增加能夠顯著增加向該國的出口),有助于目前宏觀經濟穩增長目標,特別對于中國的穩增長和走出相對的經濟下行壓力將有益處。
另一方面的影響是改進全球治理新途徑。目前全球治理結構與全球化深化要求不匹配,改進完善治理結構是推進全球化的必要功課。守成大國不積極,美國IMF份額調整拖延策略是明顯的例證。新興國家需主動積極作為,推動全球治理結構調整。“一帶一路”規劃以投資建設需要為背景創建亞投行等機構,客觀具有調整改善全球治理結構含義。
但這其中亦存在風險。一方面是大國關系的處理,如何處理與美國、俄羅斯、印度之間的大國關系。另一方面則是同沿路小國關系的處理,在具體投資項目層面則會遇到注入大規模投資開發產生的環境影響、外國政策與政局變化風險、大型國企外部形象等風險。
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的崛起一定意味著全球形勢的變化,“一帶一路”就是這一邏輯的現實展開。雖然存在困難風險,但這一戰略如能很好實施,將有望推進中外共同發展、改善國際治理結構、中國大國成長歷練等方面彰顯成就。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