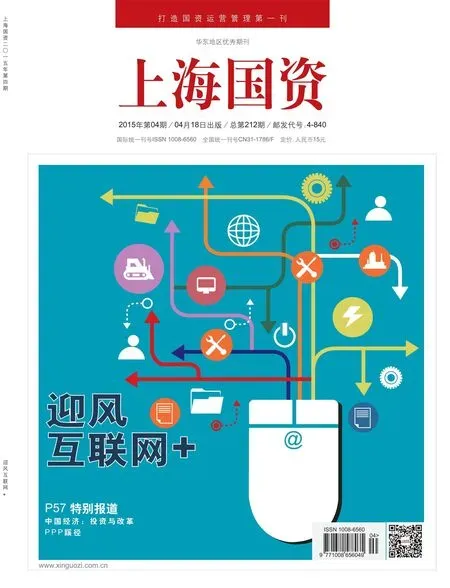迎風互聯網+
文‖上海國資記者 左沈怡
迎風互聯網+
文‖上海國資記者 左沈怡

上海日立電器鈑金工場的三條生產線已基本實現無人化生產,自動化機器人14臺
從內生的、封閉的自主創新到聯盟式、合作式的協同創新,再到無邊界、平臺型的開放式創新是一個技術發展的規律,也是互聯網時代的特征
顛覆的時代已經到來,信息革命帶來的裂變正破壞著各種固有模式。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兩會”期間的政府報告中首提“互聯網+”。他要求,制定“互聯網+”行動計劃,推動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與現代制造業結合。促進電子商務、工業互聯網和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引導互聯網企業拓展國際市場。
“站在‘互聯網+’的風口上順勢而為,會使中國經濟飛起來。”總理在會后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
一夜間,“互聯網+”連同“大眾創新、萬眾創業”,一起成為了舉國最熱的詞。
這是一個加速迭代的時代。新興企業的生命周期正在被無限縮短,信息高速公路帶來了量級提升。曾經代表著創新和顛覆的谷歌、蘋果已經成為傳統企業。Airbnb,Uber,才是現今最火熱的企業,它們分別顛覆了酒店旅游業和出租車行業。協同共享的經濟,已經被認為是未來社會的縮影。
在美國的工業互聯網與德國的工業4.0之間,中國提出了自己的“互聯網+”行動。中國政府希望通過互聯網技術帶來的機遇,推動中國經濟走出下行壓力。對于企業,亦是一個可貴的歷史機遇。
逆向倒逼產業
不管企業是否已經準備好,在互聯網時代,新興網絡企業正在從產業鏈下游端向上蠶食。傳統制造業面臨倒逼。

圖1:產業互聯網化的“逆向”過程

現代設計集團通過BIM技術完成的項目近百項,例如上海市BIM示范項目瑞金醫院質子中心、世博會博物館項目等
中國科學院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呂本富認為,“互聯網+”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是一種行動,而不是一個名詞。目的是要改造制造業,進而升級中國經濟,與新常態相呼應。
在阿里研究院的一份《互聯網+》的報告中,把這一概念定義為,以互聯網為主的一整套信息技術(包括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技術等)在經濟、社會生活各部門的擴散、應用過程。“互聯網+”的本質是傳統產業的在線化、數據化。只有商品、人和交易行為遷移到互聯網上,才能實現“在線化”;只有“在線”才能形成“活的”數據,隨時被調用和挖掘。在線化的數據流動性最強,不會像以往一樣僅僅封閉在某個部門或企業內部。在線數據隨時可以在產業上下游、協作主體之間以最低的成本流動和交換。數據只有流動起來,其價值才得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
“互聯網+”的過程也是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過去十年,這一過程呈現“逆向”互聯網化的過程。在企業價值鏈層面上,表現為一個個環節的互聯網化:從消費者在線開始,到廣告營銷、零售、到批發和分銷、再到生產制造,一直追溯到上游的原材料和生產裝備。從產業層面看,表現為一個個產業的互聯網化:從廣告傳媒業、零售業、到批發市場,再到生產制造和原材料。從另一個角度觀察,“互聯網+”是從C端(個人客戶端)到B端(企業客戶端),從小B再到大B的過程,產業越來越重。在這個過程中,作為生產性服務業的物流、金融業也跟著出現互聯網化的趨勢。在“互聯網+”逆向倒逼的過程中,各個環節互聯網化的比重也是依次遞減。
阿里研究院認為,最先被互聯網帶動的是消費者,其次是零售環節的互聯網化,再往上是批發和分銷環節的互聯網化。這里包括傳統的B2B網站紛紛由信息平臺向交易平臺轉型,推動在線批發,以及傳統企業的大量開展的網絡分銷業務。
再往上倒逼就是生產制造環節,主要表現兩個方面:一是個性化需求倒逼生產制造柔性化加速,比如大規模個性化定制;二是需求端、零售端與制造業的在線緊密連接。這導致制造業也出現在線化、數據化的趨勢。
小而美
互聯網技術的革命已經昭示出社會經濟結構正在發生變化,這種變化正滲透到各個產業。這種變化來自于三方面:一是新信息基礎設施的形成;二是對數據資源的松綁;三是基于前兩方面而引發的分工形態變革。傳統的生產要素已經開始重構。
互聯網時代依賴的新基礎設施,可以概括為“云、網、端”三部分。
“云”是指云計算、大數據基礎設施。生產率的進一步提升、商業模式的創新,都有賴于對數據的利用能力,而云計算、大數據基礎設施像水電一樣為用戶便捷、低成本地使用計算資源打開方便之門。
“網”不僅包括原有的“互聯網”,還拓展到“物聯網”領域,網絡承載能力不斷得到提高、新增價值持續得到挖掘。
“端”則是用戶直接接觸的個人電腦、移動設備、可穿戴設備、傳感器,乃至軟件形式存在的應用。“端”是數據的來源、也是服務提供的界面。
新信息基礎設施正疊加于原有農業基礎設施(土地、水利設施等)、工業基礎設施(交通、能源等)之上,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
“大數據”的提出與其說是對于數據處理能力描述的再包裝,不如說是一種數據已經成為獨立生產要素的信號。歷經近半個世紀的信息化過程,信息技術的超常規速度發展,促成了數據量和處理能力的爆炸性增長,盡管處理的手段尚未有極大的突破,但是其重要性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基于信息基礎設施的完善和數據處理能力的提升,社會分工形態也出現了變革。
以企業為中心的產銷格局,轉變為以消費者為中心的全新格局。企業以客戶為導向、以需求為核心的經營策略迫使企業組織形式相應改變。新型的分工協同形式開始涌現。
阿里研究院認為,未來企業“小而美”將成為常態。由于節約了信息成本,交易費用降低令外包等方式更為便捷,企業不必維持龐大臃腫的組織結構,低效、冗余的價值鏈環節將消亡,而新的高效率價值環節興起,組織的邊界收縮,小企業會成為主流。
這種觀點與杰里米·里夫金在《零成本社會中》所述的未來社會的生產模式不謀而合。他亦認為,互聯網的廣泛滲透會使生產與消費更加融合,信息作為一種柔性資源,縮短了迂回、低效的生產鏈條,促進了C2B方式的興起,生產與消費將更加融合。
社會的協同將無處不在。技術手段的提升、數據開放和流動的加速,以及相應帶來的生產流程和組織變革,生產樣式已經從“工業經濟”的典型線性控制,轉變為“信息經濟”的實時協同。
模式之爭
很顯然,消費端的商業模式早已被互聯網所顛覆,網絡的滲透正在向制造端蔓延。可以說,互聯網企業所具有的輕便的“小而美”的結構對于零售業更易進入,而對于體量龐大的傳統制造業,當如何影響?
是通過工廠深化智能制造的德國的工業4.0模式,還是建立美國的工業互聯網模式?
德國模式偏重利用物聯網實現自下而上的產業鏈聯通,重點放在制造上;美國模式則是把互聯網技術用于工業系統中,并加速從最上端的平臺領域向下端“物理”層滲透。
中國工程院院士郭重慶表示,德國工業4.0并不適合中國,德國經濟中存在許多中小企業、家族企業,這與中國的勞力優勢的國情不同。由于德國高昂的勞動力成本和制造技術的積累,因此智能制造成為其首推。他認為,“互聯網+”的思維更適合中國,在這場工業互聯網變革中應以“眾人拾柴火焰高”的互聯網思維,聚集“全球大腦”與“萬眾智慧”為特征,以開源平臺和眾包兩個平臺釋放全球智慧,促進創新、創業。
寶信軟件資深技術總監何浩然亦認為,德國工業以離散制造業為主,其工業4.0的模式適合小企業。而在中國,大型制造業的轉型需要靠自己探索方式。
郭重慶指出,中國消費互聯網企業基本上是復制美國互聯網企業的商業模式,背靠中國的巨大市場和網絡規模,從而獲得成功。中國工業互聯網完全可以跨越美國搶先一步,“因為我們有偌大的制造業生產能力和消費市場,工業互聯網可為中國制造業的產業升級依靠社會力量創造絕好的平臺和機遇,時間和空間也恰到好處。”
不過中國的制造業似乎尚未有此意識。制造業企業從工業化時代的縱向供應鏈整合,到信息化時代的橫向價值鏈整合,再到互聯網時代的平臺型生態鏈整合,而中國制造業企業仍處于第一種狀態。
“太以自我為中心,太以技術為中心,太以產品為中心,而不是以客戶、以服務和以為客戶創造價值為中心。在工業互聯網時代,勢必會經歷一批傳統制造業企業倒閉浪潮。”郭重慶認為,由于科技資源的配置已全球化,一個企業的競爭力不僅取決于其內生的科技資源,同時取決于其整合社會化和國際化資源的能力。“一個企業,甚至一個國家很難在一個產品的整個價值鏈上都占據優勢,堅守自己增值最大的一塊,且孤立地開發產品的時代已成為過去,這已經成為世界制造業的一種常態”。
從內生的、封閉的自主創新到聯盟式、合作式的協同創新,再到無邊界、平臺型的開放式創新是一個技術發展的規律,也是互聯網時代的特征。
產業互聯網機遇
在中國,消費互聯網的寡頭已經由BAT占據,而更廣闊的產業互聯網尚處于混沌階段。
復旦大學電子商務中心研究員黃岳認為,產業互聯網還未形成寡頭壟斷,因此就在這兩年,產業互聯網行業就會逐漸有寡頭崛起。產業互聯網不同于消費電商,產業是一個更為廣闊的領域。由于不同產業之間的差異化程度大,行業壁壘高,因此在每一個產業的垂直領域,都可能產生一個淘寶的規模。不過,產業互聯網的門檻較高,首先要了解行業,包括行業規則、業務模式。另外還需要有政府相應的政策保障,特別是產業互聯網中所涉及的海量工業數據,需要政府數據庫的開放。第三,政府的扶植也是產業互聯網發展的必要條件。最后,還需要通過產學研結合。
產業平臺的搭建,無疑大型企業更具優勢。在現階段,中國的制造企業尚不具備平臺整合能力,能夠腳踏實地做的,更多的是從消費服務端開始融入互聯網。
以汽車領域為例,“互聯網+”更可行的是將互聯網作為一種工具鑲嵌入整車制造商。上汽集團與阿里巴巴聯合開發“互聯網汽車”就是一種方式。通過開發自己的應用平臺,轉型服務端,來提升其核心競爭力。“做一個比喻,把汽車看作是手機。蘋果的成功在于其有自己的應用系統和應用平臺,這也是為何諾基亞失敗的原因。”易觀國際汽車行業研究員潘葳告訴記者。他認為,汽車這樣的大型制造業被互聯網顛覆的機率很小,但如果不進行自我迭代,則會被同業打敗,上汽集團已是中國最早動身的汽車企業。
這種改變,也發生在了上海其他產業企業中。屬于工程設計業的現代設計集團利用BIM技術實現綠色建筑智造;上海電氣集團正著手實現智能工廠;儀電集團近日亦與羅蘭貝格咨詢公司簽約共建智慧城市;久事集團通過信息化及物聯網的搭建推動城市智慧公交。其他的服務型企業中,電商平臺亦在不斷升級中,如錦江集團的酒店旅游類電子商務平臺,百聯集團的網絡購物平臺,上藥集團的藥類分銷平臺等。
互聯網帶來的變革正打破過去的平衡與秩序,在新秩序的建立前,必然百舸爭游。對于企業而言,在對的時機,以正確的姿勢,迎風起飛,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