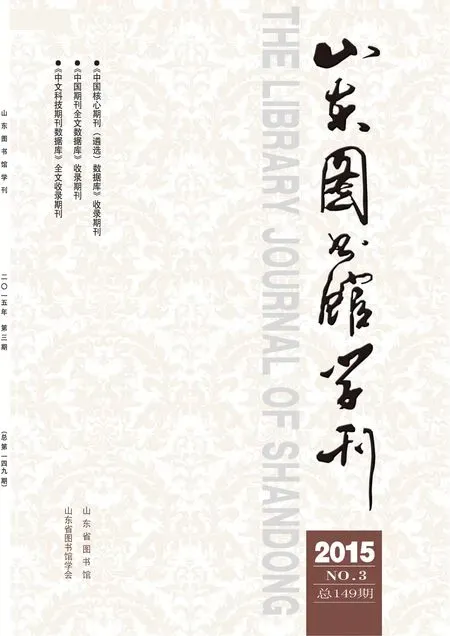為求知治學而讀書藏書:時永樂的《墨香書影》
馬紅亞
(石家莊市信息管理學校圖書館,河北石家莊050090)
為求知治學而讀書藏書:時永樂的《墨香書影》
馬紅亞
(石家莊市信息管理學校圖書館,河北石家莊050090)
河北大學文學院教授時永樂先生(1957—2014)的《墨香書影》正文分為“知人論學”“書林嘗臠”兩輯,并附錄有兩篇“代編后記”。題為《奮斗·付出·收獲》一文是書作者的“代自序”,是其獻身于求知治學、教書育人和讀書藏書活動的簡明自傳。
本書作者生前系河北大學文學院文獻學專業的研究生導師,古籍整理和校勘考證是他畢生傾注心力的領域。針對當前國學復興與學界急功近利,學者們文獻學功底欠缺和文獻學專業招生受冷落、畢業生分配難等現狀,以及“近五十年走上文壇的學人中,大師,絕無蔑有;大學者即大家,鳳毛麟角;而學者即小家,則車載斗量”(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魯國堯先生語)之實情,時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學術視野狹窄,缺少文獻學常識”,正是造成這種情況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在《應該學點兒目錄學》一文中寫道:“目錄學是讀書的向導。我國古籍眾多,且新書每年以十幾萬種的速度增長,一人傾畢生精力不能讀其萬一,加之良莠不齊,故讀書必須善于選擇。”“目錄之學,讀書入門之學也。當今報刊上,一些著名學者的推薦、導讀書目,開出的少而精,青年學子應該加以關注、利用。”
針對近年來我國古籍整理類圖書數量較之以前有了大幅度提高但精品卻少的現狀,他在《古籍整理重量更重質》中呼吁,國家有關部門要完善出版管理制度,重視文獻學人才的培養,因為文獻學是國學的基礎。他在《國學教育與研究應該重視文獻學》中擔憂說:“這種狀況若不改變,再過若干年,恐怕將少有人知道何謂版本、目錄、校勘及辨偽,那時的‘科研成果’,恐怕更是傷痕累累,錯漏百出,這將不僅是文獻學的悲哀,恐怕也是整個國學的悲哀!”
埋頭學問的同時,時先生始終把教書育人的使命與國情和社會聯系在一起。他不是孤立地鉆研學問,而是把歷史與現實結合,撫古思今,是為了借鑒前人的經驗和教訓,創新發展,做好當下。《談“仕而優則學”》《“人有病,天知否”》《葉圣陶編〈十三經索引〉給當代編輯的啟示》《孫犁論古籍與古籍整理》等篇章,無不體現了先生作為人文學者,在維護學術尊嚴的同時,亦密切關注國家的興衰和人事的成敗,對踏實向學的弟子們的深切關愛,舐犢之情躍然紙上。
《論衡詞典》(時永樂、王景明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是兩位先生耗時六年,潛心鉆研整理而成的心血之作。《墨香書影》第二輯中所收錄的《〈論衡詞典〉自序》《〈論衡〉校讀札記》《〈論衡〉校注史上的突破性成果——〈論衡校箋〉評介》以及《〈訓詁資料纂輯〉的創新價值》等篇目,體現了時先生獨特的治學門徑和深厚的文獻功力。
時先生認為,教師是一項嚴肅、神圣的職業,育人來不得半點疏忽。他的主攻方向是文獻學,書籍是他的主要研究對象。他所講授的古籍整理、古典文獻學、社科文獻檢索、古代漢語等課程,無不需要大量文獻資料。而圖書館的工具書不全,進書速度與數量遠不能滿足教學之需。為了能利用第一手資料,使授課與最新學術進展同步,衣食之外,時先生所有的收入幾乎全部用于購書。
其中“一個人總是要有一點精神的……”,作為當代不可多得的一位讀書治學型藏書家。他認為,“教學與科研是學術而不是權術,一個真正的學者要鉆研而不要鉆營。”為此,他敬畏學術,對待工作嚴謹而勤奮。他努力絕緣于學術上的“二手資料”。譬如《現代漢語詞典》出了五個版本,他購買了五次,相應地講稿也重寫了五次;《辭海》修訂了六次,他購置了六本,講稿也隨之重寫了六次。因此,站在講臺上的他底氣十足,授課時旁征博引,有根有據,糾正了不少以訛傳訛的“定說”,其治學精神和學者風范,影響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后學。
河北大學教授孫微先生在本書一篇“代編后記”里說:
時永樂先生是位履道堅貞的學者,一生淡泊名利,唯嗜藏書、讀書,尤喜古籍版本之學,家藏典籍50架,多至數萬冊,自言“未嘗一日廢書”,居恒苦讀,靜心揣摩,徜徉書海,神交古人,自得其樂。先生治學極為嚴謹認真,對文獻的檢核更是一絲不茍,但他為人卻極為寬厚隨和,溫潤儒雅,有循循長者之風,又古道熱腸,時刻關心著他周圍的學生、同事、朋友的各種瑣事,盡量為他們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幫助。
他認為,時先生的讀書札記等隨筆文字中,“有訪書的喜悅與艱辛,有對文獻學研究的展望,也有對國學學科的冷靜思考,有對前賢長者的真摯追憶,內容涉及先生幾十年治學路程上的方方面面,這些文字對我們從不同角度了解時永樂先生的學術人生都是極為有益的補充……當可管窺時永樂先生之性情人品,及其聚書讀書、治學問道之曲折歷程,進而了解時先生堅忍不拔之求道精神。”
作為一個終身以書為友的讀書人、藏書家,時先生的訪書買書經歷也非常被人關注。用他自己的話說,他買書就像妻子買菜,每天都往家里提溜。《得不償失》《價格不菲的驢肉火燒》《尋覓20余年的兩宜軒本〈說文解字注〉》和為買一本自己喜歡的書一家人吃了一周的白菜、借錢買《清代版本圖錄》及賣書的經歷等,讀來令人心酸落淚。他的碩士研究生弟子許超杰在“代編后記”中的《書人已逝,墨香永馨——記先師時永樂教授之讀書、購書與著書》一文對此多有披載。
我是在清明節后,收到現在華東師范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許超杰校友贈寄本書的。閱后方知,該書系其弟子們拾掇散篇,并在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教授徐雁和河北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杜恩龍的熱忱幫助下,納入“全民閱讀書香文叢”之一后結集出版的。讓時先生的學術思想和人事德行昭示來者,讓這縷散發著清輝的學術薪火得以傳承,大概這便是這部具有文獻價值和紀念意義的學術隨筆集問世的意義罷!
馬紅亞,館員,現就職于石家莊市信息管理學校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