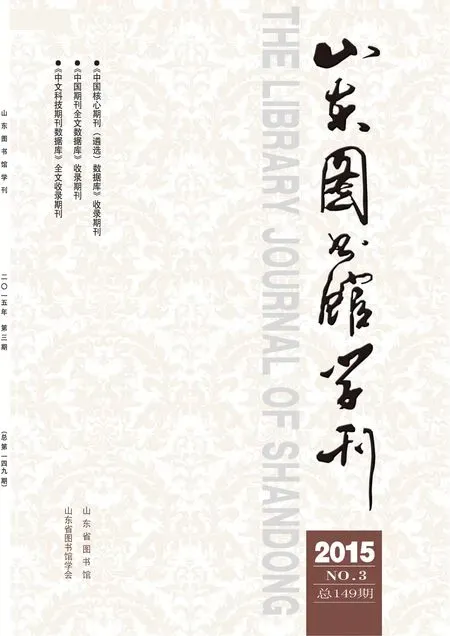“桐城文脈”的過去與現在
李國春
(桐城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安徽桐城231400)
·故紙滄桑·
“桐城文脈”的過去與現在
李國春
(桐城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安徽桐城231400)
看一個地方文化繁榮發展,主要視其地域人文有多少積淀、文教風氣有無形成。一邑文化能傳承光大,表現在人的方面,須代有才俊,呈現在世風上,則無外乎倡導教化。而自古至今,一地文化賡續不斷、人文血脈綿長不竭,唯有書籍方可承此重任。
桐城之人文活動有史籍可以稽考的不會早于晚周。但是直到唐代至德年間桐城稱縣,文明始倡,此乃桐地文風郁聚之初,洎宋、明初開始勃發,迨明、清則大昌。
明中葉以還,桐城無論甲族小戶,都不互攀誰家財富多寡,卻以本族有無讀書上進之子弟為榮辱、有無官刊家刻書籍為顯隱。清嘉道年間,桐城梁伴梅先生有齋曰“僅可齋”。有人問:何謂“可?”梁先生曰:我少時讀書,不慕做官,開卷有獲以求明理而已,不求顯貴;少時即貧乏,靠耕耨掙得溫飽而已,無有奢欲;少時無所定居,現今能構書室數間,只求得適意而已,不慕華麗。這種人生境界,代表了當時讀書人的一種基本價值取向。
即使是官宦之家,其宅第也決無富麗堂皇、高門敞軒之隆盛,如桐城名門大族張姚馬左、方吳葉盛諸姓人家,其房舍庭園,與江南、三晉富戶大宅相比也黯然失色。值得顯耀門庭的是家有幾多童子學業優良。街巷里弄、竹蘺茅舍,隔牖可聞瑯瑯書聲。據馬其昶(1855—1930)《桐城耆舊傳》記載:明代史仲宏路過摯友方懋家門前,戶外先聞兒聲,入室便聞紡績之聲,登堂坐定可聞書聲,他稱贊說:兄臺家中真是人丁興盛,有折桂掇巍的氣象啊!
桐城歷史上許多讀書人,其家貧僅供裹腹,戴名世(1653—1712)、劉大櫆(1653—1712)、劉開(1784—1824)等桐城派大家,雖窮愁潦倒、顛躓不售,仍終身致力于立言警世,一生著作等身。不少士子在鄉試以后,年未衰即絕意進取,不再踏入科闈。而銳志窮經,自少年至白頭,無一日廢書著述。劉開《自樂亭記》云:
筑一亭于園之南,高不及樓,廣能容席,深無重戶,敞可延日。河水流焉,而逕其前,書室聳焉,而峙其后,高節其中,唯貯書千卷。是多佳日,主人于是讀書其間,俯而思,仰而窺,靜有悟,動有得,興至乃歌……
無論窮達,皆以讀書為樂,以著作述懷為己任。近代劉聲木先生(1876—1959)在其《桐城文學淵源考·序》中寫道:
自顧生平亦頗好聚書讀書,而半生落拓若此。細想天之生我,木不如也,草而已矣。又生于大道之旁,一任行者及牛羊踐踏,然牛羊雖能踐踏,亦不能禁其添生枝葉。予雖自為甘草,亦欲以枝葉自見。生平所欲編輯之書甚多,編輯未能成卷帙者亦多。
這是歷代無數桐城文人中一部分寒儒窮且益堅,著書不輟的真實寫照。
桐城先賢著述立言之傳統源于中國古代先哲思想。桐城派大家方東樹在他的《書林揚觶》中專作《人當著書》一章,旁征博考,援引荀子“人少不諷誦,壯不議論,則為無業人矣”之說,曹丕“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之謂,成其佐論。他特別推重宋儒有關著書之說,引程頤一段語錄最為精妙:“程子曰:農夫深耕易耨播種五谷,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德及民而虛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蠧。惟綴輯圣人遺言,庶幾有補耳。”桐城先賢們正是遵循著古代先儒的思想,視文章為天下之大事,沿著古人“諷誦議論、歲久成書、自足垂世”的寫作路徑,代代相續,構起一座貫穿唐宋元明清及至民初近一千五百多年的著作長廊。
在這一蔚為大觀的文藝長廊里,散發著諸如經典疏訓、詩歌散文、書法繪畫、水利農兵、天文歷算等萬卷書香。唐、宋、元三代作者零落,著作寥寥可數。從明初至清道光400余年,粗略估計,桐城學者著作凡官槧家刻概為1290部,5690余卷,作者700余人。其中經部60余家,128余部960余卷,史部57家77部530余卷,子部60余家96部878余卷,集部336家467部2920余卷。
此外,乾隆時查明“違礙書目”如左光斗、方孔炤、方以智父子、潘江、方文等人詩文集共計21部400余卷,再加上僅有書名而無卷數的作者詩文、筆記、訓詁、音韻、讀史、解經等著述約達500余部。這些著述書名輯錄于《四庫全書總目》《明史·藝文志》《江南通志》《安慶府志》《桐城康熙縣志》《桐城道光縣志》、朱彝尊《經義考》等典籍,尚有一些諸生布衣之著作流布民間,未收入官編史乘之中的難計其數。說桐城先賢著述囊括四部、輝映梨棗,為它縣所罕匹,確非虛誕溢美之詞。
考查今人編《桐城文物志》《桐城縣志》,現藏于本市圖書、博物、檔案三館之中的桐城先賢著述已不足上述數目的十分之一成,僅剩200余部,多為清康熙至民國初年版本。歲月嬗遞,滄海桑田,高臥龍眠的一個個耿介君子、飽學之士如桐溪之水,漸次逝去,那些藏于篋中之楮墨蕓香大多也隨風飄零了。考其原因,無外乎以下諸端。
首先是年代久遠,自然殘損。凡水火之患,蟲蠹之噬,盡可毀損書籍。史載道光年間頻發水患,縣城以下,東南地鄉鎮幾成澤國。每遇大水,浪擊房舍,居民逃生之際,家藏多被丟棄,水災過后,人畜平安已是萬幸。后代讀書人家尚能珍惜祖典,平凡人家,門庭不顯者,其先祖著作多半喪失殆盡。
其次,人為輕視,敝帚不珍。先祖嘔心瀝血,朝夕磨剴,刊刻成書,希望流播后世。倘若后代家道中落,便分田析產,鬻書置業;或家貧無以為生,便典當祖業,而篋中無用之書,便首當其用。然先祖著作由其家族收藏,為傳家之寶,一但典賣,價值陡減。至于流落民間舊籍殘稿,更難免不被毀棄了。
再次,歷次戰亂,頻遭損毀。桐城處七省通衢之要沖,自明季以后,歷經張獻忠圍城、晚清太平天國兵燹、民國初年軍閥混戰,以至現代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桐城人皆飽經戰火。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又經“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等歷次政治運動,天災人禍,桐城一邑不知有多少珍本善本、孤本殘卷遭到滅沒零落。
其四,清代文字獄,桐城學者不少著述被禁毀。戴名世(1653—1712)一生著述宏富,自康熙末年查抄毀板,至清末尚未開禁。散佚之多,殊為可惜。雖有戴鈞衡搜輯成卷,但僅《潛虛先生文集》一書不足以反映戴氏畢生著述的全貌。另有少數著述內容不足以教人修身理性,更無經世之用,漸被時間所淘汰。
所幸文化漸為國家所重視。“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已成社會共識。現藏于桐城市圖書館、市博物館、市檔案館的古籍善本,得到珍視,妥為庋藏。這些碩果僅存的先賢著述,是桐城的文化菁華、文明之源,但愿不再重罹災禍。
更有當今新一代桐城文化傳承人,如莊子所云“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常常清茗一杯,伏案夜讀。以陳所巨先生為領軍的桐城作家群體,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時代強音,握筆高歌,創作了大量有時代意義且具桐城地域特色的當代文藝作品。其后,又有洪放先生高舉“新桐城文學”大纛,一時間桐城文苑俊彥輩出,文藝創作源源不絕,洵可告慰桐城先賢于一二了。
李國春,安徽桐城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黨組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