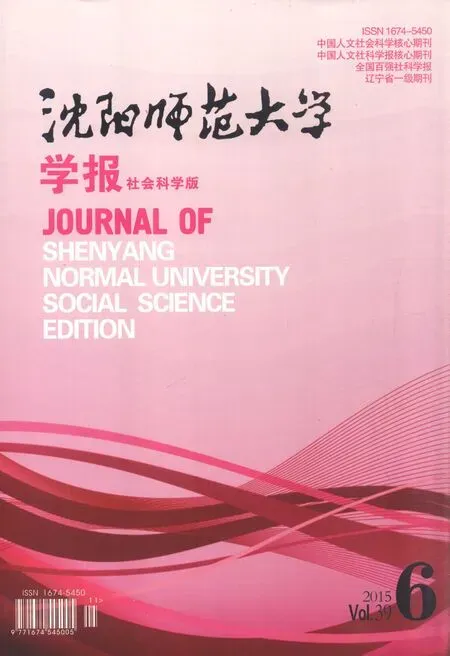滿族文學作品人民性的表現
閻麗杰
(沈陽大學文化傳媒學院,遼寧沈陽110044)
滿族文學作品人民性的表現
閻麗杰
(沈陽大學文化傳媒學院,遼寧沈陽110044)
滿族文學的人民性在實際創作中一直存在,但滿族文學的人民性并沒有被明確地提出來而且長期以來沒有受到重視,因此,有必要研究滿族文學人民性,并且對滿族文學人民性加以界定。滿族文學人民性屬于歷史的范疇,應該對之加以活態的考察。滿族文學的人民性主要體現在要表現人民的思想精神和獨特的藝術形式,滿族文學中的人民性不在于作品中描寫了人民,而在于作品怎樣描寫人民。滿族文學的人民性主要表現在滿族民間說唱藝術中。
人民性;滿族文學;滿族民間說唱藝術
滿族文學的人民性是長期以來一直存在但少有提及的一個問題,從滿族文學的實際作品創作來看,滿族文學的人民性一直存在,但沒有被明確提及。滿族文學的人民性主要存在于滿族民間文學作品中。滿族民間文學大多是勞動人民的集體創作和世代傳承的結果。滿族文學自古以來以勞動人民創作為主體,尤其是滿族民間文學構成了滿族文學的主體性存在,如滿族歌謠、滿族民間故事、滿族神話、滿族民間傳說、滿族說部、八角鼓、岔曲、滿族諺語、滿族民間小戲等滿族民眾創作的作品,這些滿族文學作品絕大部分都是口傳心授的滿族民眾創作的作品。滿族文學中的民間創作異常豐富,民眾創作已經取得了相當高的藝術成就,滿族民間故事、滿族歌謠已經成為世界級、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盡管如此,滿族文學人民性的研究工作卻明顯滯后于創作實踐,學術界對于滿族文學人民性的導向理論研究處于長期的被忽略狀態,幾乎沒有人從人民性創作導向的視角來研究滿族文學。
一、滿族文學人民性的藝術界定
人民性的概念最早是由俄國的別林斯基提出來的,是文學理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個根本問題,也是衡量文學作品價值的一個重要尺度。人民性的概念是一個歷史范疇,對于文學人民性的界定要結合具體的歷史語境,要看到滿族文學的人民性研究是一種活態的研究,因為人民是一個歷史范疇,不是一個固定的范疇,人民的界定取決于歷史的發展。不同的歷史時期,對人民性的界定是不一樣的。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在我國現代史上,人民的涵蓋對象就不斷發展變化著,抗日戰爭時期的人民、解放戰爭時期的人民、社會主義時期的人民涵蓋對象都是不一樣的。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切擁護抗戰的人都屬于人民。在解放戰爭時期,一切擁護祖國解放戰爭的人都屬于人民。在社會主義時期,一切擁護社會主義建設的人都屬于人民。由此可見,不同的歷史時期,人民的涵義是不相同的。
隨著時代的發展,人民性的涵義還會有變化,有不同的具體內容,因此,要客觀地根據實際情況考量滿族文學的人民性問題。
滿族文學的人民性同樣體現在勞動人民身上。盡管滿族文學作品沒有使用人民性一詞,但是滿族文學的人民性是十分明顯的。在滿族文學中,能夠代表滿族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素質的作品仍然是具有人民性的作品。滿族勞動人民不但是滿族歷史的創造者,同樣是滿族文學的主要創造者。
文學的人民性概念的提出,有著深刻的理論和實踐意義,人民性是衡量文學作品的思想原則的尺度之一,具有人民性的作品可以最大限度地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需要和美學享受。滿族文學的人民性研究是一種活態的研究,因為人民是一個歷史范疇,不是一個固定的范疇。從量的規性上,滿族人民是相對于個別人而言的,是指大多數的人。勞動群眾始終是人民的主體。正如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的那樣,中國最廣大的是勞動人民,勞動人民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廣大的人民主要包括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從質的規定性上,滿族人民是指歷史上先進力量的代表,是對社會歷史起推動作用的人。歷史的實踐已經證明,人民創造了歷史,人民創造了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人民永遠是社會進步的主體力量,人民應該是歷史的真正主人。因此,要客觀地根據實際情況考量滿族文學的人民性問題。同時還要看到,人民當中存在的東西不一定都是具有人民性的東西,滿族文學中同樣存在一些糟粕的東西,不要把低俗的東西當成通俗的東西,欲望不等于希望,要注重發掘滿族文學中的引人積極向上,有利于民族團結的富有人民性的作品。
具有人民性的作品,往往是具有很高價值的文學作品。具有人民性的作品,往往是在民間得到了時間的驗證,是勞動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具有巨大的藝術魅力。滿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人民性特點十分鮮明。因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往往是活態的民間存在,滿族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滿族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
滿族文學既有人民性又有民族性,要區別人民性和民族性的關系。別林斯基認為:“‘民族的’一詞在涵義上其實比‘人民的’更為廣泛。‘人民’總是意味著民眾,一個國家最低的、最基本的階層。‘民族’意味著全體人民,從最底直到最高的,構成這個國家總體的一切階層。”[1]由此可見,人民性與民族性有交叉的部分,民族性包括人民性,或者說民族性大于人民性,不能把人民性與民族性等同起來。
二、滿族文學人民性的思想精神
滿族文學中的人民性不在于作品中描寫了人民,而在于作品怎樣描寫人民,對人民群眾的態度如何。滿族文學中人民性思想的產生源自對底層滿族人民生活的描寫,對底層人民的深切關懷和同情。看一部滿族文學作品是否具有人民性,就是要看這部滿族文學作品是否用正確的態度對待滿族人民,反映了滿族人民群眾的思想、愿望和利益,并為滿族人民群眾所理解和喜愛。人民性不是形式問題,而是要看作品是否表現了人民的思想精神。作品中“必須滲透著人民的精神,體驗他們的生活,跟他們站在同一水平……感受人民所擁有的一切質樸的感情”[2]。在藝術創作中,站在人民的立場,飽含對人民的同情和贊頌之心去接近人民、感受人民的疾苦,描寫群眾生活,同情、歌頌人民群眾的作品。哪些滿族文學表現了滿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如何表現了滿族人民的思想情感,因為,滿族文學作品的人民性最鮮明地表現著文學與人民的聯系。
1.人民群眾是作品的創作主體。人民是文學的真正的主人。在滿族文學作品中,滿族人民一直是滿族文學創作的主體,滿族文學的人民性是鮮明而突出的。人民群眾創造歷史,滿族文學作品的創作主體是勞動人民。滿族文學的大多數作品都是由滿族人民創作的,滿族民間故事、滿族歌謠、滿族薩滿神歌、滿族神話、滿族民間小戲、滿族說部、滿族岔曲、滿族八角鼓等等。這些滿族文學作品大都是底層人民創作的文學作品。
滿族人民群眾創作的作品受到滿族貴族的重視和提倡。滿族許多民間創作都是在民間興起,然后由上層貴族大力提倡、扶植的。滿族的八角鼓岔曲就有著獨特的發展道路,從民間產生,到宮廷提倡,再到民間發展。滿族岔曲最初屬于民間俗曲。相傳由流行于民間的戲曲高腔之脆白發展而成。岔曲的演唱最初沒有固定的形式,可以坐著唱,站著唱,騎馬唱,走路唱,隨意而歌。岔曲最初是由軍中外火器營人文小槎,在行軍途中,自制馬上曲,成為最初的岔曲。“隨著班師的軍隊,岔曲這種藝術形式又被帶入京城,由于雅俗共賞,符合滿族審美習慣,岔曲又在八旗軍民中流傳,進而傳入宮中,受到王公貴族甚至皇帝的喜愛,乾隆皇帝允許旗籍子弟自由創作、演唱‘得勝歌詞’、并且親自命令宮中另制曲詞,教習南府歌演。自此,岔曲開始興盛起來,沿著民間和宮廷兩條脈絡比較迅速的發展。”[3]滿族岔曲、八角鼓的誕生走過了迂回曲折的道路:從民間到軍旅、到宮廷、到府第、到票房、到茶館、到劇場,再回到民間。它經歷了興起、發展、繁華、衰弱的過程,融合了滿族和漢族的文化。
鐵保對滿族人民群眾的創作給予很高的評價:“余嘗謂:讀古詩不如讀今詩,讀今詩不如讀鄉先生詩。里井與余同,風俗與余同,飲食起居與余同,氣息易通,瓣香可接。其引人入勝,較漢魏六朝為尤捷。此物此志也。”[4]
滿族民間故事是滿族人民口頭創作的不押韻的敘事類作品的總稱。民間故事總體特點是故事篇幅不長,單線索發展,故事情節完整,情節生動吸引人,并在情節中伴有附會傳說等虛構成分,表達了勞動人民的生活習俗、理想愿望。滿族民間盛行講故事。俗稱“講古”或“講瞎話”。滿族民間故事反映了滿族的風俗習慣、審美理想、生活態度。滿族民間故事主要包括幻想故事、生活故事、動植物故事、智人故事等。滿族民間故事表現了滿族對真善美的追求,對智慧的熱愛。如滿族民間故事中很有代表性的作品《滿族三老人故事集》中的三位作者李成明、李馬氏、佟鳳乙都是遼寧省岫巖的老人,三位老人從小不識字,都是地地道道的民間百姓。三位老人在孩童時代從老一輩人口里聽來了上百則故事。
滿族傳說的創作主體也是人民群眾,是由滿族民眾創作的關于歷史上某人、事、物傳承下來的一些說法。關于歷史人物、事件、古跡、習俗有關的故事,往往以歷史事實為依據,具有探因溯源的效果。滿族說部是滿族世代口耳相傳的長篇敘事說唱藝術,以歌頌祖先和英雄人物為主要內容。滿族說部往往以家族的方式傳承,與家族活動關系密切。
滿族歌謠都是滿族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口頭創作的篇幅短小的具有韻律的文學作品,能夠最直接地表達勞動人民的呼聲。由于勞動人民地位低下,往往沒有話語權,歌謠成為表達滿族勞動人民心聲的最直接的途徑。滿族歌謠不分演出地點,山間河邊、田間地頭都可以隨口而唱,隨性而發。
滿族八角鼓既是一種滿族民間樂器,也是一種曲種的名稱。八角鼓是單弦和八角鼓曲種不可缺少的伴奏樂器,是滿族最有特色的民間樂器。八角鼓的演唱地點靈活多變,沒有固定的場地,無論是行軍打仗,還是田間地頭都可以隨性演唱。
由此可見,滿族大部分文學為民眾所創作,在民眾中流傳,被民眾所接受。在滿族民間文學中,很難找到作品的原創者,我們找到的往往只是傳承人。滿族民間文學作品往往是世世代代相傳下來的,是滿族民眾集體傳承、創作的結果。
2.人民群眾成為文學作品的主要表現對象。文學的事業從本質上說是人民的事業,所以人民群眾要成為文學作品的主要表現對象。“人民不僅是創造一切物質價值的力量,人民也是精神價值的唯一的永不涸竭的源泉,無論就時間、就美還是就創作天才來說,人民總是第一個哲學家和詩人:他們創作了一切偉大的詩歌、大地上一切悲劇和悲劇中最宏偉的悲劇——世界文化的歷史。”[5]滿族人民應該成為文學的積極的主角,因為人民創造了一切文學藝術賴以產生的物質基礎。滿族作家的創作靈感來源于人民群眾的生活,人民是作家創作的源頭活水,離開了人民,作家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也就不能創作出好作品。許多經典的作品都是來源于民間的傳說、故事。在滿族文學作品中要感應時代的脈搏,描寫人民的生活和實踐、苦難和歡樂,表現人民的理想與希冀,抒發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審美追求。滿族民間故事直接反映現實生活,表現了滿族民眾的生活百態和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樂之情。這類故事內容較多地表現了家庭成員的關系、家庭生活、愛情生活、學習技能手藝、風土人情、地方特產等。
在滿族文學作品中,表現最多的內容就是滿族人民的生活習俗、勞動生產、愿望要求。如《勇敢的阿渾德》《繡花女》《黑水姑娘》《射柳》《冰滑子》等等,總之,人民群眾成為滿族文學的主要表現對象。
3.真實地描寫社會生活,揭示社會生活本質的某些方面的作品是具有滿族人民性的作品。有些滿族民間文學本身就是滿族民眾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很多滿族民間文學本身具有二重性,它即屬于生活本身,又屬于文學藝術。有些作品很難區分是屬于生活的還是屬于藝術的。如,滿族的薩滿神歌、滿族的勞動歌謠既是滿族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又是文學作品,滿族民間文學和生活呈現了一種水乳交融的親和狀態。這些作品都真實地描寫了滿族人民的社會生活,并揭示了社會生活本質的某些方面。在文學作品中,可以有假詩文,但沒有假民謠、沒有假山歌,這使得具有人民性的滿族作品具有真實自然、剛健清新的特點。
滿族神話主要有創世神話、自然起源神話、人類起源神話、英雄神話、文化起源神話等。鮑亞士認為:“神話的觀念便是對世界的構成及起源的基本見解。”[6]滿族神話傳說表現了先民用原始思維對于原始自然、社會的理解,間接地表現了滿族先民的社會生活。滿族神話是滿族先民對于不了解的大自然的一種主觀的解釋。滿族神話主要反映了滿族勞動人民的生活愿望。滿族文學的進步性、民主性和反抗壓迫的革命的傾向性是滿族文學人民性的基本精神。
當前,滿族文學創作要尋找一條“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和“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創作道路。
三、滿族文學人民性的藝術形式
考量一部滿族文學作品是否具有人民性還要看作品的藝術性是否為滿族人民喜愛和了解,是否有滿族人民喜愛的通俗易懂的藝術形式。
具有人民性的作品往往是通俗易懂的作品。因為許多勞動人民沒有讀書的機會,不識字。“到現在,到處還有民謠,山歌,漁歌等,這就是不識字的詩人的作品;也傳述著童話和故事,這就是不識字的小說家的作品;他們,就都是不識字的作家。”[7]因此,具有人民性的作品大多在民間口頭傳承,具有通俗易懂的形式。
滿族人民最初結繩記事,據滿洲實錄,1599年努爾哈赤命額爾德尼和噶蓋兩人將蒙古字母借來創制滿文。在很長的時期內,滿族民眾沒有文字,依靠口頭傳承,他們是最底層的、也是最基本的階層,其文化學習程度也往往很低,甚至沒有受過教育,因此,滿族人民對滿族文學藝術形式有著特殊的喜好,他們往往喜歡通俗易懂的藝術形式。要想使文學作品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接受、理解和廣泛的傳播,產生應有的社會作用,文學作品就必須有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
(一)滿族文學的口頭傳承
滿族文學很多都是口耳相傳。由于很多民眾不識字,其傳承的方式都是口耳相傳的,沒有文字記載。口語化打破了讀者接受的障礙,降低意義的識別程度,通俗易懂,明白曉暢,朗朗上口,便于記憶,使讀者瞬間領悟作品的內容,使作品得到廣泛的傳播。
滿族文學的口頭傳承文學具有重要的價值。人民群眾的口頭創作為專業文藝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營養,成為專業文藝創作的一個溫床。沒有人民群眾的口頭創作,就沒有專業文藝創作。精神財富的根基永遠在勞動群眾中。如果說人民群眾的口頭創作是“俗”,專業文藝創作是“雅”,雅正是從俗中來的,沒有俗就沒有雅。俗的也可以變成雅的。
(二)滿族文學的說唱文學
滿族文學很多作品都具有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首先,通俗易懂。由于許多作品都是民間群眾創作,很多人不識字,較少有文學藝術的修辭方法,所以其作品往往自然清新,直抒胸臆,真摯感人。
滿族文學最受歡迎的喜聞樂見的形式是說唱文學。滿族歌謠、滿族岔曲、滿族八角鼓、滿族薩滿神歌、滿族民間小戲、滿族說部、滿族子弟書等,這些滿族文學藝術形式都屬于口頭文學中的說唱文學。這些滿族說唱文學和滿族的民族審美心理、風俗習慣一致。滿族是個能歌善舞的民族,很多滿族文學都具有說唱的特點。滿族文學人民性的藝術形式的突出特點就是說唱文學。
說唱文學句子往往短小精悍,有利于演員演出,便于朗朗上口,及時把要表演的思想內容傳達給讀者,另外,也有利于聽眾接受,便于聽眾絲絲入耳,及時領會表演意圖,取得相應的審美效果。
(三)滿族文學的音韻節奏
滿族文學的音樂美特征十分明顯。滿族詩歌、歌謠、薩滿神曲的合轍押韻具有明顯的音樂美。滿族的岔曲本身就是演唱的藝術。“從流傳至今的岔曲旋律看,宮調式和do re mi三音列骨干音,以及簡約、質樸、棱角分明的氣質,都是滿族音樂的典型特征。”[8]可見,岔曲的音韻是有比較固定的審美范式的。滿族八角鼓由軍中自娛性演唱發展為滿族的一種說唱藝術形式。滿族子弟書類似長篇敘事詩,句式短小,修辭方法豐富,大量的排比句,形成了很強的節奏感,句尾押韻,產生了韻律美。就是滿族的敘事文學也有很明顯的音韻節奏,滿族說部、滿族民間故事的演說者說到興起時可以即興演唱。
滿族文學的喜聞樂見的形式還應該關照滿族文學的民族特點。
社會主義文藝是為人民服務的,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從本質上講,社會主義文藝就是人民的文藝,所以社會主義要反映人民的心聲、情感。文學的人民性的有無,是衡量社會主義文學的重要尺度。滿族作家應該以表現滿族文學人民性為天職。現在學術界充分認識到文學人民性創作導向的重要性,正在努力進行文學人民性導向問題的研究,少數民族文學也不例外,滿族文學人民性導向的研究是刻不容緩的責任,有必要對其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
[1]別列金娜.別列金娜選輯[M]//別林斯基論文學.梁真,譯.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8:82.
[2]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2卷[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184.
[3]何曉芳.滿族民間說唱藝術研究[M].沈陽:白山出版社,2012:156.
[4]彭書麟.于乃昌.馮育柱.中國少數民族文藝理論集成[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582.
[5]高爾基.個人的毀滅[M]//高爾基論文學續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54.
[6]鮑亞士.神話與民俗[J].民俗第1卷,1942(4).
[7]魯迅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94-95.
[8]東方音樂學會.中國民族音樂大系·曲藝音樂卷[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1989:193-194.
【責任編輯 詹麗】
I29
A
1674-5450(2015)06-0012-04
2015-09-20
遼寧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L14DZW 016)
閻麗杰,女,遼寧沈陽人,沈陽大學教授,主要從事文藝學與滿族文學藝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