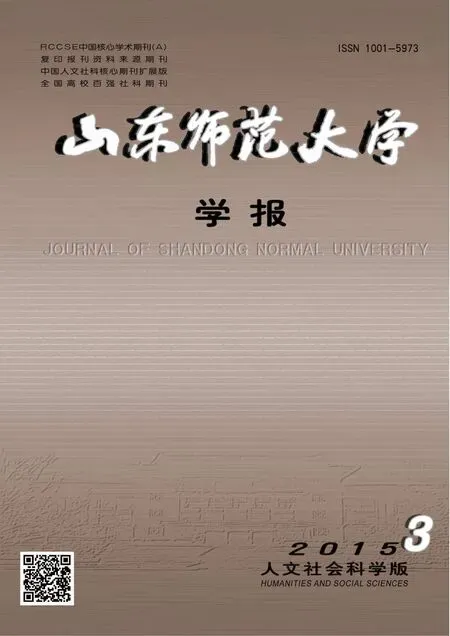戰國時期“鄒魯之風”的形成與演變*①
王志民
( 山東師范大學 齊魯文化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250014 )
戰國時期“鄒魯之風”的形成與演變*①
王志民
( 山東師范大學 齊魯文化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250014 )
鄒、魯是兩個文化淵源不同的東方古國。在春秋戰國時期,以尊孔、崇儒、讀經、傳經為主要特征的“鄒魯之風”形成發展過程中,鄒、魯經歷了二元一體的文化演變,成為一支以“鄒魯之風”為時代文化內涵的區域文化。“鄒魯之風”肇端孔子,始于魯;興于子思,擴于鄒;盛于孟子,風行鄒魯,并由士風演變為世風,由鄒魯之地傳播影響至全國。從楚墓郭店竹簡發現的與思孟學派有關的活動情況,結合《莊子· 天下篇》、《荀子 ·非十二子》綜合分析,可以看出:戰國“鄒魯之風”形成的骨干力量——鄒魯之士,實際即是思孟學派的廣大成員。他們根植鄒魯,活躍四方,西至中原,南到長江,推動了鄒魯之風吹向全國。戰國“鄒魯之風”是先秦儒學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它為秦漢以后不絕于史的“鄒魯之風”在全國各地的落地生風,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鄒魯之風;儒學;文化傳播
國際數字對象唯一標識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5.03.003
在中國儒學史乃至文化史上,“鄒魯之風”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重要文化現象。在漢代以后的二千余年里,“鄒魯之風”已經成為“儒風”及傳統文明之風的代稱,例如《唐文拾遺》卷45載《文宗御注孝經賦》即有:“萬門翕集,清傳鄒魯之風;萬室雍熙,普詠文明之德”。以“鄒魯之風”與“文明之德”對應。元代詩人吳海為福建閩縣人,博學負氣節,人稱“性不悅流俗,慕鄒魯之風”②《元詩選上集·辛集》。。《臺南古跡志》記載徐樹人任職臺南時,大興海東書院,“一時文士興起,有海濱鄒魯之風”③《雅堂文集》卷三。。可見,“鄒魯之風”歷來作為一地優良文化風氣的代表。
鄒魯是孔孟的故里。鄒魯文化研究是儒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但勿庸諱言,這個領域的研究,特別是鄒魯文化與孔、孟及儒家學派關系等諸多問題的探討,還是很不夠的。
杜維明先生從世界儒學研究意義出發,提出了一個思考深遠的問題:“為什么曲阜、鄒城形成的區域文化影響到中原,繼而到全世界?這其中經過怎樣的曲折和發展,逐漸成為主流……都很值得探究。”④杜維明:《在儒家思孟學派國際學術研討會閉幕式上的總結發言》,《儒家思孟學派論集》,濟南:齊魯書社,2008年,第3頁。最近,我又讀到了李學勤先生在十年前談到這個問題時切中肯綮的一番話,很受啟發:“鄒魯文化何以會孕育出孔子及儒學?孔子和儒學又怎樣塑造與推進了鄒魯文化?以孔子儒學為代表的鄒魯文化是在什么環境下形成的,與其他區域文化存在著如何的關系?要回答這一類問題,必須對鄒魯文化進行全面的考察分析,說明其本質和特征。”⑤李學勤:《〈鄒魯文化研究〉序》,賈慶超等:《鄒魯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杜、李兩先生的話,代表了新時期學術界對孔子與儒學研究的一種熱切期望:要從地域文化的角度來深入挖掘和探求孔、孟及儒學孕育、產生、發展的文化動因。這不僅是儒學研究深化的需要,也是齊魯文化研究的重大課題。本文擬對鄒魯之風的形成、發展、演變的過程,作一些粗淺的探索。
一、鄒、魯與“鄒魯”——二元一體的文化演變
“鄒魯”并稱,始見于戰國《莊子·天下篇》。雖不見此前史籍,但鄒、魯兩國都是立國很早,而且文化淵源有自的文明古國。關于兩國文化的淵源、發展及相互關系,已有學者進行過有益的探討論說*李啟謙:《論孟子思想與鄒魯文化》,《煙臺大學學報》1995年4期;王鈞林:《論鄒魯文化》,《東岳論叢》1997年1期;楊朝明:《邾魯關系·邾國文化·鄒魯文化》,《齊魯師范學院學報》2012年第4期。,但仍有必要在此梳理辨析。
(一)鄒與魯——兩支不同淵源的文化
鄒、魯兩國毗鄰,以今日觀其古國遺址,相距不過20公里。但從文化淵源看,兩國文化并非一體。魯,立國于周初封建諸侯之時,為周宗室、姬姓,史多有載,論者亦多,此不贅述。鄒之文化淵源卻值得深入探析。
從已有的研究成果看,能夠確信的是:鄒,即邾(鄒,亦作“騶”,為“邾”之異體字)。邾,也作邾婁,為一立國早于魯的東夷土著方國。其文化淵源,有學者依據《路史》、《元和姓纂》等文獻和出土的《邾公牼鐘》認為:邾人的祖先為陸終氏,而陸終氏為黃帝之孫昌意之子顓頊高陽氏的后裔。*郭克煜:《邾國歷史略說》,《東夷古國史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且據《路史》:“朱,曹姓,子,邾也。”曹為姬姓,如此說,鄒與魯應為同祖同源的姬姓方國了。但此說頗多可疑處。一是上述材料多據唐人之《元和姓纂》和南宋羅泌《路史》,其中推導、傳說成分較大。二是與先秦文獻中有關邾、魯關系的記載多有矛盾之處。細斟驗之,筆者以為:王獻唐先生在《炎黃氏族文化考》一書中所說“三邾土著為東夷炎族”,而非黃帝族裔,是正確的。此外,我們發現還有三條資料可以證明鄒、魯兩國不同源,現補充如下:
其一,周王室未視邾為同族同源之國。邾為夏商時立國的東方較大方國,與商奄等同屬東夷土著。其大約未參與周初的商奄、薄姑叛周之亂,在周公東征后,保留下來。然而周初封建,并未封邾,只是將其作為周之附庸而據邾地。直至春秋時期,因其支持齊桓霸業,“尊王”有功,方封其為子爵之國。*《左傳·隱公元年》載:“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杜預注:“以為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孔疏:“齊桓行霸,儀父附從,進爵為子。”顯然,周王室并未將邾視為同宗。更沒有象魯、晉一樣,具有“以蕃屏周”之待遇。
其二,春秋之世,邾、魯堪稱最為敵對之國。邾魯毗鄰,觀春秋之時,邾與魯,雖時有朝魯及與魯盟好之事,但總體看,卻始終為敵意最大之國。這與魯同晉、曹等同宗之國的親密關系形成鮮明對照。此非純粹外交之事,而與文化相異有較大關系。據顧棟高《春秋大事表》統計:春秋之世,魯國“兵之伐國僅二十,而書公伐邾者六,書大夫伐邾者八。……邾在魯之宇下,而陵弱侵小之兵,史不絕書如此”。所以,王獻唐在說到春秋邾三國之憂時說:“鄰國來侵,亦時以兵戎相見,其愁結最深者莫如魯。”*王獻唐:《三邾疆邑圖考》,濟南:齊魯書社,1982年。統觀《左傳》所記春秋史料,邾與魯,能抗則抗,能伐則伐,時有結盟,但以敵對為主。《左傳》記載中,亦不乏邾聯莒、聯齊、聯吳、聯晉等國攻魯之事。*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62-364頁。以“尊尊親親”為治國方針,至春秋時仍享有“周禮盡在魯”之譽的魯國,對鄰國之邾,“相煎何太急”?看來,本非同根生。
其三,魯人視邾為“蠻夷”之國。據《左傳》僖公二十一年載:魯僖公母成風之母國須句為邾所滅。“成風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不僅指邾滅須句為蠻夷亂夏,且認為這是周王朝之禍。并于次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禮也。”可見,邾在魯人眼中,實為異類。邾、魯之爭,帶有夷夏文化沖突的底色。
鄒、魯文化的差異,從古文字和考古學上也能得到進一步的認證。山東考古學者王樹明先生在其《邾史二題》一文中就提出:“邾之得名,緣于邾人原以蜘蛛為圖騰,邾又‘邾婁’一名,是人們直呼其圖騰之名‘蜘蛛’二字的聲轉易字。”*棗莊市山亭區政協:《小邾國文化》,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197頁。
又例:邾國有諸多與魯人相異的習俗。《左傳·定公三年》載:邾莊公下葬,“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這與同屬炎帝后裔,保留較多東夷習俗的齊人殉車馬、殉人*齊國故城遺址中,現有大型殉馬坑:東周殉馬坑、殉車馬坑兩處。參見山東省博物館:《臨淄郎家莊一號東周殉人墓》,《考古學報》1977年第1期。相類似,而在魯國不曾發生。
近些年,在棗莊東江村發掘的三座小邾國墓葬中,發現春秋時期青銅器63件,24件有銘文。其中,多有小邾國君為嫁女而制作的媵器。這與在河北易縣及河南洛陽發現的齊嫁女的青銅媵器十分相似。*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05頁;李零:《讀小邾國銅器銘文》,棗莊市山亭區政協:《小邾國文化》,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年。
春秋之時,邾與魯為敵,卻一直與齊國結盟,數度夾攻魯國,很有些“藉齊勢以侵魯”、“邾為齊之屬”*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63頁。的傾向。這應該與文化上的同源不無關系。
以上梳理可以大致總結為:鄒、魯文化是兩支淵源不同的文化。在春秋以前,魯為周之封國,鄒為周之土著附屬國。在“興滅國繼絕世”的周禮文化生態環境下,鄒、魯兩國主要傳承著各自的部族文化。鄒為土著東夷古國,保留和傳承著較多的東夷土著文化的諸多特色;魯為周文化在東方的代表,傳承著以周禮為核心、周魯文化的傳統。兩國和平關系的維持主要表現為:邾(鄒)以禮朝魯、尊魯;魯以禮安邾。彼此關系平穩,各承傳統。
(二)鄒魯文化交匯于春秋,融合于戰國
春秋時期,王室衰微,綱紀不張,禮樂崩壞,列國紛爭。從鄒、魯兩國關系講,在魯強鄒弱的基本格局下,進入了一個以動蕩、沖突、敵對為主的時期。從文化上看,則經歷了一個由排斥、沖突到交流、融合的過程。大致可以說,春秋前、中期,兩支文化在以沖突、敵對為主的關系中交流;春秋后期,隨著魯強鄒弱國勢的定格和士階層的興起,鄒、魯在上層文化中加快了交流與融合。
春秋末到戰國中期,是由鄒、魯兩支文化到“鄒魯”文化融二為一的完成期。它以文化下移、士的崛起為基礎,以孔子大興私學為途徑,以鄒魯士風的一體化形成為展現,實現了鄒魯文化融二為一的過程。這種融合,從民族文化的發展演變講,是在犬牙交錯的部族文化交流融合中,在一個相對統一的地理單元內,夷、夏文化融合的縮影;是社會巨變所導致的原部族方國與封國之勢力消長而形成的文化融合的必然結局。由鄒、魯到“鄒魯”,既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又是社會文化劇變的結晶。鄒、魯兩支異質文化的融合,不是簡單的一加一式結合,也不是以魯融鄒的簡單合并,而是兩支文化的提升和升華。鄒魯文化既非鄒文化,也不是簡單等同于魯文化。鄒魯文化是在制度文化大變革時代產生的新區域型的文化。而其結晶體,即表現為“鄒魯之風”。
二、從《莊子·天下篇》看“鄒魯之風”
“鄒魯”并稱,最早見于《莊子·天下篇》,也是關于鄒魯之風形成的最早文獻記載。《莊子·天下篇》是一篇專論諸子百家爭鳴的珍貴文獻,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學術史專論。《天下篇》認為:古之道術“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于本數,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而到了戰國之世,天下大亂,賢圣不明,道德不一,而各派思想家各執一己之見。作者遂以此篇論述今之各派與古之道術關系。
《天下篇》以“古之道術無乎不在”為宗,評述當時六個主要學術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主旨及與“古之道術”的淵源關系。其中提及五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13人,其中,對墨翟、禽滑厘(墨家),宋钘、尹文(稷下黃老學派),彭蒙、田駢、慎到(稷下道法家),關尹、老子以及莊子本人(本真道家)等四家論述,大致運用同一模式:先述學術宗旨及與古之道術關系,再提代表人物,繼之評說基本思想主張。以稷下道法家為例:“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于慮,不謀于知,于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造則不遍,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另一家惠施、桓團、公孫龍等辯者(后世稱名家),則對其善辯特點及思想觀點主張進行了評述。《天下篇》汪洋恣肆,思想宏闊,知識廣博,又精深獨到,點石成金。雖然,該文的作者是否為莊子本人,歷來存較大爭議,但如非像莊子這樣的曠世奇才確難寫出如此之高論。誠如王夫之所說:“或疑此篇非莊子自作,然其浩博貫綜,而微言深至,固非莊子莫能為也。”*王夫之:《莊子解》,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值得我們特別關注的是《天下篇》對儒家學派的記載,從內容及引文方式與前數家學派都不同,可說是一個特例。其記載為:
古之人其備乎!其明在于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道名分。其數散于天下而設于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細分析這段文字,作者在這里實際提出了在道術為天下所裂之后散布的三個方面:一是“舊法、世傳之史”;二是《詩》、《書》、《禮》、《樂》之五經文獻;三是百家之學。評析儒家,既沒有與其他各家并列論之,也沒有像其他各家一樣去評析代表人物及思想主張,而是講述了對“鄒魯”之地的一個群體——“鄒魯之士”與“縉紳先生”的一種風氣:對《詩》、《書》、《禮》、《樂》中的“古之道術”,“多能明之”。這是對“鄒魯之風”的最早描述。其中,有幾點很值得關注:
其一,“鄒魯之士”是鄒魯之風的營創者。在“士”階層蓬勃興起、百家爭鳴的戰國中期,“鄒魯之士”已是一個在各派各家學者中影響巨大的群體,以至莊子在評述各主要學術派別時,不得不將他們作特別的表述。這個群體跟其他學派那些朝秦暮楚、“取合諸侯”的游士不同,他們固守著“鄒魯”文化家園,營造出一種區域獨特的文化風氣。這個群體數量之眾,不限于部分學者,而是一個階層——“士”。這個階層在《莊子集解·天下篇》表述為:“士,儒者;縉紳先生,服官者或云縉。……紳,大帶,六經所由傳。”《莊子集釋·天下篇》《疏》亦云:“先生,儒士也。”*《莊子集解· 天下篇》。總體分析,大約有兩部分人組成:一種是儒士,即馮友蘭先生所說:“是一種有知識有學問之專家,他們散在民間,以為人教書相禮為生。”*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附錄:《原儒墨》,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鄒魯為孔子興學之地,儒士眾多,當在情理之中。二是“服官者”,即穿官服的知識分子。我的理解即是新興的士大夫階層,包括大、小有知識的官吏。總之,鄒魯之地的龐大知識分子階層成為百家爭鳴中的一支生力軍。正是他們,催生了鄒魯之風的形成。
其二,“鄒魯之風”的內涵主體是尊孔讀經的儒風。《天下篇》認為,那些“古之道術”載于《詩》、《書》、《禮》、《樂》等古典文獻中。鄒魯之士“能明之”,既反映出在鄒魯之地,研習六經已是知識分子的一種普遍風氣,也說明他們對六經典籍的研習已有相當的深度。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對儒家所作的詮解,實際也是對這種風氣很好的總結闡發,即“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為最高”。
今人郭沫若先生則直接將對儒的詮釋與鄒魯之士聯系在一起,提出:“儒本是鄒魯之士縉紳先生的專號。”*轉引自陳來:《古代宗教與倫理》,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第367頁。此亦足見鄒魯之風在儒學形成中的重要歷史作用。
其三,鄒魯之風的精神內核是一種崇尚道德教化之風。《天下篇》對鄒魯之風的精神文化內涵并沒有直接的表述,但是,它肯定了“其”(古之道術)在六經中的蘊含,鄒魯之士“多能明之”,實際上即是說,鄒魯之士最能理解與領會“古之道術”的實質,而這古之道術即是“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于本數,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莊子· 天下篇》。的精神思想的內核,亦即指中華文化自上古“三代”以來的文化精髓。而這個精髓,主要還是體現在精神層面,亦即思想文化。
陳來先生在其《古代宗教與倫理》一書中,對儒家思想的來源曾作過系統的梳理和考證。他認為:“儒家思想本身是三代以來中國文化的產物。……儒家思想是接續著三代文化的傳統及其所養育的精神氣質的。”《周禮·地官》之“大司徒”職中,有所謂“十二教”,“十二教中的前六教明顯是屬于禮樂教化的部分,與后來春秋戰國儒家所講的禮樂教化,其精神是一致的”*陳來:《古代宗教與倫理》,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第373、377頁。。關于教,文獻中記載:“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圣、義、忠、和;二曰六行:教、友、睦、嫻、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周禮、地官、大司徒》。可見,所謂六德、六行主要是道德教化。《左傳·昭公二年》中有晉國韓宣子到魯國感嘆“周禮盡在魯”的記載,魯地作為周公的封地,一直是《周禮》之制的典范執行者,到了春秋禮崩樂壞之時,魯地可謂“亂云飛渡仍從容”,仍然保持周禮。可以想見,鄒魯之風所展現的也是一種道德教化之風。
三、鄒魯之風的形成
關于鄒魯之風形成的過程,并無直接的文獻記載。但作為鄒魯之地一種“儒風”文化現象,來探討其形成的歷史軌跡,我們大致可以作如下的追溯:鄒魯之風的文化基礎,應該上溯至周公封魯之時。楊向奎認為:“魯遵守西周傳統,‘周禮在魯’是宗周禮樂文明的嫡傳……以德、禮為主的周公之道,世代相傳,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禮為內容的儒家思想。”*楊向奎:《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作為以尊孔讀經為主體展現的鄒魯之風的形成,則應該從孔子生前整理六經、并以六經授徒開始。其在春秋戰國之世的形成發展過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肇于孔子、興于子思、盛于孟子。
第一階段:肇端孔子,始于魯。
孔子對中華文明的最大貢獻之一,即是對三代文獻為主的古代典籍整理而編定“六經”。《莊子·天運篇》借孔子與老子的對話說:“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匡亞明在“文革批孔”后不久出版的《孔子評傳》中即高度評價說:“經過孔子整理的‘六經’(現僅存‘五經’),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夏、商、周特別是春秋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情況,對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文化史、政治社會史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六經’不僅是我國的珍貴史料,也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富有學術價值的古代文化瑰寶。這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匡亞明:《孔子評傳》,濟南:齊魯書社,1985年,第355-356頁。在整理六經過程中,孔子本身就為學生和社會樹立了一個學習經典、尊崇傳統的榜樣。《孔子世家》記載孔子讀《易》“韋編三絕”的事,可見他讀經之勤奮和編經之艱辛。據筆者粗略統計,《論語》中,有13次專談或采引《詩經》,74次提到禮,數次引用《書》、《易》,多次論樂。誦讀、研習《詩》、《書》、《禮》、《樂》、《易》成為他一生的精神追求和職業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孔子應該是“鄒魯之風”的開創者,也是其形成的前提和基礎。
前人早已注意到,孔子編定六經的目的之一,是作為私學教材。《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近人周予同先生說:“孔子既然設教講學,學生又多,很難想象他沒有教本。毫無疑問,對于第一所私立學校來說現成的教本是沒有的……孔子為了教授的需要,搜集魯、周、宋、杞等故國文獻,重加整理編次,形成《易》、《書》、《詩》、《禮》、《樂》、《春秋》六種教本。”*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01頁。孔子的弟子眾多,其弟子尊崇孔子,亦以孔子為榜樣,讀經習經。可以設想,在孔子生前,魯地在一定程度上就已形成一種崇禮重經的文化風氣。
應當看到,孔子去世后,魯國文風曾一度消沉。一是弟子四散。《史記·儒林傳》載:“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漢書·藝文志》引劉歆語云:“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雖然孔子死后,“弟子皆服三年”,然后“相訣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余室”,但畢竟師生相聚論學、共讀經典的昔日風光不再,魯地的文風大受影響。二是百家之學興,讀經之風消。時入戰國之后,列國紛爭,兼并戰爭激烈,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各國爭相延攬人才,催生諸子百家的形成。而各家各派學者大多“喜議政事”、“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力求投合統治者的需要。而以三代文獻為主編定而成的“六經”,因其不合時宜,則受到冷落。這也對魯地文風產生重大影響。《文心雕龍·時序》中評論說:“春秋以后,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飆駭。”正是這種情況的寫照。
第二階段:興于子思,擴于鄒。
在鄒魯之風的興起發展中,子思是一個關鍵人物。子思,名伋,為孔子嫡孫。其一生以弘揚乃祖之學,教授六經為己任,在鄒魯之地大興私學,使鄒魯之風得以興盛發展。關于子思的生平,文獻記載較少,大致說來有以下幾點:
其一,子思生于孔子晚年,曾親聆孔子教誨*據李啟謙先生考定,孔子去世時,子思12歲。李啟謙:《子思及〈中庸〉研究》,《孔子與孔門弟子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他一生以弘揚孔子之學為己任。《孔叢子·記問》記載:“夫子閑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可見,孔子晚年對子思的成長十分關注,每有閑居獨處之時,祖孫問答,即刻教誨,解疑釋惑,著力培養。《孔叢子》記孔子與子思對答共四處,涉及家事、任賢、禮樂、哲理等,內容廣泛,可見多所用心。而子思也繼承乃祖之志,以弘揚儒學為己任,成為孔子之學的正宗傳人。正如康有為所說:“孔子之道大矣,蕩蕩如天,民難名之,唯圣孫子思,親傳文道,具知圣統。”*康有為:《孟子微·禮運注·中庸注》,北京:中華書局 ,1987年,第187頁。
子思曾受孔子得意弟子曾子之教。《孟子·離婁下》曾記載說“曾子、子思同道”。《禮記·檀弓上》、《孔叢子·居衛》都記載有曾子對子思教育的話。宋儒則認為:“孔子歿,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二程語錄》,轉引自李啟謙《子思與〈中庸〉》一文。孟子則“受業子思之門人”(《史記·孟荀列傳》)。可見,子思上接孔子,下啟孟子,是孔學傳承譜系中的關鍵人物。
其二,子思做過官,但官職不高,曾受到魯、宋國君重視,做過師傅、咨詢一類虛職,大致屬于頗有聲望的“士”一類。他曾在魯穆公時為官吏。《孟子》中多次提到子思:“魯穆公之時,公儀休為政,子柳、子思為臣。”他也曾在宋國做官,但依孟子的說法,“子思,臣子,微也”。可見,子思的官職并不高。
其三,子思一生主要的事業是繼承乃祖的衣缽:讀經傳經,興學授徒,安貧樂道。《鹽鐵論·貧富》曾記載:“孔伋,當世被饑寒之患。”《說苑·立節》則記:“子思居于衛,缊袍無表,二旬而九食。”可見,他一生比較貧寒。子思興學的直接文獻資料亦較缺乏,但他一生門人眾多,應是事實。孟子即“受業子思之門人”。《禮記·檀弓下》記載:子思之母死于衛,子思哭于廟,而門人隨至,勸其不要哭于廟。另有多處記載子思與門人的對話,均可見其門人之多。
子思興學授徒,曾擴展到鄒地。這方面先秦兩漢文獻中并無直接記載,但《史記·孟荀列傳》中,既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一說,孟子就學未有到鄒之外的記載,可作一證。另外,鄒城地方文獻及林廟石刻中有多方面記載,眾多歷代遺址尚存,想必也是有歷史依據的。
鄒城現存宋代以來的林廟石刻中記載,子思曾來鄒地講學,并在鄒地寫成《中庸》。元代所修的中庸精舍,有《中庸精舍記》記其事:“舊名子思講堂,謂孟子傳道于此。”*劉培桂:《孟子林廟歷代石刻集》,濟南:齊魯書社,2005年,第28頁。此后,改為中庸書院、子思書院等,明清時代多次重修,今遺址尚存。
筆者綜合各種資料認為:在戰國初期鄒魯之風的形成發展中,子思是一個過渡性的關鍵人物。一是他將孔子去世后,因弟子各奔東西、散游諸侯,魯地一度消沉的文風重新振作起來,使之得以延續。二是他將興教講學擴充到鄒魯之地。這在戰國初期魯國國力日衰,“狀如小侯”的情況下,為鄒魯之地傳承發展儒學、培養人才、提供了支持,也為孟子的出現奠定了厚實的文化基礎。三是子思施教,以傳授五經為主。這為形成“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對《詩》、《書》、《禮》、《樂》“多能明之”的鄒魯之風形成打下基礎。《孔叢子·雜訓》載:“子上雜所習,請于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圣,……故夫子之教,必始于《詩》、《書》,而終于《禮》、《樂》,雜說不與焉。’”這說明,在戰國百家之學興,天下之士朝秦暮楚、以干世主的風氣下,面對混亂的思想局面,子思堅持“學必由圣”,排除雜說,以《詩》、《書》、《禮》、《樂》教授弟子,傳承儒學,對鄒魯之風的形成、延續和發展起了決定性作用。而事實上,鄒魯之風的形成由孔子教授六經之起到孟子崇孔讀經之興,子思是個關鍵人物。正如清代黃以周在輯錄《子思子》時所言:“求孟子學孔圣之師承,以子思為樞紐。”*《清史稿》卷482。子思所作《中庸》中,共引《詩》14篇,亦可見他對詩學的重視。
第三階段:盛于孟子,風行鄒魯。
從文獻記載的角度看,鄒魯之風的繁盛和戰國之世儒學的振興,是直接聯系并連接在一起的。而這都得之于孟子的偉大貢獻。
《漢書·儒林傳》:“天下并爭于戰國,儒學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至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這說明,在戰國早中期相當一段時間,儒學聲勢大衰,《詩》、《書》、《禮》、《樂》的傳授也僅在齊魯之地綿延不斷而已。儒學的振興,主要得力于孟子、荀卿二人。六經復傳,并推動鄒魯之地形成知識分子一代文化風氣的,則主要是孟子。原因有二:
其一,孟、荀為戰國時代振興儒學之大師,且因在齊國的稷下學宮論儒傳教,影響巨大。但孟子較荀子早半個世紀。前有孟子,后有荀子,共推儒學,顯于當世。而所謂“威、宣之際”儒學“顯于當世”,主要是孟子。根據歷代學者考定,荀子出現在稷下的時間大致不早于齊泯王時期。
其二,孟子一生,絕大部分時間生活在鄒國。其對鄒魯之地的文化影響是可想而知的。有關孟子生平事跡的材料較少,但現有歷史文獻中,大致可以這樣來分析他與鄒國故鄉的關系:第一,他在40歲之前,沒有離開鄒國的記載。總體來看,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的生活內容:一是他在鄒國接受了啟蒙教育,著名的“孟母三遷教子”的故事就是出現在這個階段。二是他在這兒從師學習,受子思影響巨大,是子思門人的學生。盡管后世學者以此認為孟子可能在魯國求學,但古代文獻中并沒有孟子在魯國或其他地方從師學習的記載,為子思之后學,與是否在魯求學是兩碼事。孟子很可能是子思及其弟子在鄒地興學的直接受教者。三是孟子曾在鄒地設教授徒。*楊澤波:《孟子生卒系年新考》,《孔孟學報》第80期(臺灣孔孟學會)。四是初仕鄒國。《孟子·梁惠王下》曾記載鄒穆公問政孟子之事,如清人周廣業在《孟子出處時地考》一文中說:“孟子之仕,自鄒始也。時方隱居樂道,穆公舉之為士。”*王其俊:《中國孟學史》上冊,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70頁。
總結來看,早年孟子之與鄒國關系大致可概括為:幼承母教,從師學習,設教授徒,出仕為宦。他的人生是從鄒國開始的。
第三,孟子在40歲到60歲的20年間,曾周游列國,于齊、梁兩大國之間奔波往復用力最多,冀有所為。孟子在鄒、魯、滕、薛、宋等國間率徒游說,傳經講學,將鄒魯之風傳播各地。值得關注的是,孟子在齊威王、宣王之時,三次游齊,在稷下學宮長駐達十數年之久,在各國與君臣交往甚廣。《孟子》一書中提到齊宣王就有23次,是所有國君中提及次數最多的。其在齊之稷下率徒講學,不治而議。但官居卿位,特受尊崇。辯說爭鳴,影響極大。在魏國,他與梁惠王大談“仁政”,希望他“省刑罰,薄稅斂”,“與民同樂”;他稱不行仁政的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在滕國,他“館于上宮”*《孟子·盡心下》。,受到很高禮遇。他勸滕文公保民而王,大講“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的道理,如此等等。可以說,孟子對“鄒魯之風”的形成發展,貢獻是巨大的:一是孟子盡其所為,所到之處,大力弘揚儒學,力挽“儒學既黜”之頹勢,重振儒風,大力提升了鄒魯之風的影響力。二是培養了大批“鄒魯之士”。同時,孟子講學始于鄒魯,其弟子大多為鄒魯之士。*劉培桂主編:《孟子志·孟子弟子考述》,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孟子出游,從者如云,“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孟子·滕文公下》。,這實際上為鄒魯之風的發揚光大,培育了數代傳承的生力軍。
第四,終老鄒國。根據大多數前人研究的成果,大致說來,孟子自60歲左右直到84歲去世,晚年20余載主要是在故鄉鄒國度過的。其晚年對鄒魯之風興盛發展的推助及影響甚大。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其晚年以研究《詩》、《書》、《禮》、《樂》為主業,對鄒魯士風影響極大,《史記·孟荀列傳》云:(孟子)“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史記考證》引清人梁王繩語:“七篇中言《書》凡二十九,援《詩》凡三十五;故稱敘《詩》、《書》。”趙歧《孟子題辭》亦說:孟子晚年,“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于《詩》、《書》”。《莊子·天下篇》所言:“《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能言之”,與孟子晚年與眾弟子萬章等人在鄒地的《詩》、《書》活動有極大關系。其二,晚年教授大量生徒,為鄒魯之士的大量產生做出突出貢獻。孟子晚年生平情況文獻記載不詳,但其廣招弟子,講經授徒是可以肯定的。從文獻記載看,萬章、公孫丑之徒是其晚年不離左右的弟子,后世學者多認為:“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韓昌黎文集·答張籍書》。孟子曾說:“君子三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教育天下英才為三樂之一。天下英才集中于前,可見其晚年學生數量多,來源廣。孟子以此為樂事,估計其晚年教育成就之大,自己是很滿意的。
孟子是孔子之后傳承、弘揚、發展孔子儒學影響最大的學者。他不僅對孔子尊崇備至,而且也以捍衛弘揚孔子之道為其一生最主要的歷史擔當。孟子認為:“自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余歲,云圣人之世如此其未遠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孟子·盡心下》。而要擔當起這一歷史重任,“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后世學者從東漢趙岐到韓愈也都對孟子在儒學特別是對先秦孔子儒學發展中的獨特地位給予中肯的評價,稱“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韓昌黎文集·送王秀才序》。。因而,觀戰國之世儒學及百家之學發展,孟子實為儒家學派挽頹勢、開新局的中興之巨人。自其同時代稍后的學者莊子《天下篇》始,孟子已成為戰國儒學的代表。故在《天下篇》中“鄒魯”并稱孔孟之鄉,鄒、魯并稱,鄒在魯前,實因孟子。這是戰國儒學發展的時代印記,也是孔孟故里區域文化發展的歷史軌跡——儒學因孟子而興,鄒國因孟子而名世,“鄒魯之風”因孟子而達于繁盛。
四、“鄒魯之風”的發展演變
縱觀從孔子到孟子“鄒魯之風”的形成、發展過程,結合《莊子·天下篇》及先秦文獻對“鄒魯之風”的有關記載,筆者認為:在戰國之世形成的所謂“鄒魯之風”,實際是一種士風,亦即在鄒魯之地形成的一代知識分子的時尚風氣。這種士風的文化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它是一種以“述唐虞三代之德”為己任,堅守傳統,弘揚傳統的風氣。也就是說,它是以歷史擔當精神,對上古三代以來形成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堅守、傳承和弘揚。孟子“言必稱堯舜”,鄒魯之士對三代以來的經典文獻《詩》、《書》、《禮》、《樂》熱衷研習、傳誦,以致形成了一種鄒魯士人共同創始的獨特文化風氣。戰國時代,社會巨變,戰爭頻繁,“士風”的主流是熱衷政治,競逐功利,著書立說,游說諸侯,迎合時尚,以干世主。鄒魯之風顯示的卻是一種特立獨行的社會風氣,不合時俗,卻為民族文化的傳承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其二,它是一種尊崇孔子、弘揚儒學的風氣。孟子以“私淑孔子”自道,以“乃所愿,則學孔子也”為人生追求的目標,以孔子編定的六經為教材,“聚天下英才而教之”。鄒魯之士,對《詩》、《書》、《禮》、《樂》獨“能言之”,這在戰國中期,列國紛爭,“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飆駭”的大環境下是一種獨特的文化景象。從戰國儒學發展講,鄒魯則是弘揚孔子儒學、培育儒家學者、堅持傳播和發揚儒學的一個大本營和文化基地。
其三,它是一種崇尚道德教化、宣揚修身養性之風。鄒魯之士研修《詩》、《書》,深挖圣王先賢的“圣德”,以為自己的楷模和榜樣。孟子道性善并專講仁、義、禮、智四端之說,倡言以身示范,立志要做“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大丈夫。《孟子》中38次引用《尚書》*劉起玗:《尚書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49頁。,引《詩》35條,大力宣揚 “養浩然之氣”。孟子說:“唯有德者,然后能金聲而玉振之。”他認為鄒魯之士的時代使命就是要在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社會環境下,大力弘揚傳統美德。“正人心,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以承三圣者”,這是孟子所極力宣揚和堅持的,也是鄒魯之風所體現的一種道德精神。
其四,它是一種知識分子堅持理想、壯志有為的風氣。由孔子到孟子,歷覽鄒魯之風形成的精神發展過程,都體現著一種胸懷天下、積極入世、奮發有為的人生態度。孔子及其弟子、子思、孟子是這樣,鄒魯之士也是以此精神為主體的這樣一個知識分子群體。而由這樣一個群體形成的士風,也同樣充溢著這樣一種“士”的精神。孟子之所思所想即是:“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以積極的人生態度,投身其中,“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孟子· 盡心下》。。甚至周游列國,四處碰壁,有志難申之時,則“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史記·孟荀列傳》。。堅持理想,獨行其道,這反映出以孟子及其弟子為主體的鄒魯之士的共同精神面貌和風氣時尚。
以如上四點為主要內涵特征的鄒魯之風,在戰國至秦漢的歷史變遷中傳承發展,與時俱變,蔚然成為鄒魯之地一種獨特的文化景象。這種變化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由士風到世風。即由知識分子風氣演變為鄒魯之地的社會風氣。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既歿之后,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這說明孟子去世之后,特別是經秦始皇“焚書坑儒”,鄒魯之風有可能受到了摧殘。但鄒魯之風并未泯滅。一是士風延續,斷而未絕。《史記·儒林列傳》記載秦末農民起義中鄒魯之士的活動情況,其中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之事,足見鄒魯之風在暴秦之世的堅守;又記載“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的文化景象,兵臨城下,依然書聲朗朗,弦歌不絕,亦可見鄒魯之士在惡劣的社會環境中,依然有著堅守傳統、光大鄒魯之風的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二是影響所及,向世風轉化。《史記·貨殖列傳》:“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于禮”,“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史記· 貨殖列傳》。。這說明,好儒之風,到秦漢時,已從知識分子的“士風”逐漸演變為鄒魯之地的民風民俗。鄒魯以其尊孔好儒,風行詩書禮樂,已成為鄒魯異于他邦社會的文化景象。
第二,由鄒魯影響到全國。由于孟子及思孟學派的大力推動,鄒魯之風在戰國時代已遠播全國,深深影響了戰國諸子百家爭鳴的發展。
一是孟子率鄒魯弟子周游列國,“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孟子力倡仁政,傳播儒學,弘揚鄒魯之風的文化精神,使區區小國之鄒,因孟子而名揚天下。“鄒魯”遂成為儒學故鄉之代名,由此推高了儒學在戰國諸子百家中的“顯學”地位,大大提升了鄒魯之風在諸子爭鳴中的影響力。
二是鄒魯之風勁吹稷下。孟子帶萬章、公孫丑等弟子,三次游齊,與齊宣王及稷下先生多有論辯,大力推行仁政主張。他長住稷下學宮達十數載,官居卿位,待遇優厚,備受尊崇,與稷下各派學者爭鳴、交流、辯說、研討,推動了鄒魯之風與稷下之學的交匯、融合,促進了齊、魯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及儒學在齊地的傳播。戰國之時,稷下成為諸子百家爭鳴的學術中心,前有孟子,后有荀子,光大儒學,助推了諸子學術爭鳴。而齊魯之地則南有鄒魯之風,北有稷下學宮,共同營造出戰國學術文化的“重心”地位。
三是鄒魯之風遠播長江南北。從孔子到孟子,鄒魯之風如何影響傳播到長江流域,歷史文獻中相關資料并不多。《孟子·滕文公上》中記載孟子的話說:“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于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這是有關荊楚學者北學孔孟之道、感受鄒魯之風,從而南傳長江流域的一則間接記載。陳良是否來鄒魯之地或求學于孟子,該篇記載不詳,但卻記載著楚人學者許行和陳良及其弟子陳相與其弟陳辛等數十人在滕國與孟子辯仁政、論農家之事。滕為鄒之鄰國,又是孟子率徒久住論學之處,我們說,有大批的楚地學者來鄒魯之地求學,與鄒魯之士談經論道,將鄒魯之風帶回長江荊楚之地,應在情理之中。戰國鄒魯之士是否到長江流域傳經說儒,雖然所見文獻的直接記載不足,但是,史載孔子的弟子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史記·儒林列傳》也有“澹臺子羽居楚”的記載。可見,鄒魯之地的孔門后學曾大批南下長江一帶,恐怕從孔子時代就已開始。《呂氏春秋·去宥》有“荊威王學《書》于沈尹華”的記載,沈尹華為何處之儒家學者,史無詳考,但楚國威王學《詩》、《書》、《禮》、《樂》應有儒家學者教之,其中應有鄒魯之士。總之,僅從文獻典籍考察,鄒魯之士將“鄒魯之風”傳播至長江流域是完全可能的。
20世紀90年代,在湖北荊門郭店楚墓中出土的一批戰國中后期的竹簡及其釋文的發表,為鄒魯之風遠吹長江流域荊楚之地提供了新的證據。這些竹簡中有14篇為儒家著作。李學勤先生認為,郭店楚簡的“這些儒書都與子思有或多或少的關連,可說是代表了由子思到孟子之間儒學發展的鏈環”*李學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發現》,《中國哲學》第20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對于簡書《五行》篇,龐樸先生認為“經部是子思所作,說部是孟子后學的綴補”。陳來先生結合《荀子、非十二子》中的“子思唱之,孟軻和之”,進一步提出“《五行》說文為孟子所作”*陳束:《〈五行〉經說分別為子思孟子所作論》,《儒家思孟學派論集》,濟南:齊魯書社,2008年,第32頁。。其中出土竹簡《緇衣》即出自《子思子》,已是絕大多數郭店竹簡研究學者的共識。*梁濤:《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32-233頁。而《緇衣》中“簡本保留戰國中期的特點,引文只引《詩》、《書》”*周桂鈿:《郭店楚簡〈緇衣〉校讀札記》,《中國哲學》第20輯。。郭店竹簡的出土,為鄒魯之風傳至長江流域,提供了探討的路徑。
鄒魯之風怎樣吹到長江岸邊?杜維明先生有一段話值得我們分析思考。他說:“郭店出土的資料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這次出土的資料可以認為是先秦時期一個精致的圖書館里的材料。郭店一號楚墓的墓主,現在認為是‘東宮之師’,也就是楚國太子的老師,他應該是當時水平很高的知識分子。”
杜先生的推導給我們打開了一扇門窗,讓我們看到了鄒魯之風吹綠江岸的美妙圖景。這個“水平很高的知識分子”,不知其名,但極有可能是一個飽學的鄒魯之士。理由有三:一是從竹簡的內容看,儒學的著作共14篇,而其中主要的是思孟學派的著作。這個時期,正是在子思及其門人和孟子推動下,鄒魯之風的極盛時期,一位鄒魯之地的儒學大師當了“東宮之師”最具可能。二是從《五行》的作者即是子思與孟子來說,可能從子思到孟子,在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鄒魯之士持續地傳播儒學于長江流域,使鄒魯之風在戰國之時即重現江南。三是從《緇衣》內容多引《詩》、《書》看,所謂鄒魯之風傳布江南,實際是再現了從子思到孟子講學授徒重《詩》《書》的傳統,是以鄒魯之士“多能明之”的《詩》、《書》、《禮》、《樂》在楚地落地生風為主要體現的。這更顯示出,鄒魯之士在江南復制了鄒魯之風的歷史。
從郭店竹簡發現的思孟學派有關活動情況,結合《莊子· 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綜合分析,大致可以看出,戰國時期鄒魯之風形成的骨干力量——鄒魯之士,實際即是思孟學派的廣大成員。他們根植鄒魯,活躍四方,西至中原,南到長江,是推動鄒魯之風吹向全國各地的骨干力量。《荀子·非十二子》中記載荀子批判思孟學派:“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于后世。”這段話,以思孟學派在鄒魯之風形成發展中的一種文化影象來理解,會找到更好的注腳。荀子在這里,以激烈的言辭抨擊思孟,說他們那些“言必稱堯舜”,自稱是傳承“真先君子(孔子)之言”的學說,由子思首倡在前,孟子呼應在后,這個前后近百年的“唱和”,是以那些“嚾嚾然不知其非”的世俗之儒,“受而傳之”,推波助瀾的。這些“世俗之溝猶瞀儒”,實際即指那些對“《詩》、《書》、《禮》、《樂》多能明之”的“鄒魯之士、縉紳先生”。而被荀卿指斥的思孟學派的“俗化”,正是指的鄒魯之風將孔子之教義,將《詩》、《書》等經典推向大眾化、社會化和風俗化的過程。這是思孟學派的特征,也是鄒魯之風在先秦儒學發展中的巨大貢獻所在。郭店楚墓中儒簡的出土,佐證了《荀子·非二十子》中對思孟學派特征的描述,也證實了鄒魯之風強勁的文化傳播力。
戰國時代,鄒魯之風是先秦儒學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它的發展演變為儒學的廣泛傳播,在西漢時期上升為國家和民族的統治思想,為秦漢以后不絕于史的“鄒魯之風”在全國各地的落地生風,奠定了堅實基礎。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Ethos of Zou and Lu (States) ”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ang Zhimin
(Institute of Qilu Cul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250014)
As two ancient states of different cultural origins in the east of China, Zou and Lu have undergone a binary whole or two-in-one evolution in culture to become a regional culture with the “ethos or common practice of Zou and Lu” as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age through it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characterized by Confucius-worship, Confucianism-worship, reading and passing on its classics as its main characteristics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t traced back to Confucius, and began in Lu state; gave rise to by Zisi, and spread in Zou state; and flourished in the time of Mencius, and was predominant in Zou and Lu, and finally became a common practice of the world from that of the scholar-bureaucrat, and was spread and influenced the whole China. Viewed from the relevant activities of the Mencius-recollecting (Simeng) school found from the Guodian Chu-tomb bamboo slips, and combined wit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anxia (land under heaven) in Zhuangi and Fei Shierzi in Xunzi, it is evident that, the scholars-bureaucrats of Zou and Lu, or the backbones of its formation, are ,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numerous members of the Mencius-recollecting (Simeng) school. They were from Zou and Lu, but active everywhere, as far as to the Central Plains in the west and to the Yangtze River down in the south, thus spreading it all over China. And it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e-Qin Confucianism, and has laid down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taking root in the whole of China of the “ethos or common practice of Zou and Lu” which is ever present in history.
ethos or common practice of Zou and Lu; Confucianism; cultural transmission
2015-04-11
王志民(1949—),男,山東淄博人,山東師范大學齊魯文化研究中心首席專家,教授,博士生導師。
①本文為作者主持研究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課題“齊魯文化與周秦文明重心的演變”(08BZS006)的階段性成果。
K231.03
A
1001-5973(2015)03-0021-12
責任編輯:李宗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