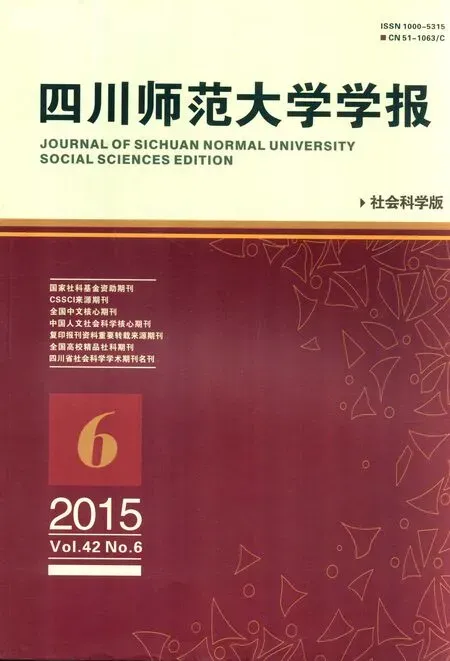河伯神話流變考釋
李 進 寧
(四川師范大學 文學院,成都610066)
關于河伯神話的源流問題,學界長期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王孝廉[1]、李立[2]等學者主張夏族集團說,何光岳[3]、林河[4]等主張東夷集團說。造成這種分歧的原因,主要是河伯神話在流傳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帶有濃郁民族和地方特色的不同稱謂,如馮夷、冰夷、無夷等。我們擬從文化和文獻角度對河伯神話源流略作梳理,以就教于方家。
一 河伯史實考
文獻載有河伯族人與其他民族的沖突和戰爭。《初學記》引《歸藏》說:“昔者,河伯筮與洛伯戰而枚占,昆吾占之:不吉也。”[5]48河伯族人為了拓展生存空間和掠奪更多人口,打算進攻洛伯族人,但戰前卜筮的結果對己方不利。《竹書紀年》記載,夏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斗”[6]20。洛伯族人與河伯、馮夷二族聯盟發生戰爭,反映了當時諸族中原逐鹿的歷史事實。可知,有夏之時,河伯族已居于河洛之地,并且為爭奪生存空間進行殊死搏斗。隨后河伯族的勢力逐步增強,其他部族如殷侯亦曾假借“河伯之師”討伐與自己不共戴天的有易族,“殷主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也”[6]22。這說明此時的河伯族人已經具有一定的經濟、軍事實力以及強大的號召力和影響力。
那么,河伯族是原始土著還是異地來客?河南二里頭遺址的考古發現解決了這一長期懸而未決的歷史問題。考古專家根據相關出土文物的碳-14測定,確認曾經生活于此的河伯族具有明顯的夏文化特征,而出土陶器等文物則具有大汶口文化的身影[7]。眾所周知,發現于山東泰安的大汶口文化已被認定為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是典型的東夷文化的代表。因此,據出土文物和傳世文獻綜合考察,可以確定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和東夷文化交流與整合的產物,而東夷文化的傳播者應當是經過戰爭和聯姻而占據河洛的河伯族人。他們憑借武器精良和英勇善戰,獲得了河洛的控制權,并且不失時機地把自己的風俗習慣、文化信仰等移植于此。另據何光岳考證[3]267-285,在夏代之前,河伯族人曾幫助大禹在黃河下游治水,并贏得廣泛稱譽和尊敬,河伯族人因此乘勢一路向西,把自己的勢力擴大至河洛之地。在經歷無數次沖突甚至廝殺之后,“最終兩族之間達成和解并結為秦晉之好,繁衍生息于河、洛之地”,這種“和親”聯姻方式促成了他們之間暫時的和諧穩定局面[8]149。于是,河洛一家,相安無事。但是,隨著河洛文明的繼續發展,東夷族一個分支——有窮夷羿攜弓負箭由黃河下游沿河而上,摧城略地,勢如破竹。在激烈爭奪之后,夏后太康失國,而與之輔車相依的河伯族也岌岌可危。隨后,有窮夷羿乘勝強掠河洛之地,追殺河伯并霸占其妻洛嬪。屈原《天問》對此疑慮重重:“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嬪?”[9]99這段歷史的文獻記載,在人們的心目中逐漸分化和變異:一方面,以這段歷史為原型,在河伯原有圖騰崇拜的基礎上,于口耳相傳的過程中演繹出曲折動人的神話故事;另一方面,遭到重創的河洛之民作鳥獸散,奔走呼號,他們銘記先祖的榮耀與輝煌,懷抱生的希望與信念,沿著陌生路途尋找自己的安身之所,訴說先祖的英雄業績和對故土的留戀,形成了對列祖列宗的遙祭。
商周之際,河伯族人對周部族立國撫民功勛卓著,贏得了周王朝的信任和器重。周穆王時,河伯酋長掌管著周王朝祭祀河神的大任。“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夭受璧,西向沉璧于河,再拜稽首。”“河伯號之帝曰:穆滿,女當永致用時事。”[10]204河伯酋長在周王的授意下召集王公大臣向天言事,在神圣肅穆的祭祀儀式中表達“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11]797的家國理念。因此,王夫之認為“河伯,古諸侯,司河祀者”[12]53,是符合歷史事實的。日本學者白川靜也稱:“河伯的祭祀原先好像是一個擁有特定傳承的氏族的一種特權,被視為能夠支配自然節奏的特定山川的信仰和祭祀。經常是和一個特定的氏族結合在一起,這些掌山川信仰與祭祀的特定氏族即是所謂的神圣氏族。”[13]100因此,當時的河伯族在國家特權的庇蔭下獲得了長足發展。
二 河伯神話考
學術界認可“河伯之說,本遠古相傳神話”[14]69的觀點。縱觀河伯族的發展歷程,不難發現圖騰化時代早已離他們遠去,因而僅從稱名上已無從尋找到自然神的蹤跡。《初學記》引《援神契》釋河伯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5]119根據約定俗成的解釋,“伯”具有陽性特征,“河伯”當為陽性神。據此可推測河伯族已進化至父系氏族社會。他們或許率先脫離東夷集團走向更為廣闊的生存空間,憑借其發展優勢,在河洛之地稱雄一方。
但是,太康失國,有窮夷羿對河伯族人進行了無情的殺戮。面對死亡的掙扎、心靈的創傷,原始思維和萬物有靈觀念極易激起他們對逝去靈魂的追憶,他們通過曲折離奇的神話傳說渲染詮釋先祖功勛,體現永志根本之意。王逸在注解《楚辭·河伯》時所引古老傳說最具說服力:“河伯化為白龍,游于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曰:‘為我殺羿。’天帝曰:‘爾何故得見射?’河伯曰:‘我時化為白龍出游。’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犯?汝今為蟲獸,當為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歟?’”[9]99河伯化為白龍,被夷羿射瞎左眼,訴諸天帝,天帝沒有為他伸張正義。這則流傳于南方的神話故事,已經具備非常完整而生動的故事情節和文學色彩。不僅如此,這則神話故事還傳達其他一些信息:河伯是水中神靈的守護者,它已經脫離了自然神的“蟲獸”之類,達到了神話發展的較高形態。我們還可以溯源而上,尋找更為古老的演變原型。西漢劉向《說苑·正諫》記載:“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15]237這可視作王逸注說的淵源。《莊子·外物篇》亦稱:“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發窺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16]933可見,關于河伯的神話在周時流傳甚廣。由于吳楚神話和莊子所記均有“魚”、“鱉”等水族形象和“漁者”的身影,這樣河伯神話原型便更加清晰地展現在我們面前。先秦其他文獻關于河伯故事的記載亦甚夥。《晏子春秋》載:“齊大旱,景公召群臣問曰:‘寡人欲祀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鱉為民,彼獨不欲雨乎?祀之何益。’”[17]56此處河伯具有“主雨”的神性,對河伯的祭祀表現了人們冀神賜福的功利目的。雖然晏子極力反對祀河伯,卻反映了自然神的客觀存在。另外,齊國勇士古冶子殺黿和《韓非子》所記“河伯,大神也”[18]218均具此種性質。即使河伯的侍從也具有水族類的標識。《古今注·魚蟲》載:“鱉名河伯從事。”[19]128《初學記》引《南越記》曰:“烏賊魚,一名河伯度事小吏。”[5]742從以上記載可知,人們認為“魚”“鱉”乃河伯魂附之物,而諸多水族之屬前簇后擁,伴隨左右,則表明河伯具有動物的某些特征,這為我們把河伯定位為自然神提供了依據。
趙輝認為:“神話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表現為不同的形態。它有一個由動物神到半人半神、再到人格神的發展歷程。”[20]75河伯與“魚”的關系,我們也可以視其為河伯族人的自然神話。這也恰恰驗證了王孝廉所說:“古代人最初信仰的神,是他們生活周邊的敬畏或具有實益的動植物和自然現象,其后隨著人的自覺意識的提高,人們所祭祀的神也逐漸由完全的動植物等轉化為半人半獸的神。”[21]45《尸子》所描寫的河神即為人面魚身,具有半人半神的神格特征。“禹理水,觀于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22]167《酉陽雜俎》亦載:“河伯人面,乘兩龍,一曰冰夷,一曰馮夷。又曰人面魚身。”[23]77這些記載說明,河伯除了具有魚的特性,還有人的性格和面貌,實現了從純動物向人面魚身的過渡。這是神話形態的一種飛躍,是古人思維模式的重大轉變與革新,是人類文明的進步與升華。
由上可知,春秋戰國時期的河伯神話已經廣泛流傳并深入人心,而且其神格已經擺脫原始意義的神話色彩,具有了人的思想和情感。《莊子·秋水》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16]561河伯與海神若的一番辯論,體現了智者之思。而真正把河伯形象在歷史和神話基礎上進行藝術加工并糅合在一起的當是楚人屈原。屈原因讒見疏,被貶于湘、沅之地,目睹世俗所祭,遂作《河伯》以寄哀怨之情和鴻鵠之志。“與女游兮九河,沖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登昆侖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為兮水中,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游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9]76-78河伯與南浦女乘上水車,駕馭螭龍,逍遙自在地神游昆侖之墟,而后閑庭信步于龍堂朱宮,此種閑情逸致表現了詩人在河伯形象上所寄寓的某種理想或情愫。然而,南浦送別,執手相看淚眼,不免使河伯徒增幾分憂傷和落寞。詩人通過對河伯內在神性和外在形象的描繪,完成了河伯人格化和理想化的蛻變。這樣,屈子筆下的河伯神話已經具有人格神的特質,標志著它已步入了高級形態神話的發展階段。
三 馮夷、冰夷、無夷等神話傳說考釋
從文獻記載看,“河伯”還有多種稱謂,如馮夷、冰夷、無夷等,這些稱謂應當存在內在聯系。《山海經·海內北經》載:“昆侖虛南所,有氾林方三百里。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一曰忠極之淵。”[24]369這里的“冰夷”具有人面、乘兩龍的神態特征,說明它已經發展到了半人半神的自然狀態;所居之地為“從極之淵”,從地理特征看,應在陽紆和陵門山一帶,即今渭河下游和黃河河曲一帶,它應是當地的水神。那么,這個半人半神的冰夷又是如何產生和發展演變的呢?
李立認為:“在先秦文獻所記載的河神話傳說中,有河伯神話,有冰夷傳說,河伯與冰夷相合者并不多見。”[25]52可見,冰夷神話傳說自成體系。但如果對“冰夷”稱名略作分析,不難發現其與“河伯”具有同質性。先看“冰”字。許慎《說文解字》:“冰,水堅也,從仌,從水。”[26]240我們把“冰”與“馮夷”的“馮”的語源學結構做一比較。《說文解字》:“馮,馬行疾也。從馬,冫聲。”[26]200左邊兩點是“冰”,做“馮”的聲部。檢《宋本廣韻》“馮”“冰”同屬下平十六“蒸”韻之“憑”韻部[27]179,古音中兩字是極為接近的。因此,《山海經》中的“冰夷”極有可能就是“馮夷”。再看“夷”字。“夷”字蘊含著濃郁的地域性和族源性色彩。《周禮》:“東方曰夷,被發文身。”[28]2637《大戴禮記》:“東辟之民曰夷。”[29]162《說文解字》:“夷,東方之人也。”[26]8《竹書紀年》亦載,天下九夷彼此消長,榮衰于中原與邊疆,“后芬發即位,三年,九夷來御”[6]19。《后漢書·東夷傳》:“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30]2807從文獻看,九夷形成于山東半島,隨著東夷逐漸強大,東夷一些支族陸續遷移至周邊區域,甚至于黃河上游,最后畛域漸消,文化信仰也融合于華夏族。“夏侯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武乙衰敝,東夷浸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30]2808由此可知,冰夷即為馮夷,與河伯同出東夷。關于馮夷的神話傳說流傳也頗廣,如《淮南子》:“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云車,入云蜺,游微霧,騖怳忽,歷遠彌高以極往。”[31]8《水經注》引《括地圖》稱:“馮夷恒乘云車駕二龍。河水又出于陽紆凌門之山,而注于馮逸之山。”[32]3這里的馮夷“乘云車,駕二龍”與冰夷“人面,乘兩龍”異常接近,因此郭璞注《山海經·海內北經》曰:“冰夷,馮夷也。”故我們更有理由相信“從極之淵”就是馮夷(冰夷)神話傳說產生和流傳的發源地。當然,隨著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使它在獨立發展的同時,也逐漸融入他族文化。這進一步說明,部族文化的相互滲透和兼容,仍然裹挾著最初的地域風貌和原始文化內涵。正如李誠所說:“神話傳說的特點之一,即在于流傳過程中,幾乎任何一個故事都會產生一些異說、歧說。但是既然產生于一個母體或母本,也就有極大可能在典籍和口頭傳說中不知不覺留下其內在的可能是帶有規律性的共同點和聯系。”[33]8所以,諸多典籍多以“馮夷”稱代“冰夷”。如《楚辭·遠游》:“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9]8《莊子·大宗師》:“馮夷得之,以游大川。”[16]8這種稱名一旦形成,便深入人心,在流傳中很難從部族的記憶中抹去,這種半人半神的神格給予我們無盡的想象和深思。
關于“無夷”,學界一般認為它是東夷集團所屬方國——當時生活于黃河下游的部族“蒲夷”的別稱。《山海經·北山經》:“又北五百里,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多蒲夷之魚。其上有玉,其下多青碧。”[24]118《西山經》:“冉遺之魚,魚身蛇首六足,其目如馬耳。”[24]73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九卷引此經作無遺之魚,疑即蒲夷之魚也,見《北次三經》碣石之山下;蒲、無聲相近。夷、遺聲同。”[24]74據此,“無夷”或即“蒲夷”。當蒲夷之民沿河西遷之后,也把自己部族的信仰帶到了河渭之地。《穆天子傳》:“戊寅,天子西征,騖行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10]58這一方面說明河伯無夷稱名上已經統一、無夷文化信仰已經隸屬于河伯文化的事實;另一方面說明穆王西征時曾經到達河伯無夷所居的陽紆山,而這里正是河伯無夷祭祀河源的圣地,也是他們通向傳說中的昆侖山的必經之地。《淮南子》:“禹之為水,以身解于陽紆之河。”[31]1317據“河伯無夷”之連稱,可知此時的民族風俗和文化信仰已經完全融合并同化于河伯文化信仰。
綜上,馮夷、冰夷、無夷等部族在民族融合之前均有一個相對獨立的發展時期,他們散居于黃河沿岸,形成不同的神靈崇拜和神話傳說。雖然名稱各異,情節有別,但他們又都從屬于東夷集團,擁有大體相同的神靈觀念。正如何新所說:“在原始先民的文化中,神話并不是一種單純想象的虛構物,一些或有趣或荒謬的故事。神話本身構成一種獨立的實體性文化。神話通常體現著一種民族文化的原始意象,而其深層結構,又轉化為一系列觀念性的母體,對這種文化長期保持著深遠和持久的影響。”[34]289因而其神靈的神態特征和生活習性,大都與黃河相關,這些自然神可以視為其方國的起源神。白川靜總結道:“當時散布在黃河及其支流的民族,各有各自的洪水神話與祭祀的水神及各別的祭河儀式。”[13]100隨著東夷西進、西夏東上步伐加劇,以及兼并戰爭愈來愈頻繁、民族融合步伐越來越快,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逐漸融為一體,如河伯馮夷、河伯無夷等稱謂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展而來的。
四 河伯神話與其他神話的整合與發展
河伯神話源遠流長,在長期的民族遷徙、斗爭和聯姻中逐漸形成了以河伯文化信仰為主、其他諸夷文化信仰為輔的兼容并包的格局。這不僅有利于多民族國家的祭祀活動,而且有利于部族的多元發展。我們所看到的河伯形象更多地體現了華夏各族由原始野蠻走向文明開化、由多神走向一神、由分散走向統一的歷史趨勢。史實證明,禹夏之時,河伯諸神話已經出現了重組與整合的端倪。如《竹書紀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斗。”[6]20《穆天子傳》:“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10]58這些記載說明馮夷及無夷族已經遷徙至中原腹地,在族際間的文化交融中,占絕對優勢的河伯文化以其強大的吸引力和包容性,覆蓋了馮夷和無夷的文化信仰,出現了二者連用的稱名。這種聯合方式在共同發展中保留了各自的特質,他們共同承載了不同的文化積淀。這是黃河流域各部族相互斗爭和融合的結果,也是他們在經濟或文化方面共通和互補的迫切需要,更是社會發展不斷前進的必然選擇。
經過多次民族大融合,河伯文化得到了長足發展,在夏、商、周三代較為正式的國家祭祀中,河伯神往往作為國家整體概念上的主宰神靈出現在祭祀場合,儼然成了一個國家同宗共祖的標志。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中國早期神話一個明顯的特點:即神話演變中的那種巨大的內聚力,它以神格為中心,將其相似和相關的內容加以改造而向它聚合。但是,后來隨著社會的發展,神話人物逐漸定型化,功能越來越明確,那種模糊性、交叉性逐漸消除,代之以職能性的專職神的產生。”[35]87這種趨勢一直延續到秦并天下,隨著諸侯咸服,天下合一,始皇帝命令祠官按照常奉次序祭祀天地諸神,其中有“水曰河,祠臨晉”之稱,這里用“河”代替帶有地方色彩的“河伯”或“馮夷”,使之更具整體概念意義,顯得更為莊重和神圣。到漢宣帝時,更具抽象意義的“四瀆神”被正式列于國家祭典。這樣,長期以來具有恤民安國之稱的驕子形象的河伯逐漸退出歷史舞臺,隱去曾經耀眼的光環,落拓于鄉間野舍,最終在佛道的巨大影響下華麗轉身:或附于懲惡揚善的娑竭龍王之身,接受民間的禱告和朝拜;或離開神話傳說的桎梏而羽化登仙,在虛無縹緲的天國尋找自己的神龕。誠如宋趙彥衛所說:“《史記》西門豹傳說河伯,而《楚辭》亦有河伯祠,則知古祭水神曰河伯。自釋氏書入中土有龍王之說,而河伯無聞矣。”[36]178從河伯在中原的發展情況看,這種說法具有一定的歷史根據,也是合乎歷史邏輯的。然而,河伯馮夷神話的仙話化則是在道家及道教思想的改造下完成了歷史使命。
秦漢魏晉時,道家仙術蔚然成風,人們試圖通過對古代神話故事的改造,來演繹羽化登仙、長生不老的人生。因此,他們對河伯馮夷神話進行了刪改和增補。首先,將尚未完全人格化的神改造成形神兼具的人,這些神祇擁有了名姓和籍貫。其次,由原來半人半神改造成不食人間煙火的仙人形象。《后漢書·張衡傳》李賢注引《龍魚河圖》:“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30]1925《楚辭》王逸注引《抱樸子·釋鬼》:“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9]78又引《清泠傳》:“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于河而溺死,一云溺死。”[9]78《搜神記》卷四:“弘農馮夷,華陰堤首人也。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又《五行書》曰:‘河伯以上庚辰日死。不可治船遠行,溺沒不返。’”[37]8這些記載向我們展示了河伯馮夷仙話的形變及演化過程:他是弘農華陰人,也就是冰夷神話傳說的發源地,他或溺河而死成為水仙,或修行得道服藥成仙。在道教的大力改造和重組中,河伯馮夷終于得道成仙,順利完成了由神話傳說向仙話的過渡。這樣,具有濃厚仙話色彩的河伯馮夷終于跳出了神話傳說的藩籬,走向了新的歷史舞臺。為了抬高河伯神的地位,道教還給它安排了神位。《真靈位業圖》曰:“太清右位:河伯。”[38]84《歷代神仙通鑒》卷十五:“黃河:澄靜尊神河伯。”[39]848河伯的使者也被《神異經·西荒經》描寫成白衣玄冠如風似飛:“西海水上有人乘白馬,朱鬣白衣玄冠,從十二童子,馳馬西海水上,如飛如風,名曰河伯使者。”[40]96至此,神話中的河伯形象在人們虔誠的禱告中堂而皇之地走向了仙話世界。
五 結論
由上述考證可知,河伯神話傳說的發生發展及逐漸淡出人們視野的過程,正是人類社會從萬物有靈的圖騰崇拜到歷史意識和主體意識逐漸覺醒的過程,它昭示著原始信仰的終結和宗教熱情的冷卻,也說明“人類由多神崇拜到一神崇拜,由對自然神的崇拜到祖先神的崇拜,又由祖先神的崇拜發展到對本族英雄的崇拜,是同生產力和社會發展相適應的”[41]138規律。同樣,在夏、商、周三代由河伯族人所主導的以河神為尊的國家祭祀,也是這種規律的客觀反映。不可否認,入主中原前,河伯神話傳說是從東夷集團裂變而生,充其量它只是原始意義上的自然神話,是萬物有靈觀念的產物。但是,當它走向中原腹地,同其他部族密切聯合形成了新的共同體之后,也就形成了新的民族意識和文化信仰,尤其是舉族生死存亡之際,更能激起他們的民族認同感,因而又形成了半人半獸或者完全意義上的人格神的神話。
縱觀典籍所記,河伯化為白龍遭射以及屈原所刻畫的“乘水車、駕兩龍”的河伯形象,馮夷“乘云車、駕二龍”與冰夷“人面、乘兩龍”的神態勾勒,均有著相似的特質和容貌,不得不使人認為他們就是融各部族神話傳說于一身的河伯神話。而那些不同的稱名,則反映了他們在重組、整合與發展過程中,并非簡單地以一種文化取代另一種文化,而是兩個或數個不同文化圈的文化元素的交融與組合。因而,從社會發展規律來看,河伯神話的進一步發展和流傳就是華夏各民族彼此融合與發展的縮影。隨著秦朝一統天下和佛教進入中土,各種意識形態也在相互碰撞中尋找著自己的歸宿,由于統一的多民族文化信仰的共同需要,河伯的宗主地位遭到了質疑、排擠,進而被更具抽象意義的“四瀆神”所取代。
[1]王孝廉.中國的神話與傳說[M].臺北:聯經出版社,1977.
[2]李立.文化整合與先秦自然神話演變[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3]何光岳.東夷源流史[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
[4]林河.《九歌》與沅湘民俗[M].北京:三聯書店,1990.
[5]徐堅.初學記[M].北京:中華書局,1962.
[6]李民,等.古本竹書紀年[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7]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河南堰師市二里頭遺址中心區的考古新發現[J].考古,2005,(7).
[8]李進寧.論“河伯”形象的文化意蘊[J].文藝評論,2014,(10).
[9]洪興祖.楚辭補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0]山海經·穆天子傳[M].郭璞注,張耘點校.長沙:岳麓書社,2006.
[11]《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12]王夫之.楚辭通釋[M].北京:中華書局,1975.
[13]〔日〕白川靜.中國神話[M].王孝廉譯.臺北:長安出版社,1983.
[14]劉永濟.屈賦通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
[15]向宗魯.說苑校證[M].北京:中華書局,1987.
[16]郭慶藩.莊子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1961.
[17]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1962.
[18]王先慎.韓非子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98.
[19]崔豹.古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0]趙輝.楚辭文化背景研究[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21]王孝廉.水與水神[M].北京:學苑出版社,1994.
[22]李守奎,李秩.尸子譯注[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
[23]段成式.酉陽雜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4]袁珂.山海經校注[M].成都:巴蜀書社,1992.
[25]李立.文化整合與先秦自然神話演變[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26]許慎.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1963.
[27]陳彭年,等.宋本廣韻[M].北京:中華書局,1982.
[28]孫詒讓.周禮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87.
[29]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M].北京:中華書局,1983.
[30]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
[31]何寧.淮南子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1998.
[32]陳橋驛.水經注校證[M].北京:中華書局,2013.
[33]李誠.屈賦神話傳說三題[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6).
[34]何新.諸神的起源(第一部)[M].北京:中國民主法治出版社,2008.
[35]熊良智.《楚辭》后羿形象思考[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6).
[36]趙彥衛.云麓漫鈔[M].北京:中華書局,1996.
[37]干寶.搜神記[M].汪紹楹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
[38]陶弘景.真靈位業圖校理[M].王家葵校理.北京:中華書局,2013.
[39]徐道.歷代神仙通鑒[M].沈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5.
[40]張華注.神異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41]潛明滋.中國古代神話與傳說[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