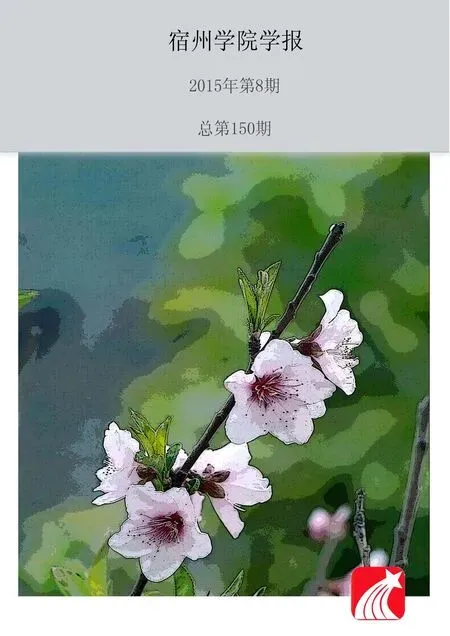詮釋理論視閾下的中國古籍英譯論析
——以英譯《莊子》為例
劉澤林,丁延海
亳州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外語系,安徽亳州,236800
詮釋理論視閾下的中國古籍英譯論析
——以英譯《莊子》為例
劉澤林,丁延海
亳州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外語系,安徽亳州,236800
從詮釋理論的視角分析了中國古籍的英譯現狀,指出譯者容易忽略對原文本哲學精神、文本結構、修辭手法的詮釋,遺失了原文的民族個性,缺失了中國傳統文化精髓。以《莊子》的英譯為例,結合具體的古籍英譯實例,對英譯過程中所涉及到的問題進行了簡要的分析,提出重視對哲學精神、文本結構、修辭手法的詮釋,不僅能揭示翻譯中理解的復雜性和整體性,也對譯本的整個面貌產生綜合的、決定性的影響,既能彰顯譯本個性,又能更加準確地傳播中國傳統文化。
古籍翻譯;詮釋理論;哲學精神;文本結構;修辭手法
中國古代典籍是中華民族燦爛的傳統文化中的璀璨明珠,是中國人民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社會實踐的智慧結晶,曾對中國乃至世界歷史文化的發展產生過深遠的影響。當代,要做好對外文化交流,讓漢語走上世界,增強在全球人文領域的影響力,要讓世界能夠看懂中國古籍,那么古籍翻譯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
中國歷史上有著悠久的詮釋經典的傳統,如,儒家思想的學術發展史就是儒家典籍的詮釋史。就翻譯的性質而言,語言學和哲學都認為翻譯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詮釋。從詮釋理論角度研究中國古代典籍的譯介和傳播,事關中國在國際上的軟實力和話語權,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1 關于詮釋理論
詮釋理論是對哲學、語言學、宗教學等諸種理論中有關解釋、理解等問題的方法論、技術范疇的統稱,亦稱“詮釋學”“釋義學”“闡釋學”[1]。它主張通過文本本身來了解文本,強調忠實客觀地把握文本和作者的原意,是在現象學與存在主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個美學流派。早在人類遠古文明時期就已存在詮釋的問題,以古希臘時代亞里士多德、中世紀奧古斯丁和卡西昂、16世紀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19世紀德國哲學家施萊爾馬赫和狄爾泰、20世紀德國哲學家M·海德格爾等為代表的學者對傳統詮釋理論進行孜孜不倦的探索,在促使詮釋理論由人文科學的方法論轉變為一種哲學并發展成為哲學詮釋學方面作出了積極的貢獻。直至20世紀50年代末,德國哲學家加達默爾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人文科學不可避免地具有歷史相對性、文化差距性與視界溶合性的詮釋理論基本觀點[2]。他把海德格爾的本體論與古典詮釋學結合起來,認為:當前的認識因受制于歷史因素而具有相對性;人的認識因局限于不同的傳統文化中,而不可避免地具有“偏見”;真實的詮釋就是各種不同的主體“視界”相互“溶合”的結果。這些觀點在西方學術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據此,隨著東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日益加強,古代典籍譯介研究的不斷深入,結合大量的具體古籍翻譯實踐,對中國古籍英譯展開進一步的探討,將會產生新的詮釋和啟迪。
2 詮釋理論視閾下的英譯《莊子》
本文以英譯《莊子》為例,對古代典籍英譯和傳播過程中,所涉及的哲學精神、文本結構以及修辭手法等方面加以研究和探討,努力為國內學者提供啟發和借鑒。
2.1 英譯《莊子》中的哲學精神詮釋
中國古代典籍富于哲學精神,且大多通過暗示表現出來。然而,包括古籍翻譯在內的翻譯活動,往往是一種解釋,譯文只能傳達一個意思,往往無法翻譯原文可能含有的通過暗示所表明的哲學精神,很容易導致“古籍譯文把原文固有的豐富哲學精神丟掉了許多”[3]的現象。因此,譯者在古籍翻譯過程中,強化詮釋哲學精神意識的同時,需要竭力并創造性地采用恰當的語言表達形式對哲學精神加以詮釋。
《莊子》的譯本有許多,除馮友蘭先生外,大多似乎并未觸及到原文作者的哲學精神。例如,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89年的《莊子:神秘家、道德家、社會改革家》(Chuang Tsu:Mystic,Moralist,and Social Reformer)、理雅各(James Legge)1891年的《莊子》(The Writings of Kuang Zou)對原作者哲學思想實質把握不住,很少涉及到對原作者哲學精神的詮釋,故其譯本傳譯不夠嚴謹,在英語世界的影響大打折扣。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的中國著名學者馮友蘭先生在英譯《莊子》的過程中,充分利用自己的優勢,重視向西方讀者詮釋《莊子》的哲學精神。他將道家思想放入以西方哲學為主要視野的哲學分類中,根據自己的理解對《莊子》哲學精神正確的解釋給出新的翻譯,如有必要還加上注釋和評論。例如:
源文: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4]172。
譯文:In doing what convention considers as good, eschew fame. In doing what convention considers as bad, escape disgrace or penalty.Always pursue the middle course.These are the ways to preserve our body,to maintain our life,to support our parents,to complete our terms of years.[4]40
“無為、養生”是《莊子》的核心哲學思想之一。馮友蘭先生在譯文中強調了這一觀點,將上面的英譯文回譯成現代漢語,將會體會到:在做所謂善事時,要(想法)回避出名;在做所謂惡事時,要(設法)避開遭受恥辱或懲罰。總是尋求適度,忘善惡而居中。這些就是保全生命、維持生活、贍養父母、安度一生的方法。譯文某種程度上詮釋了作者的“養生非求過分”的折中哲學精神[5]。
2.2 英譯《莊子》中的文本結構詮釋
在傳統的翻譯觀中,譯者通常按照源文本文句的順序,把文本內容翻譯出來,不考慮文本的編排結構和特點;有時候,若遇到比較大的句群,其句子間順序可能也有所改變;對于文集來說,譯者通常也只是按原書的編排順序用目標語表達出來。例如,花滋生(Burton Watson)1964年的《(莊子)全譯》(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 Tzu)、汪榕榕和任秀樺1997年出版的《莊子》(Zhuang Zi)就沒有太考慮原文本的編排結構特點。然中國古籍的文本結構具有特殊復雜性,不能理所當然地按順序譯出,也不能受到其原有形式的古老風貌所束縛。
中國道家經典著作《莊子》雖早在公元前四世紀就已產生,但直到公元三世紀才編訂完成。它從一開始的52篇到現代比較流行的33篇的整個編訂過程已很難講清楚,并對現如今的33篇《莊子》,其內篇(7篇)、外篇(15篇)、雜篇(11篇)三部分的區分、篇目的真偽、成書的時間以及作者等問題也從未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見。因此,《莊子》文本有不少脫節、殘損、甚至明顯的難解之處,部分與部分之間在寫作日期、思想和風格上的不一致,原文的斷裂處、模糊處,韻文與散文的區別等等問題,需得到譯者的重視,而不應被流暢的譯文所掩蓋[6]。
葛瑞漢在《論道者》“《莊子》其書”一節中認為《莊子》不是一部傳統意義上完整連貫的書,而是一部“為隱退到私人生活論證的哲學著述選集”[7],是由不同思想、不同流派的作者創作而成的諸多論文的匯編。在英譯此類古籍的過程中,譯者對文本的編排順序進行合理的改動,以突出不同的主題,使文本脈絡更加清晰,幫助讀者領會、掌握文本精髓,是一種明智之舉。葛瑞漢在英譯《莊子》的過程中,依據不同的作者群或不同的主題對文本的編排結構進行了非常大的變動:將《莊子》內、外、雜篇3個部分重新調整成6個部分。除長篇譯序外,其余5部分是:內七篇和“與內篇有關系的段落”(The Writings of Chuang-tzu:the Inner Chapters of Chuang-tzu and Passages Related to the Inner Chapters)、“莊子學派”選譯(A “School of Chuang-tzu” Selection)、原始主義者的論文(The Essays of the Primitivist and Episodes Related to Them)、楊朱學派的論文(The Yangist Miscellany)、調和論者的作品(The Syncretist Writings)。葛瑞漢不僅對文本的編排結構進行大幅度的調整,還在更小層次的段落、句群、句子方面進行較大的改動。實例說明,在英譯古籍的過程中,譯者不應把原文本全盤接受作為應該遵照的“模范”,而應對原文文句進行詮釋。在承擔傳統翻譯任務的同時,也需承擔大量非傳統的整理、修改、完善和甄別等詮釋任務。
2.3 英譯《莊子》中的修辭手法詮釋
由于漢語言的獨特特點和中國人特有的審美習慣,形成了我國古代典籍獨有的文學美感,但是影響文學美感的因素在英譯過程中往往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和詮釋[8]。
《莊子》的最鮮明特點之一是借代的使用,既突出事物的本質特征、增強語言的形象性,又使語言富有變化、引人聯想,使其表意細致、豐富。例如:
源文:子游曰:“地賴則眾竅是已,人賴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4]155
譯文:The music of earth,“Tzu Yu said,”consists of sounds produced on the various apertures; the music of man, of sounds produced on pipes and flutes. I venture to ask of what consists the music of heaven.”
“The winds as they blow,”said Tzu Chi,“differ in thousands of ways, yet all are self-produced……”[4]19
“籟”本義為“從洞孔發出的聲音。”可泛指“自然界的風聲、水聲、鳥聲等音響。”原文作者采用借代修辭手法來說明“世界萬物看起來是千差萬別,歸根結底卻又是齊一的”的觀點。馮友蘭先生采用借代修辭手法把“地賴、人賴、天籟”分別譯成“The music of earth”;“the music of man”;“the music of heaven”。堅持保留《莊子》原有的借代修辭手法,說明他認識到對典籍修辭手法詮釋的必要性。
《莊子》中也大量使用排比、對偶等修辭手法。所謂排比,就是把三個或以上結構和長度均類似、語氣一致、意義相關或相同的句子排列起來。使用排比修辭手法,不僅可使句子結構整齊、增強語言的連貫性和節奏感,而且還能突出事物的特征;對偶所用的字數相等,結構形式相同或相似,節奏感強。例如:
源文: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4]217。
譯文:Do not be the owner of fame. Do not be full of plans. Do not be busy with work. Do not be the master of knowledge.[4]99
譯文作者保留了原有的排比、對偶等修辭手法,把“無為”等譯成比較簡短的“Do not be”,然后把“名尸、謀府、真事任、知主”分別譯成“owner of fame,full of plans,busy with work,master of knowledge”。這樣,譯文表達整齊勻稱,有音樂美感,易于記憶,表現效果凸顯。
古代典籍字詞的豐富內涵和高度靈活的結合,妨礙了翻譯中比喻、疊字、頂針、排比、對偶、借代等修辭手法的使用,再加上這些修辭已經超出了單個句子的范圍,擴展到了句子以上的層面,要求譯者在英譯中對譯文在“形合”和“意合”間進行微妙的轉換,同時也表明古籍翻譯中加強對修辭手法的詮釋能夠使翻譯具有無窮的再生力量。
3 結 語
詮釋理論視閾下的中國古代典籍翻譯是動態的、開放的,不同時空、不同視角、不同譯者的中國古籍翻譯研究的歷史就是一部詮釋史。在中國古代典籍翻譯過程中,重視對其哲學精神、文本結構、修辭手法的詮釋,不僅揭示翻譯中理解的復雜性和整體性,也對譯本的整個面貌產生綜合的、決定性的影響;既能彰顯譯本鮮明的民族個性,又能更加準確有效地傳播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文化。
[1]謝天振.譯介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28
[2]蔣勁松.經驗、理論與整體主義:兼與柯志陽先生商榷[J].自然辯證法通訊,2003(5):102-106
[3]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13
[4]Zhuangzi Youlan Feng.A New Selected Translation with an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Kuo Hsiang[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12
[5]劉笑敢.莊子哲學及其演變[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95-96
[6]徐來.《莊子》英譯研究[D].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2005:45
[7]葛瑞漢.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論辯[M].張海晏,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202
[8]徐來.英譯《莊子》研究[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95-96
(責任編輯:李力)
10.3969/j.issn.1673-2006.2015.08.021
2015-03-06
安徽省教育廳人文社科研究項目“皖北‘亳文化’英語譯介與傳播研究”(SK2013B306)。
劉澤林(1970-),安徽鳳陽人,碩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英漢語言文化對比、翻譯理論與實踐。
H315.9
A
1673-2006(2015)08-007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