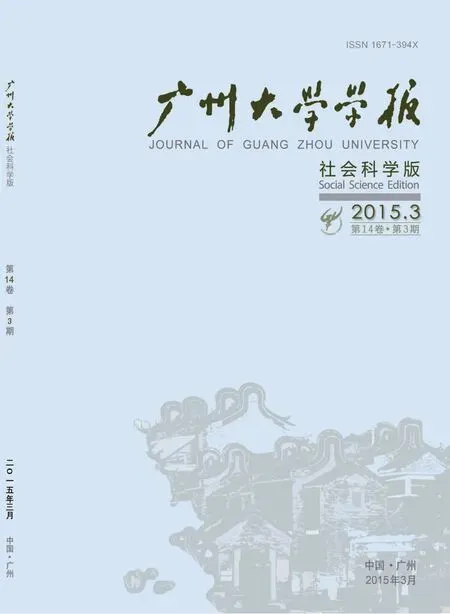貨幣政策立場度量的演進和發展
鄒文理
(廣州大學經濟與統計學院,廣東廣州 510006)
貨幣政策是中央銀行為實現其特定的經濟目標(如穩定物價、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和平衡國際收支)而運用各種工具調節貨幣供給和利率,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方針和措施的總和。貨幣當局制定政策的最終目的是通過一系列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以達到影響實體經濟中的各種宏觀經濟變量,如產出、就業和通貨膨脹等。因此,準確度量當前的貨幣政策立場(monetary policy stance)對于評價不同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定量分析貨幣政策對產出和通貨膨脹的影響效果非常重要。
實際上,要完美地回答這個問題卻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量化和規范研究貨幣政策的前提是尋找到貨幣政策立場的合意度量指標(indicate),但問題的關鍵又是只有找到某種準確刻畫或度量當前貨幣當局政策立場的指標才能進行一系列的理論與實證研究。關于如何度量貨幣政策立場就成為了金融經濟學研究中從理論上容易理解,但是從實證分析上卻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為了研究的需要,學者們做了大量探索,度量當前貨幣政策立場的指標經歷了從定量的單一金融變量到綜合金融變量,再到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敘述性度量指標的發展過程。本文將主要圍繞這個發展過程,對貨幣政策立場的度量問題進行一個詳細總結和簡要評述。
一、單變量度量指標法
對貨幣政策立場傳統的度量指標是單變量(single variable)指標,單變量度量指標是指采用某一個具體的金融變量作為政策立場的度量指標,這些單一指標包括有貨幣供應總量、某種利率、貼現率等。弗里德曼和斯瓦茨(1963)認為貨幣供應總量是代表貨幣政策沖擊的合適指標,因此在他們最為著名的《美國貨幣史:1867~1960》以貨幣存量為主線,研究了美國1867~1960年近一個世紀的貨幣發展歷程,及其對美國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的影響。Sims(1972)[1]、Christiano 和 Ljungqvist(1988)[2]也采用貨幣總量度量貨幣政策,考察貨幣政策與GNP和工業生產總值之間的關系。
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研究發現以貨幣供應總量作為貨幣政策立場的度量指標有著諸多不足:一是采用貨幣總量的變化表示貨幣政策立場改變難以區別這種政策變化是需求因素導致的,還是供給因素導致的;二是隨著金融創新的不斷出現,金融管制的不斷放松,貨幣總量的定義也在不斷變化,貨幣增長速度的變化僅僅能夠體現政策變動的方向,很難真正體現貨幣當局的政策意圖。而且,在接下來的實證研究中,人們發現當以貨幣總量代表貨幣政策時,很多在實證結果中將很難解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流動性之謎(liquidity puzzle)”。“流動性之謎”較早出現在 Melvin(1983)[3]、Christiano(1991)[4]、Leeper和 Gordon(1992)[5]的研究中,指的是在實證研究中,貨幣供應總量與名義利率之間不存在短期的負向關系,而是存在正向關系。
意識到貨幣總量作為貨幣政策立場度量指標存在這些缺陷之后,經濟學家開始尋求其他的金融變量來 代 替 貨 幣 總 量。Sims(1980)[6]、McCallum(1983)[7]、Litterman 和 Weiss(1985)[8]以及 Laurent(1988)[9]發現與貨幣總量相比,短期利率對于實體經濟的預測能力更強,因而利率更加適合度量貨幣政策。他們主張采用利率的變化表示貨幣政策立場的改變。但是隨后的實證研究又發現,采用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立場的度量指標將產生所謂的“價格之謎(price puzzle)”。“價格之謎”是指在一段時間的緊縮性貨幣政策之后,總體價格水平會上升。關于“價格之謎”的討論可以參考 Balke和 Emery(1994)[10]、Giordani(2004)[11]、Hanson(2004)[12]等的研究。此外,以利率變化作為貨幣政策立場的度量指標還會產生“匯率之謎(exchange rate puzzle)”。“匯率之謎”指當一國提高利率,實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時,本國貨幣將貶值而不是升值,這與利率平價理論相悖。關于“匯率之謎”的詳細討論參見Grilli和 Roubini(1995)[13]、Philippe 和 Eric(2006)[14]等的研究。
在單變量指標中,除了貨幣總量和利率意外,還有一些金融變量被認為是度量貨幣政策立場的良好指標。Bernanke和 Blinder(1992)[15]的研究有著最大的影響力,他們通過詳細的向量自回歸(vector autoregression,VAR)分析,比較聯邦基金利率、貨幣供應量M1、M2,以及3個月和10年期國庫券利率對宏觀經濟的預測能力,證明聯邦基金利率更加適合作為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度量指標。Balke和Emery(1994)[16]等支持了 Bernanke 和 Blinder(1992)的觀點。此后一段時間,美聯儲的聯邦基金目標利率變化就成為度量美國貨幣當局政策立場最主流的度量指 標。 但 是 Thornton(1988)[17]和 Strongin(1995)[18]等人卻有不同看法,Thornton(1988)、Christiano 和 Eichenbaum(1992)[19]、Strongin(1995)考察了多個金融變量與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發現非借入準備金(non-borrowed reserves)是度量貨幣政策立場的最優指標。由于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和自有儲備與美聯儲所處的時期有很大程度關系,比如在沃伯格任美聯儲主席期間,其調節經濟的主要工具是自有儲備,而在格林斯潘時期,美聯儲調節經濟的主要工具則為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因此,這些度量貨幣政策立場的單變量指標均體現了非常強烈的時代特征,與當時的貨幣政策操作程序有密切的聯系。Armour等(1996)[20]認為隔夜拆借利率的變化是度量加拿大貨幣政策立場的良好指標。Laurent(1988)[21]、Goodfriend(1991)[22]、Oliner 和 Rudebusch(1996)[23]的實證研究發現,利率展期(term spread)可以作為度量貨幣政策立場的指標,因為中央銀行的一般工具是改變短期利率,公眾會對利率的改變做出相應預期。比如,公眾預期短期利率在短暫改變之后會慢慢回到初始水平,那么長期利率的改變將比短期利率的改變要小一些。反過來,如果公眾預期到當前短期利率的改變僅僅是長期改變的開始,那么人們將預期長期利率會比短期利率的變化更大。因此,利率展期(長期利率與短期利率的差異)對于分析貨幣政策立場將非常重要。
二、多變量復合度量指標法
上述所有研究都假設某一單變量是度量貨幣政策立場的良好指標,但是,對于任何經濟體來說,由于實際研究中問題的復雜性以及研究時期的局限性,各個研究結果卻是各不相同,難以找到一個準確度量貨幣當局政策立場的最優指標。因此,度量貨幣政策立場的多變量指標由此產生。
貨幣政策立場的多變量復合度量指標是指不事先設定某單個變量為貨幣政策立場指標,而是假設能夠代表貨幣政策立場的變量有多個;通過將代表貨幣政策立場的各個變量賦予一定的權重,然后在此基礎上進行各種加權求和計算,得到一套指標序列,這套指標序列就代表了貨幣政策立場的變化。
最早采用多變量復合指標度量貨幣政策立場的是加拿大銀行(Bank of Canada),他們創造了一套貨幣條件指數(Monetary Condition Index,MCI)。MCI是通過計算利率和匯率變化的加權求和得到的。其計算公式為:

式中,MCIt表示t時期代表貨幣政策立場的貨幣政策條件指數,λ1和λ2分別表示匯率和利率的權重,下標0表示基期,且λ1+λ2=1。
MCI方法也遭到了諸多批評[24-25]:一是 MCI體現了利率和匯率的變化,但是有可能這些變量與貨幣政策是沒有太大關系的;二是MCI僅僅考慮了利率和匯率兩個變量,而沒有考慮與貨幣政策傳導非常密切的其他金融變量,包含的變量有可能是不全面的;三是存在模型缺乏動態性,權重設定的隨意性和不一致,解釋變量不是外生變量等問題。對于這些批評,Gauthier等(2004)[26]提出了一些修正的方法:第一種方法是從IS-PC框架中計算得到權數。MCI式中的權數將通過加總所有滯后變量系數得到,由于增加了MCI的滯后項,也就解決了模型缺乏動態性的問題;第二種方法是通過廣義脈沖響應函數得到權數;第三種方法是通過因子分析得到權數,解決權重設定的隨意性問題。在這三種解決方案中,第一種方法最為流行。
另外一種基于多變量度量貨幣政策立場的方法是 Bernanke 和 Mihov(1998)[27]創建的,簡稱 BM法。他們在Bernanke和Blinder(1992)的基礎上,假定不存在某單個變量能夠準確度量貨幣政策立場,而考慮美國經濟結構的變化以及聯儲在1965年以后不同時期的貨幣政策操作程序的演變,通過“半結構VAR(semi-structural VAR)”方法,對不同樣本時期的操作程序進行參數設定,然后通過對模型施加識別約束的條件得到了模型的參數估計,并最終確定了對應于不同時期和不同操作程序情況下的貨幣政策立場指標。Bernanke和Mihov(1998)的研究結果表明,對于1965~1996年這段時間,沒有一個單一的變量能夠準確度量貨幣政策立場,隨著貨幣當局領導人和貨幣政策操作程序的變化,貨幣政策立場度量指標也在不斷變化。1979年之前,聯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s rate)是度量貨幣政策立場的較好指標;1979~1982年間,非借入準備金是較好指標;1982年之后,基金利率和非借入準備金是較好指標。
BM的具體做法如下。
首先,假設“真實”的經濟結構可以表示為無約束線性動態模型的形式:

式中,A,B,C,D和G為系數矩陣,Y是非政策向量,P是政策向量。非政策向量中包含有實際產出、價格水平等變量,政策向量中包含貨幣增長率、利率、匯率和利率展期等變量。
為了識別式(2)和(3),需要對模型施加一定的約束條件,假設貨幣政策有一定滯后性,貨幣政策變化對同期非政策向量沒有影響,也就是C0=0。經過簡單的數學運算,式(2)和(3)可以被表示為:

將式(2)、(3)與(4)、(5)對比:

式(6)就是標準的結構VAR模型,假設貨幣政策的備選度量指標包括:貨幣增長率m,利率i,利率展期ts,匯率ex,我們可以寫出其矩陣形式:

V表示VAR模型(2)和(3)的殘差。因此,貨幣政策立場指標可以表示為:

相對于MCI,BM的優點更為明顯:首先,BM考慮了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所有重要的金融變量;其次,包含了貨幣政策的定量指標;再者,這種方法很容易推廣到各個國家、各個時期,應用相當廣泛。
Fung 和 Yuan(2001)[28]按照 Bernanke 和 Mihov(1998)的做法,假設貨幣政策立場是不可觀察的,但是能夠通過一些金融變量的變化行為來反映,因此通過分析四類金融變量(M1、利率展期、隔夜利率和匯率)來度量加拿大的貨幣政策立場。
Sajawal和 Abdul(2007)[29]采用了 MCI 和 BM兩種方法構建了巴基斯坦的貨幣政策立場度量指標,并在此基礎上通過比較分析了MCI和BM兩類指標的表現,結果發現,對巴基斯坦而言,以MCI作為貨幣政策立場的度量指標更為合適。
由此可見,相對于單變量指標而言,多變量復合指標考慮的變量更多,也可以更加全面地對貨幣政策立場進行度量,但是在確定各個變量的權重時依然存在譬如主觀性和時變性等問題。
三、敘述性度量方法
度量貨幣政策立場的第三種方法是敘述性方法(narrative approach)。敘述性方法這種稱謂是Romer和 Romer(1989)[30]提出的,這種方法的核心思想是在分析貨幣政策時不是從統計的角度進行分析,而是通過閱讀分析各種有關貨幣當局政策制定和未來政策趨勢的信息,進而判斷當前貨幣政策立場及其效果。也就是說,敘述性方法是通過參閱有關貨幣政策的歷史記錄(如貨幣政策決策過程),分析當前的貨幣政策變化是否由實體經濟引起,進而判斷當前的貨幣政策立場。由此可見,敘述性方法更多是一種定性分析的工具,結論是判斷當前貨幣政策是趨于擴張還是緊趨于縮性。
Friedman 和 Schwartz(1963)[31]是敘述性分析方法的先驅,他們在《美國貨幣史》中曾運用此方法分析了美國貨幣政策歷史事件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此后的25年里,敘述性方法一直被規范的經濟學研究所忽視。直到 1989年,Romer和 Romer(1989)的研究才使敘述性方法重新煥發光芒。Romer和Romer認為將某些單變量指標度量貨幣政策分析貨幣政策與產出之間的關系不能識別是貨幣政策的改變影響產出還是產出的改變引起了政策變化,即他們之間的因果關系難以確定。但是,敘述性方法則能較好地解決這個問題。Romer和Romer(1989)利用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FOMC)的各種文件(主要是會談紀要),查閱是否政策更加傾向于反通貨膨脹,如果在某一天,貨幣政策確實表現為反通貨膨脹,那么他們就記錄下貨幣政策變為緊縮的日期。通過將1920年之后所有貨幣政策改變為緊縮的時間點記錄下來,就形成了一個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時間序列,通常我們將這個序列稱之為“Romer序列(Romer Dates)”。
Romer和Romer方法有兩個顯著的優點:第一,它探索了標準統計分析沒有包含的內容,即貨幣政策的意圖;第二,也是更為重要的是,從計量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種分析對經濟結構不敏感,在不同的經濟背景和不同的貨幣政策操作程序中都具有相當的穩健性。當然,Romer和Romer方法也存一些不足:第一,沒有區別政策變化到底是內生的還是外生的,這就使得從理論的角度來看,這種方法就沒有吸引力;第二,Romer序列中包含的信息是較為有限的,既沒有考慮貨幣政策的持續緊縮,也沒有考慮貨幣政策的擴張;第三,在構建Romer序列時多少會有主觀判斷的成分,存在固有的主觀性問題。
為了彌補這些不足,在Romer和Romer(1989)的基礎上進行了修改,Boschen 和 Mills(1991)[32]也根據FOMC的文件記錄,同時考慮了貨幣政策的松緊變化,按照貨幣政策緊松程度,他們設計了一份月度的貨幣政策立場指標體系,將“嚴重緊縮”“中度緊縮”“中性”“中度擴張”“嚴重擴張”分別賦值為-2、-1、0、1、2。相比 Romer和 Romer(1989)的研究,由于其同時考慮了貨幣政策的緊縮和擴張,Boschen和Mills(1991)所構建的貨幣政策敘述性指標體系包含了更多信息。
作為一種定性度量方法,敘述法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貨幣政策立場的識別問題,促進了貨幣政策效應的研究。[33]但是敘述性方法還是受到了諸多批判,Leeper(1993)[34]和 Shapiro(1994)[35]認為敘述性方法所度量的貨幣政策立場具有極大的內生性,而不是一種外生的貨幣政策變化,因此不適合用于計量經濟分析。此外,貨幣政策的定性判斷完全是主觀設定的,特別是對于區分“嚴重緊縮”和“中度緊縮”則更為困難。因此,固有的主觀性缺陷也是敘述性方法時常受到攻擊的原因。
盡管度量貨幣政策立場的敘述性方法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但敘述性方法已經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Romer和Romer(1994)同樣利用來自FOMC的會談紀要和公開市場操作的管理周報(Weekly Report of the Manager of Open Market Operations)的文字記錄,采用實際聯邦基金利率的變化減去聯邦基金目標利率的變化,構建了一組度量貨幣政策立場的新指標,這組新的度量指標能夠很好地解決敘述性方法的內生性缺陷。Skimmer和 Zettelmeyer(1996)[36]采用3個月利率變化來代替 Romer和Romer(1989)所使用的虛擬變量表示貨幣政策立場。Bagliano等(1999)將敘述性方法擴展到開放經濟中,但是由于在開放經濟中識別貨幣政策變化不但要考慮利率變化還要考慮匯率變化,貨幣政策立場的識別將變得更為困難。
四、中國貨幣政策立場度量指標
1995年3月1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正式頒布,標志中國貨幣政策制定的執行有了法律依據,學術界對中國貨幣政策的研究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貨幣政策的實施過程,就是通過使用貨幣政策工具作用于操作目標,進而通過操作目標影響中介目標,以實現最終目標。若要實現貨幣政策最終目標,央行的政策工具必須通過操作目標和中介目標來實現。那么,作為連接貨幣政策工具和最終目標的中間指標,操作目標和中介目標應該能夠充分體現出貨幣當局的政策意圖,即通過貨幣政策操作目標和中介目標以便能衡量或度量當前的貨幣政策立場。因此,有關我國的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度量指標,大部分研究者是從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或操作目標這個角度尋找中國貨幣政策立場的度量指標。
對于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國內的研究主要分為三派:一派認為應以貨幣供應總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一派認為應以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還有一派是可以稱之為綜合派,其認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應該包含更多的內容,不能僅僅只考慮單一指標。其中貨幣供應總量派又可以分為三類:一類認為狹義貨幣供應量M1適合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如蔣瑛琨、劉艷武、趙振全(2005)[37],耿中原、惠曉鋒(2009)[38]等;一類認為廣義貨幣供應量M2適合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如陸昂(1998)[39]等;還有一類認為M1和M2都適合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應該同時關注M1和M2,如王大用(1996)[40]、董承章(1999)[41]等。
孫華妤(2007)[42]考慮到中國現階段實行的是釘住匯率制度,通過實證分析發現,利率比貨幣供應量更加適合作為貨幣政策工具。徐亞平(2009)[43]認為,雖然我國尚未實現利率的市場化,但利率政策在我國宏觀調控中十分重要,從某種意義上說,利率變動是我國貨幣政策變化的信號。張屹山、張代強(2007)[44]認為同業拆借利率、存貸款利率和兩者利差的具體走勢,能夠為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個參考尺度,以衡量貨幣政策的松緊。
夏斌、廖強(2001)[45]認為貨幣供應量已經不適宜作為當前我國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但是他們也沒有提出一個具體的中介目標應該是什么,而一個可行的選擇是放棄采用任何中介目標,直接盯住通貨膨脹率,同時將貨幣供應量、利率、經濟景氣指數等其他重要經濟變量作為監測指標,即采取通貨膨脹目標。秦宛順、靳云匯、卜永祥(2002)[46]通過分析中央銀行的福利損失情況,發現以短期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和以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是無差異的,貨幣當局可以從金融運行的實際情況出發,靈活選擇應用這兩種工具。陳利平(2006)[47]在一個引入時滯和貨幣政策傳導擾動的貨幣政策模型中,分析了貨幣存量中介目標制下的貨幣政策效率問題。發現我國當前中央銀行不必承諾要達到某個中介目標,而應將中介目標定為一個綜合目標,重點看M2和貸款量,同時參考貨幣市場利率。劉金全、劉兆波(2008)[48]認為以貨幣供給量為中介目標的同時考慮提高名義利率的作用。
對于貨幣政策的操作目標而言,戴根有(2003)[49]以及謝平(2004)[50]認為基礎貨幣是我國貨幣政策的操作目標;陳雨露、周晴(2004)[51]認為超額準備金是我國貨幣政策的操作目標;而王曉芳和王維華(2008)[52]則認為準備金總額是我國貨幣政策的操作目標。由此可見,國內學界對于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包括操作目標和中介目標)仍然沒有一致的看法。
由于對于貨幣政策立場指標的不統一,近年來部分學者開始系統地研究度量貨幣政策立場的指標問題。索彥峰和范從來(2007)[53]借鑒Bernanke和Blinder(1992)的方法,以我國1998年以來的貨幣政策操作實踐為研究背景,對貨幣政策立場指示器問題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發現,在對實際經濟活動的預測能力方面,M1的增長率預測能力最強,M2的增長率次之,利率指標則較弱,所以M1的增長率是我國貨幣政策立場的良好指示器。姚余棟和譚海鳴(2011)[54]通過理論和實證分析,發現并證明了央票發行利率能夠綜合代表數量型和價格型的貨幣政策,其可測性、可控性、相關性比較理想,優于新增貸款和M2等數量型指標,也優于SHIBOR、基準存款利率等價格型指標。王曦和鄒文理(2012)[55]使用基于VAR的格蘭杰因果檢驗與方差分解方法,比較銀行間7天拆借利率、基礎貨幣、金融機構信貸總額、貨幣供應量M1和M2對實際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社會消費總額以及物價水平的預測能力。同時利用脈沖響應分析,討論M1和M2的作用方向是否符合理論預期。最后匯總比較指標的預測能力以及實際經濟效果,以甄別確定我國貨幣政策的最優度量指標。發現貨幣供應量等數量指標比利率指標更適合作為中國貨幣政策的度量指標;在研究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消費、投資和產出)的作用時,M2是最優的貨幣政策度量指標;在研究貨幣政策對通貨膨脹的作用時,M1是最優的貨幣政策度量指標。
五、評述和展望
貨幣政策是宏觀經濟調控中的兩大政策之一,合理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對于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意義非凡。檢驗貨幣政策制定和執行效果是否合符貨幣當局初衷對于將來制定和調整貨幣政策至關重要,而要準確檢驗貨幣政策的效果首先需要對貨幣政策立場本身作出清晰界定和度量。因此,尋找一個能夠準確度量貨幣政策立場的指標是進行一系列貨幣政策分析的前提和基礎。這樣一項看似簡單,實則困難的研究一直困擾著經濟學者。
就目前對貨幣政策立場的度量研究來看,其基本的演進路徑是:從單變量度量指標過渡到多變量的復合度量指標,與上述定量指標共存的還有一種敘述性的定性度量指標。由這個演進路徑可以看出,貨幣政策立場的度量指標越來越復雜。單變量度量指標僅僅以某一個具體的金融變量代表貨幣政策立場,這樣必然只考慮了貨幣政策某一個方面,難以對貨幣政策立場進行全面度量。多變量復合度量指標考慮到了貨幣政策的多個方面,對貨幣政策立場的度量更為全面。但是與單變量一樣,選取哪些變量作為度量貨幣政策立場的備選變量也是多變量不可回避的問題。此外,多變量復合度量指標的計算更加復雜,在計算多變量復合度量指標時需要對多個變量賦予一定的權重,權重的計算也沒有一致的看法。相對于單變量指標和多變量復合指標這些定量指標而言,度量貨幣政策立場的敘述性指標是一種定性指標。單變量或多變量這些定量指標對經濟結構的依賴性非常高,發達國家適用的政策度量指標對于發展中國家可能就不合適。相反敘述性方法得到的政策立場度量指標對經濟結構則不敏感,在不同的經濟背景和不同的貨幣政策操作程序中都具有相當的穩健性,具有更為廣泛的適用性。因此,盡管敘述性度量指標僅僅是一種定性指標,但仍然有其特有的優勢和生命力。因此,今后貨幣政策立場度量指標的方向應該有3個。
第一,構建特定時期的單變量度量指標。單變量度量指標的適用性較窄,可能在某個具體時間段,采用某一具體變量度量當時貨幣政策立場是合適的。當研究時間段較長時,采用單變量指標度量貨幣政策立場則不太合適。
第二,構建更為合理的多變量復合度量指標。多變量復合度量指標把包含了理解貨幣政策立場的更全面的信息,因此,多變量復合度量指標是未來度量貨幣政策立場的發展方向。其中,構建多變量復合指標的備選指標和各變量權重的賦值將是需要特別注意和研究的地方。
第三,敘述性指標不受研究時間的限制,具有非常廣泛的適用性。在定量度量指標的基礎上,采用敘述性方法構建一組度量貨幣政策立場的定性指標,形成一套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敘述性度量指標,能擴展和提升貨幣政策研究廣度和深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要構建一組合理的、能夠用于計量經濟分析的貨幣政策敘述性指標就必須想辦法解決敘述性方法所存在的主觀性和內生性問題。
中國貨幣政策立場的度量研究才剛剛起步,大部分研究都還是討論貨幣政策操作過程中的某一個具體階段,比如哪些指標適合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哪些指標適合作為貨幣政策的操作目標等問題,很少有研究將貨幣政策操作看成一個整體進行研究,對其政策立場進行嚴謹的度量。索彥峰和范從來(2007)、姚余棟和譚海鳴(2011)、王曦和鄒文理(2012)都采用VAR分析方法對貨幣政策立場的度量進行了分析,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研究思路。但是就這些研究結論來看,仍然沒有一致的看法:索彥峰和范從來(2007)認為M1的增長率是我國貨幣政策立場的良好指示器;姚余棟和譚海鳴(2011)認為央票發行利率能夠代表貨幣政策;王曦和鄒文理(2012)則認為研究實體經濟時,M2是最優的貨幣政策立場度量指標,研究通貨膨脹時,M1是最優的貨幣政策立場度量指標。此外,關于中國貨幣政策研究還完全沒有敘述性度量指標。因此,構建一套度量中國貨幣政策立場的定量指標和敘述性的定性指標十分必要,這對于規范中國貨幣政策效應分析,推進中國貨幣政策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意義重大。
[1] SIMS CHRISTOPHER A.Money,Income,and Causality[J]. AmericanEconomicReview, 1972(Sep):540-542.
[2] CHRISTIANO LAWRENCE J ,LJUNGQVIST LARS.Money Does Granger-Cause Output in the Bivariate Money-Output Relation [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Sep):217-36.
[3] MELVIN M.The vanishing liquidity effect of money on interest:analysis and implications for policy[J].Economic Inquiry,1983,21(2):188-202.
[4] CHRISTIANO L J.Modeling the liquidity effect of a money shock[J].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1991(4):3-34.
[5] LEEPER E M,GORDON D B.In search of the liquidity effec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2,29(3):341-369.
[6] SIMS CHRISTOPHER A.Macroeconomics and Reality[J].Econometrica,1980,48(1):1-48.
[7] MCCALLUM,BENNETT T.A Reconsideration of Sims'Evidence Concerning Monetarism [J].Economics Letters,1983,13(2-3):167-71.
[8] LITTERMAN ROBERT B ,WEISS LAURENCE.Money,Real Interest Rates,and Output:A Reinterpretation of Postwar U.S.Data[J].Econometrica,1985(1):129-56.
[9] LAURENT,RABU D.An Interest Rate Based Indicator of M.P.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J].Economic Perspective,1988(1-2):3-14.
[10] BALKE NS,EMERY KM.Understanding the price puzzle[J].Economic Review,1994,Fourth Quarter.
[11] GIORDANIA PAOLO,SEP.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of the price puzzle [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4,51(6):1271-1296.
[12] HANSON S M.The“price puzzle”reconsidered [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4,51(7):1385-1413
[13] GRILLI VITTORIO,ROUBINI NOURIEL.Liquidity and Exchange Rates:Puzzling Evidence from the G-7 Countries[R].Working Papers from New York University,Leonard N.Stern School of Business,Department of Economics,1995.
[14] PHILIPPE BACCHETTA ,ERIC vAN WINCOOP.Can Information Heterogeneity Explain the Exchange Rate Determination Puzzle?[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96(3):552-576.
[15] BERNANKE S BEN ,BLINDER S ALAN.The Federal Funds Rate and the Channels of Monetary Transmission[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2,82(4):901-921.
[16] BALKE S NATHAN,EMERY M KENNETH.The Federal Funds Rate as an Indicator of Monetary Policy:Evidence from the 1980s[J].Economic Review,1994,First Quarter.
[17] THORNTON DANIEL.The borrowed-reserves operating procedure:Theory and evidence[J].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 Review,1988(1-2).
[18] STRONGIN STEVEN.The identification of monetary policy disturbances explaining the liquidity puzzl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5,35(3):463-497.
[19] CHRISANO LAWRENCE,EICHENBAUM MARTIN.I-dentification and the Liquidity Effect of a Monetary Policy Shock[M]//A CUKIERMAN,Z HERCOWITZ,L LEIDERMAN,eds.Political Ecomony,Growth and Business Cycles.Cambridge MA:MIT Press,1992.
[20] ARMOUR J,W ENGERT,B S C Fung.Overnight Rate Innovations as a Measure of M.P.Shocks in Vector Autoregressions[R].Bank of Canada.Working Paper No.96-4,1996.
[21] LAURENT ROBERT D.An Interest Rate-Based Indicator of Monetary Policy[J].Economic Perspectives(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1988(January/February):3-14.
[22] GOODFRIEND MARVIN.Interest rates and the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J].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1991,34:7-30.
[23] OLINER STEPHEN D,G D RUDEBUSCH.Is There Broad Credit Channel of MP?[J].FRBSF Economic Review.1996(2).
[24] ERICSSON N,E JANSEN,N KERBESHIAN ,R Nymoen,Interpreting a Monetary Condition Index in Economic Policy[R].I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Conference Paper:Vol 6.1998.
[25] BATINI N,E NELSON.The Lags from Monetary Policy Action to Inflation Friedman Revisited[R].Bank of England External MPC Unit.Discussion Paper:No 6,2002.
[26] GAUTHIER C,G CHRISTOPHER ,YING LIU.FINANCIAL CONDITIONS Indexes for Canada[R].Bank of Canada Working Paper,2004.
[27] BERNANKE B S,I Mihov.Measuring Monetary Policy[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8,113(3):869-902.
[28] FUNG BEN S C,MINGWEI YUAN.The Stance of Monetary Policy[EB/OL].[2014-04-15].http:∥www.bankofcanada.ca/en/pdf/99-2-prelim.pdf,2001.
[29] SAJAWAL KHAN,ABDUL QAYYUM.Measures of Monetary Policy Stance:The Case of Pakistan[R].PIDE Working Papers,2007.
[30] ROMER CHRISTINA D ,D H ROMER.Does Monetary Policy Matter?A New Test in the Spirit of Friedman and Schwartz[M]//OLINER BLANCHARD ,STANLY FISHER(eds.),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1989.
[31] FRIEDMAN MILTON,SCHWARTZ ANNA J.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
[32] BOSCHEN J F,L O MILLS.The Relation between Narrative and Money Market Indicators of Monetary Policy.[J].Economic Inquiry,1991,33:24-44.
[33] KASHYAP A,J STEIN ,D WILCOX.Monetary Policy and Credit Conditions:Evidence from the Composition of External Finance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3,83(1):78-98.
[34] LEEPER E.Has the Romers’Narrative Approach Identified Monetary Policy Hocks?[J].unpublished,Federal Reserve Bank of Atlanta,1993(February).
[35] SHAPIRO M.Federal Reserve Policy:Cause and Effect,in N Gregory Mankiw,Monetary Polic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or NBER,1994.
[36] SKIMMER T ,T ZETTELMAYER.Identification and Effect of M.P.Shocks:An Alternative Approach[R].Working Paper,MIT,1996.
[37] 蔣瑛琨,劉艷武,趙振全.貨幣渠道與信貸渠道傳導機制有效性的實證分析——兼論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J].金融研究,2005(5):70-79.
[38] 耿中元,惠曉峰.M1和M2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適用性研究[J].統計研究,2009(9):64-69.
[39] 陸昂.關于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問題的幾點看法[J].金融研究,1998(1):64-69.
[40] 王大用.中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問題[J].經濟研究,1998(1):13-20.
[41] 董承章.中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與調控區間的確定[J].統計研究,1999(8):20-24.
[42] 孫華妤.傳統釘住匯率制度下中國貨幣政策自主性和有效性:1998 ~2005[J].世界經濟,2007(1):29-38.
[43] 徐亞平.公眾學習、預期引導與貨幣政策的有效性[J].金融研究,2009(1):50-65.
[44] 張屹山,張代強.前瞻性貨幣政策反應函數在我國貨幣政策中的檢驗[J].經濟研究,2007(3):20-32.
[45] 夏斌,廖強.貨幣供應量已不宜作為當前中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J].經濟研究,2001(8):33-43.
[46] 秦宛順,靳云匯,卜永祥.從貨幣政策規則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選擇[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2(6):14-16.
[47] 陳利平.貨幣存量中介目標制下我國貨幣政策低效率的理論分析[J].金融研究,2006(1):40-50.
[48] 劉金全,劉兆波.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與宏觀經濟波動的關聯性[J].金融研究,2008(10):37-47.
[49] 戴根有.中國央行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實踐和經驗[J].金融研究,2003(1):55-65.
[50] 謝平.中國貨幣政策分析:1998-2002[J].金融研究,2004(8):1-20.
[51] 陳雨露,周晴.浮動匯率制度下貨幣政策操作模式及中國貨幣狀況指數[J].世界經濟,2004(7):24-28.
[52] 王曉芳,王維華.政策性沖擊、貨幣政策操作目標:基于準備金市場模型的實證研究[J].金融研究,2008(7):26-34.
[53] 索彥峰,范從來.貨幣政策立場指示器的實證研究——來自我國貨幣政策操作實踐的證據[J].南開經濟研究,2007(2):107-119.
[54] 姚余棟,譚海鳴.央票利率可以作為貨幣政策的綜合性指標[J].經濟研究,2011(增2):63-74.
[55] 王曦,鄒文理.我國貨幣政策的最優度量指標[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1):202-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