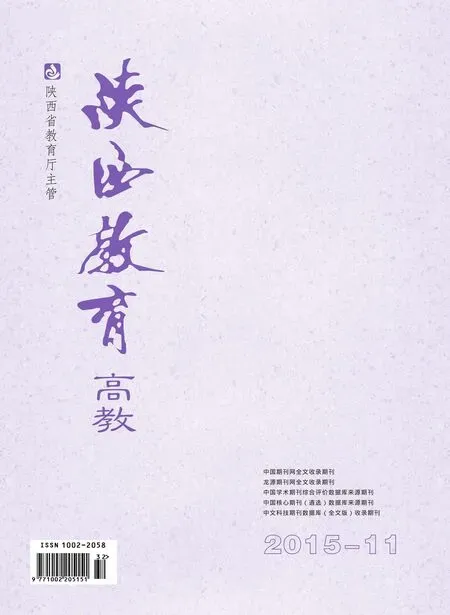胡琴聲部演奏員合奏能力的理解與思考
——聆聽、交流、融合
郭琴星
胡琴聲部演奏員合奏能力的理解與思考
——聆聽、交流、融合
郭琴星
中國民族管弦樂隊在學習、吸收、借鑒西方交響樂隊成功經驗的基礎上越來越“交響化”,其演奏的作品越來越豐富多變,其影響亦越來越廣泛,這就對民族管弦樂隊的演奏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合奏區別于獨奏,它更注重一個演奏員的合作能力和團隊意識。筆者嘗試以胡琴聲部為例,對演奏員的合奏能力作出一系列分析,并在培養與訓練方面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議。強調合奏能力是樂隊演奏員必備的素質,是一種傾聽、調節、溝通的能力,是一種團隊協作的意識。
民族管弦樂隊 胡琴聲部 合奏能力
20世紀中國音樂的發展有一個重大的成果,那就是在今天被人們廣泛認同的民族管弦樂隊以及為其創作的音樂作品。雖不能說它是仿制西洋交響樂隊而得來的,但至少它是接受了西洋交響樂隊影響后的一種選擇。
我國周代有以鐘鼓為主的鐘鼓之樂和以絲竹為主的竽瑟之樂,漢代有鼓吹音樂和吹、打并重的吹打音樂,近代還有以彈撥為主胡琴配奏的弦索樂隊等。卻唯獨沒有像今天民族管弦樂隊這樣的合奏組合。
這種新的民族樂隊萌芽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大同樂會”“國樂改進社”等都可以視作是初步的探索;繼而到了建國后的五六十年代,上海民族樂團、中國廣播民族樂團等專業團體的先后成立,標志著這種新型的合奏形式進入了形成和發展的階段;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民族樂隊合奏藝術進入了繁榮期,大量專業作曲家和指揮家的參與使民樂合奏藝術有了空前的發展,它在學習、吸收、借鑒了西方交響樂隊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更加具有“戲劇性”“史詩性”“交響性”。這就對其演奏樂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為一名合格的民族管弦樂隊演奏員,就需要具備一個關鍵的能力,這就是我們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演奏員的合奏能力。
合奏中的基礎音樂素質與能力
所謂基礎音樂素質,它包括音準、節奏、速度、力度等方面。之所以稱之為基礎,是因為這些方面決定了音樂作品完成的準確與完整。在合奏中對于基礎音樂素質的要求是有別于獨奏的。
獨奏時,演奏者可以很清楚地聽到自己演奏的音高,從而作出判斷和調整。但合奏時,尤其作為胡琴聲部,遇到樂隊強奏的情況,對于自己演奏的音高有時是聽不清楚的。此時,樂器的特點又造成了很多的不利因素。如,沒有品位,不能像彈撥樂器那樣直觀地看到自己演奏的音高位置,這就需要演奏者要具備良好的把位意識。
對于樂隊的節奏訓練與獨奏時也有著很多不同。樂隊分譜上有很多獨奏譜里見不到的伴奏音型,對于這些節奏型的掌握和熟練就成了樂隊節奏感的基礎。樂隊的節奏比之獨奏要求更為嚴格。它需要以最小的節奏單位作為標準進行訓練,通常稱作“數小拍”或“打分拍”。以節奏的最小單位進行訓練,是一名樂隊演奏員應有的素質與能力。
同樣,對于力度的要求,合奏與獨奏也有區別。音樂中到底有沒有絕對的力度概念呢?一個pp是多少分貝,而f又是多少分貝?這樣的問題應該怎樣解決?我認為,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閻惠昌先生作出過一個精辟的論述。
“一個pp的力度應當怎樣去演奏,一般情況下,你應該先聽到別人的聲音,然后再將自己的聲音融入其中,這樣,集體的效果就是一個標準的pp力度。”這樣的解釋即直觀易懂又容易操作,確定了pp的力度,那么依次遞增就能夠構建出各個力度層次的音響效果。
聆聽與配合能力
一支樂隊是一個集體,演奏員只是這個集體中的一個個體,個體要在整個集體中發揮作用、體現價值,就必須學會與其他個體進行交流、協作。
音高是絕對的,但音準有時卻是相對的。在民族管弦樂隊中,各樂器種類之間的律制也不相同。有的是五度相生律,有的是十二平均律,有的則是純律。一段相同的旋律分別在弦樂聲部、彈撥樂聲部和吹管樂聲部演奏時,其音高就會有少許的差別。西洋交響樂團也存在類似的問題,那就需要演奏者根據不同的情況進行調整。如果是重復上一個聲部旋律,那就需要盡量的模仿而作出微調;如果是在和聲織體中,那就需要演奏者用耳朵去聆聽其他聲部和整個和弦的感覺,再將自己的音高放在全局中去找到合適的平衡點。作為一名樂隊演奏員,不但要掌握絕對音高概念,更要有相對音高感覺。
音準如此,力度亦是如此。例如趙季平先生的“為小提琴、古琴、女高音與樂隊而作的《幽蘭操》”中,弦樂聲部其中的一段旋律和女高音的旋律是一樣的,在沒有擴音的情況下,一個女高音要和幾十位演奏員的音量取得平衡,這就需要演奏員有意識地控制自己的力度。雖然旋律是非常富有歌唱性的大樂句,但與女高音相比弦樂聲部始終是陪襯地位,即使譜面標記的力度為f,在實際演奏中也需要降低力度層次。這一切都是在聆聽與配合的基礎上作出的調整。
一個連續十六分音符的音型,作曲家往往不會將其安排在一個聲部內完成,尤其是現代作品。通常情況下,這樣的音型是由“接龍”方式來完成的。在這樣的織體下,為了確保聲部進入的準確性,除了嚴格按照拍子以外,還要學會聆聽前面的聲部,演奏員邊聽著前面聲部、邊看著指揮的圖示、邊演奏,從而達到“接龍”的準確和連貫。
如果把每個聲部看作是戲劇中的表演者,那么它們應該分別飾演著不同的角色。在眾多的聲部中搞清楚自己的位置也是聆聽與配合能力的一種體現。
如《古槐尋根》(趙季平)的快板部分,二胡聲部奏出喜慶、歡快的“晉中秧歌風”,此時“唱”的是“主角”,就需要充分展現出弦樂的歌唱性和長線條。接下來同樣的旋律由嗩吶領軍的管樂聲部奏出,氣氛更加熱烈,二胡聲部此時卻變成了伴奏音型,是“配角”,就必須收斂個性,降低音量,把“戲臺”讓給“主角”聲部。
這種配合能力在演奏協奏曲中顯得更為突出。間奏時,樂隊是主角,要盡可能地奏出音樂的表情和張力。一旦獨奏進入,樂隊就要立刻輕下來,由主動的演奏變為被動的跟隨和配合。
有了聆聽與配合,還要有交流。獨奏和伴奏交流、聲部與聲部交流、樂隊與指揮交流、演奏者與觀眾交流,這些在樂隊合奏中都是必不可少的。
音樂修養與藝術境界
要做一名出色的樂隊演奏員,增加自己的音樂修養,提高藝術審美和境界是十分必要的。讀先人的書是用自己的生命和經歷去激活它。演奏音樂作品也需要調動自己的生活閱歷和知識儲備去發掘作曲家所要表現的內涵和意境。要想準確、生動地將其演繹出來,就需要演奏者具有豐富的想象力和畫面感。
《秦·兵馬俑》(彭修文)的第一段“軍整肅”的開始就描寫了這樣一幅畫面:拂曉時,從遠處傳來軍隊的行進聲和號角聲,漸漸地,一個聲勢浩大的行軍隊伍躍然于眼前。樂師如果帶著這樣的畫面感去演奏,勢必會更加生動和貼切地表達出樂曲的意境。
每一件樂器都有自己本然的音色,就像天是藍色的,云是白色的。基本音色確定了一件樂器的性格。就民族樂隊中的胡琴樂器來說,聲音甜美近似人聲、表現力豐富富有歌唱性這些都是它們共同的特點。不同的是高胡更為明亮清秀,二胡則委婉抒情、剛柔多變,中胡的音色深厚豐潤,三個聲部的音色既有相同點又存在區別。
而世間萬物都在不斷變化,有時天可以是灰色的,云可以是紅色的。那樂器的音色也是可以變化的。在演奏和聲織體或者是鋪墊性、襯托性的樂句時,有時就需要作出音色的調整,使整體感覺更加融合或是更加虛幻、飄逸。
《和平頌》(趙季平)第二樂章《江淚》,一開始,所有的弦樂聲部演奏出二度疊置的不協和音程,好像一陣陣陰風吹過,不協和和弦的使用似陰霧籠罩在大江的上空。此時,演奏員就要放棄自己樂器的本然音色,甚至可以將聲音演奏的空洞、嘶啞。接著,小軍鼓由弱至強急促地進來,日寇法西斯的鐵蹄踏到了這塊美麗富饒的土地上,昔日的京畿繁華瞬間變成了人間的地獄,秦淮河的煙波槳影泛起了殘酷后的血腥。以三弦領軍的彈撥樂奏出連續的八分音符,弦樂聲部隨之模仿進入,就仿佛是日寇的鐵蹄一樣。此時,難道你還能用甜美而富有歌唱性的音色來演奏?我想這絕對是不合適的。弦樂聲部用弓根在琴弦上大力撞擊而發出鏗鏘、尖銳的音響效果才是音樂所需要的。
美不等于唯美,江南水鄉的清新秀麗,西北戈壁的荒涼空曠都是美的不同方面。有時嘶啞、尖銳的音色也是一種美,因為它恰如其分地表現了音樂的意境。
柳宗元在《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中寫道:“海畔尖山似劍芒,秋來處處割愁腸。”其中“尖山”“劍芒”“割愁腸”等字眼可說與美毫無關系,但恰恰是這些讓人“心驚肉跳”的字眼真實地反映出作者思鄉的情懷,將那種急迫的期盼和渴望演繹得淋漓盡致,讓人讀后感同身受。美,于是產生了。
在這里,我想借用著名哲學大師李澤厚先生在《美學四講》中所提出的三個境界來作一個歸納。掌握了基礎的音樂素質,可以將作品演奏得準確而完整。通俗來講,就是好聽。這只是達到了第一個境界——悅耳悅目;能夠在樂隊中學會聆聽與配合,將音樂演奏得精彩,這就達到了第二個境界——悅心悅意;只有不斷提高自己的音樂修養和藝術境界,將音樂作品演繹得深情動人,使聽眾皆深有感觸,真真正正做到了讓聽眾被你的音樂所打動,這才是最高的境界——悅神悅志。
談了這么多,相信大家對于合奏能力已經有了一定的認識。其實,你也可以稱它為樂隊能力、樂隊感覺或合奏意識,這種意識是區別于獨奏來談的一種合作意識,是個性融入共性的群體意識,是個人服從集體的服從意識。合奏意識也是一種能力的體現,是作為一名樂隊演奏員所必備的素質。所以,我們在這里稱之為合奏能力,它即是傾聽能力,也是調節能力,還是溝通能力。
作為一名民族管弦樂隊的聲部演奏員,他的角色時而是主角,時而是配角,時而是登高一呼,時而是一唱一和,時而戲份濃重,時而又只是看客。為了適應這樣的需要,就需要具備這樣一種合奏能力。
[1]陳明志:《中樂因您更動聽——民族管弦樂導賞》。
[2]梁茂春:《論民族樂隊交響化——為香港中樂團主辦的研討會而作》。
作者單位:西安音樂學院民樂系陜西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