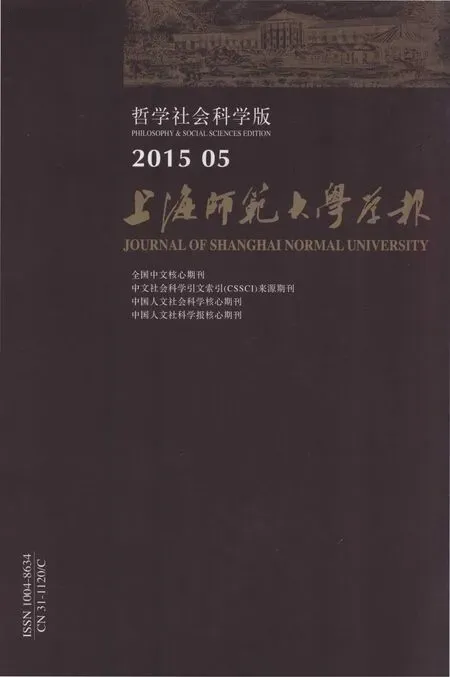《列子》自然本體論的音樂欣賞審美
卞魯曉,張允熠
(1.淮北師范大學 政法學院,安徽 淮北 235000;2.上海師范大學 哲學學院,上海 200234)
《列子》文本中關于音樂的文字主要著眼于音樂作為一門具體藝術的審美經驗及其內部規律,對于音樂的論述大多從藝術本身的特質出發,少有涉及音樂與政治、教育關系的問題。基于此,它的音樂實踐活動更多地強調音樂本身所帶來的審美愉悅,這樣我們就不能不談及音樂實踐活動中最后一個環節——音樂欣賞。《列子》以為在音樂欣賞中人們可獲得音樂美感,這種美感不僅僅是感官的簡單體驗,更重要的是精神愉快和知性滿足。這種感受既體現在“余音繞梁木麗,三日不絕”①的審美心理效應上,也體現在“子之聽矣!志想象猶吾心也”②的明確音響感知、深度情感交流和想象聯想之中,以及對“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③的音樂自然之道的理解。
一、“余音繞梁木麗,三日不絕”:審美心理效應的再現
音樂作品及作品的表演使欣賞者感受和理解作者想要表達的情感內容和思想意境,這是一個由表層欣賞到內在體驗的過程,《列子》用“余音”來說明聲音的表層結構消逝以后,欣賞者所感知到的音樂里層,用“三日不絕”的藝術夸張描述欣賞者被音樂精神等內在的情感深深打動的情形,由此而進入到忘記自我和身處無我之地的境界,在情感上無論悲傷還是喜悅總能與創作者產生共鳴,在痛苦或者歡樂中精神得到升華,從而產生審美效應。
《列子》記述了一則關于音樂的故事:“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繞梁木麗,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這段文字涉及了音樂欣賞心理效應的幾個層次,首先韓娥用原生態的演唱、無多余加工的聲音,借聲音的高低、長短、輕重、緩急等,從感官上深刻地打動聽眾,產生“既去而余音繞梁木麗”的效果,使人們在無關聯的現實生活中仿佛還能找回音樂的蹤跡,“三日不絕”時時回味聲音的抑揚頓挫、豐滿圓潤,這是音樂所形成的聽覺記憶,也是音樂感性知覺的最明確表述。這種感知本身也伴隨著音樂欣賞的第二層心理,即情感體驗。
音樂是長于激發感情的藝術,是常態情感與音樂情感交相傳導的中介。“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韓娥因受辱而產生激烈的悲傷情緒,這一情緒是主體自身主觀經驗到的一般情感,是對客觀所歷與自身相聯系引起的一種態度,是對現實的最貼近的判斷、評估和反應,單純而直接同時伴隨著介于情感與理性之間的知性因素,即內在訴求的流露。然而這還不能稱之為音樂情感,因為音樂本身所內含的情感并不只限于人的喜怒哀樂,它常常是某種精神和品格的結合。當韓娥長聲哀哭以歌唱抒發情感,把痛苦、希求體現在旋律之中,把具體的不幸與心酸等一系列心靈體驗置放于歌聲中,這時她的心靈處于一種內容豐富而復雜的空間,并同時賦予所唱以具體的、可感知的音樂情景以及自我精神,使音響所形成的意象與情思、心愿密切聯系,成為欣賞者可以感受和領悟的音樂。欣賞者的領悟并不是來源于單純的聲音的運動,而是源于內含了歌者特殊的、經過曲折轉化的、以音樂為形式精巧安排的情感體驗,正是這種音樂情感喚起了聽眾的想象和同情,相應地產生了激動的情感效應:“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如果說老者被觸動了心弦,幼者則感于歌聲所攜之激情產生的知性之真,迅速轉化為未成年人的情感體驗,形成音樂欣賞中的主體間性,造成一種為之悲愁、垂淚相對、食不下咽的心理效果。由此可見欣賞者可以在充滿激情的音樂中無限地把自身投射于音樂中去,這時的音樂欣賞心理正處于一種是“我”而“非我”的狀態之下,形成一種歌者與聽眾的情感交相流淌的互動模式,即使音樂感性形式隨生隨滅之后,仍然滲透到聽眾的心靈并占領當下的意識,持久地感受著音樂傳遞的情感,使他們或“垂涕相對,三日不食”或“喜躍抃舞,弗能自禁”。
唐人盧重玄《列子解》對上述文字解曰:“夫六根所用皆能獲通。通則妙應無方,非獨心識而已。”“六根”即眼、耳、鼻、口、舌、身六種感覺器官,“皆通”表明感知在“意”的作用下形成審美通感,“心識”則指知性,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列子》對音樂欣賞心理的描述。美學家朱光潛認為:“近代美學所側重的問題是:‘在美感經驗中我們的心理活動是什么樣?’至于,一般人所喜歡問的‘什么樣的事物才能算是美?’這一個問題還在其次。”[1](P3)其實在中國古代的文本夾縫中,不僅有著對審美體驗的具體描述,也在這些文字中暗含著對于審美心理的記錄,這一記錄既包括音樂創作主體的心理活動凝結在音樂作品中通過樂音流動展現出來的過程,也包括作為欣賞主體的心理活動,比如音響感知、情感體驗、想象、聯想和理解認知,等等,這些心理活動在欣賞不同的音樂時所起的作用不同,所占的比重也不同,倘若要達到對音樂及作者的深度理解即理性欣賞,那么對欣賞者自身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因此才有《列子》所謂“知音”的故事。
二、高山流水覓知音:樂山樂水知人的情懷
中國古代的文人常常用音樂寄情巍巍高山和潺潺流水,把自我的全部身心寄托于外界事物,以為心物可以相感,用樂聲的音響形式模擬自然的風貌,并把自我的人格特征看成與山水相類,視山水為可以達成精神交往的另一主體,《論語·雍也》有所謂“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與仁兼而有之的人格理想經由音樂創造的山水意象傳遞出來,被真正的音樂欣賞者深切感受到,與演奏者內在情懷和精神品格形成共鳴,從而進入更高尚、澄澈、震憾的境界。《列子》所記伯牙一曲高山流水覓得知音的故事,體現了基于音樂自身的感情體驗和哲理思考的音樂鑒賞乃至于對人自身的欣賞過程,集中地概括了中國傳統文化對于音樂美感的深度理解。
伯牙是戰國時楚國人,曾在晉國為官,是一位撫琴大師,關于他的記載曾見于《荀子·勸學》“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牙有移情入樂、以琴表達心志的創作本領,據傳作品有《高山流水》、《水仙操》、《懷陵操》等。鐘子期也是一位楚國人,成長于音樂世家,曾是一位樂尹,后退隱山林之間。漢代高誘《呂氏春秋》注:“鐘姓也,子通稱,期名也。楚人鐘儀之族。”可見,鐘子期是一位有著很深的家學淵源和音樂修養的隱者。關于他們之間的知音故事曾出現在幾十種古籍中,繁約不同、闡釋各異,較早期的記載見于《列子·湯問》和《呂氏春秋·孝行覽·本味》。就深層意味而言,《呂氏春秋》云:“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2](P140)其寫“知音”意在強調知音難求,表述了普通人的心聲,啟迪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識人用人的道理。而《列子》則以此為結語:“伯牙乃舍琴而嘆曰:‘善哉,善哉!子之聽矣志想象猶吾心也。吾于何逃聲哉?’”其知音的故事重在音樂欣賞的深度分析,不執著于知音難求而是強調音樂審美在窮其趣,強調通過意境支配下的音響感知、想象和音樂所承載的情感、志趣以及哲理思考的結合,實現對音樂境界的充分理解并與創作主體的心靈溝通,其著重點在于音樂是人與人在境界層次溝通的中介,而非《呂氏春秋》的所謂王政之道。
就音樂的感知而言,輕松愉快的歌曲內容直淺,使人心神愉悅,聽眾無需從深層去感受樂曲的形象、意境,直覺即可欣賞這樣的音樂,從某種程度上講這只能算是音樂欣賞的最初階段。而深邃的器樂曲如果達到真正的欣賞目的則需要通過音樂意象的觸動,深入理解樂曲表現的內容,與音樂內涵的創作情感產生深深的共鳴,才能領悟到音樂所蘊藏的哲學構思以及所要表達的意向追求。“音樂不僅是一種用聲音抒發感情的藝術,而且還能夠通過感情的深刻抒發和音樂形象的邏輯發展來表達深刻的哲理思想。”[3](P79)音樂音響形式只是音樂結構的表層,透過這個表層以音響為載體的創作主體豐富的思想情感內涵,能否被欣賞者準確把握或理解,還在于欣賞者自身的音樂感知力,正如馬克思所說“對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說來,最美的音樂也毫無意義,音樂對它說來不是對象,因為我的對象只能是我的本質力量之一的確證,從而,它只能象我的本質力量作為一種主體能力而自為地存在著那樣對我說來存在著,因為對我說來任何一個對象的意義(它只是對那個與它相適應的感覺說來才有意義)都以我的感覺所能感知的程度為限”。[4](P79)這里的感知正是音樂審美的感知,是最早見于《禮記·樂記》的“知音”一詞最本源的意義,“審音以知樂”、“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也是《列子·湯問》所謂“子之聽矣,志想象猶吾心也”所表達的由音樂的深度感知進而發生聯想,從創作者那里獲取精神力量的審美過程。
就音樂的美感而言,不只是在樂音中獲得感官愉快,更主要的在于精神的愉悅和情感的滿足,這是音樂演奏與欣賞兩者的互動過程,雙方在這個互動過程中實現精神的交流,其前提必如《列子》所言“伯牙善鼓琴,鐘子期善聽”,相同的人生經歷、類似的生活體驗、共同的志趣愛好使鐘子期對樂曲的音響感知、感情體驗、想象聯想與伯牙達成了高度的一致:“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鐘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鐘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鐘子期必得之。伯牙游于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于巖下;心悲,用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鐘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嘆曰:‘善哉,善哉!子之聽矣志想象猶吾心也。吾于何逃聲哉?’”④伯牙以高妙的演奏技法對高山河流進行了惟妙惟肖的音響再現,這些音樂意象的塑造融注了個人的情感、意志和理想,他期待人們通過音樂與其達成共識,否則亦不能在演奏獲得美感,正所謂“若無子期耳,總負伯牙心”。⑤張湛《列子注》評價這段故事:“發音鐘子期已得其心,則無處藏其聲也。”認為鐘子期作為一位理想的音樂聽眾,在置身于音樂之中的同時更置身于音樂之外,看見伯牙的創作意圖,對他的生活與藝術表現出欣賞的態度,也正是在這層意義上兩者成為知已,傳為千古佳話。
《列子》用故事表述對于音樂欣賞的認識,盧重玄《列子解》對此做了總結:“夫聲之所成,因而感之,心之所起聲則隨之。所以五根皆通,心為識心所傳。善于聽者,聲咳猶知之;況復聲成于文,安可不辯耶?”音樂本身并不是對事物確切的描繪和反映,而是對事物相關的情感世界的深度探掘和聲音抽象,在仿若巍巍之山、瀲滟之水的音響律動中,與欣賞者所見、所歷形成理解的基點,在聲音的所激起的遐想中傳遞富有意味的情緒和確定的思想意境。音樂作為媒介,一百個人聽它可能就有一百種不同的主觀聯想,既然音樂創作本人帶有情感內容去創作音樂的,那么欣賞者就必須帶著探索音樂語言的能力才能把握正確的音樂運動形態。馬克思說:“如果你想得以藝術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須是一個有藝術修養的人。”[4](P108,P109)否則不能從中體悟到創作的內在情感運動軌跡。伯牙志在高山之巍峨、流水之寬廣的藝術境界和人生理想在音樂意象里展現,以音樂概念的形式嘗試說明自己,善聽的鐘子期以聽覺細心品味,以豐富的生活體驗和共同的生活態度為基礎,對伯牙創作的生動、凝純的音樂主題形象做了大膽的聯想,實現了相互間非語言的心智交流,也使音樂欣賞在理性認識的指引下達到了更深刻的階段。
音樂的理性欣賞前提在于音樂情感體現著音樂主體的精神和性格,“志在登高山”強烈地表現出伯牙積極向上的精神追求,不僅在于對現實客觀事物高山的形象表現。鐘子期在伯牙所演奏的樂曲中體驗到并欣然接受的是伯牙對現實生活、人生際遇、意志理想的藝術表現,而且在自己的意識中再創造出來,他們兩人的感情在音樂欣賞中獲得交流、雙方的內心世界得到溝通,審美評價因恰如其分而使彼此增加了審美的愉快。中國傳統樂山樂水的情懷也在音樂的流動中朝向自然的方向發展,形成一種以自然之道為精神追求的音樂終極理想。
三、“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把握音樂的自然之道
《列子》文本多處論及音樂藝術,是因為從某種角度上說,音樂是最純粹的藝術,是能夠通過聲樂和器樂充分體現形而上之思的工具,它因無法借用具體事物的表象形式來表現理念,就在音樂本身的形式中內在地反映人的自由存在方式,同時傳達給音樂欣賞者。《列子》是對人的自由生存方式進行深度思考的文本,它對音樂意象的描繪、音樂悲美精神的探索、音樂欣賞的深度理解無不彰顯對于生存本身的哲學追問,那些流于表面化、片面性的音樂以及與此相應的最低層次的音樂感受,被《列子》看作生理上的快感,即使欣賞者痛哭流涕也不過是情緒上的共鳴,虛構意象的簡單化的呈現,而最深遠的志向和情操則在于形而上學的無限性,即音樂的自然之道。《列子》對這一音樂本體的表達是借孔子與弟子之間關于音樂的對話而以逐層推進的形式展開的,它運用了逐步破舊說從而立新說的方式,帶入對音樂以自然之道為本體的新表述“無樂之樂”,把老子所謂“大音”和莊子“天籟”加以整合,開啟對音樂的形而上學的認知。
琴在中國古代是文人雅士修身養性的工具,音樂是文人們表情達意的中介,《列子》以儒家士人為故事的主人公究問音樂的本質,設定了三個不同的音樂層次,并對三個層次的內涵逐次進行了分析,最終推演出音樂的最高境界在于“無樂無知”。首先,音樂出于情性之本。故事中顏回援琴而歌、自得其樂,其言“樂天知命故不憂”,他的老師孔子對此評價說:“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于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認為顏回沉浸在個人的無憂無慮的心境里,無視生存中的諸多可憂可懼,抒發自我的無關于治亂的小我情懷,在這個層面上琴歌是暢情的工具,是抑制心中變動混亂的自我修養法則,是最低層次的學養工夫。
其次,禮樂出于治國之大義。《列子·仲尼》借孔子之口對他自己關于儒家所謂禮樂政教的認識給予了否定:“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遣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于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張湛在此文下注曰:“唯棄禮樂之失,不棄禮樂之用,禮樂故不可棄,故曰,未知所以革之之方。而引此以為憂者,將為下義張本,故先有此言耳。”當音樂被負荷治理天下、遺留后世的社會責任,用于修身乃為治國以平天下,心意執著于禮樂之所功用,音樂便失去了仁義情性之本,最終只能是無助于治亂,反而使仁義更加衰落、人情愈加澆薄,走向音樂之怡情的反面。音樂不再是自娛娛人的工具,不再是抒發人情哀樂的鐘鼓之聲,也不再是政教適性的統治手段,而是失其本而無所用之樂。
最后,音樂自然為本體的人生境界。《列子》音樂表現人生境界的態度終于呼之即出:“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此言下張湛注:“莊子曰:‘樂窮通物非圣人。’故古人不以無樂為樂,亦不以無知為知。任其所樂,則理自無樂;任其所知,則理自無知。都無所樂,都無所知,則能樂天之樂,知天下之知,而我無心者也。居宗體備,故能無為而無不為也。若欲捐詩書、易治術者,豈救弊之道?即而不去,為而不恃,物自全矣。”在《列子》看來,音樂藝術既不是對現實的逃避,也不是對現實的描摹,它應該是士人對于自然宇宙總體的感悟理解,無論是個體的生命安放,還是群體的和諧存在,都已然包括其中,正像中國傳統哲學所認為的,一切變易之數皆來自于不變之一,一切出于天命之性情自然之道的才是音樂之本,這個本是與道合而為一的終極,當這個終極之本統御音樂,作樂用樂順應自然,則不治而治,《詩》、《書》、禮樂拋棄抑或者改革又有什么關系呢?但是,如果憂與不憂的執念使音樂蒙上無法大全的陰影,那么音樂則無法超越時空之外,只能局限于物境空間的有限時空關系中,不能展現生命最本真的律動節奏,以及主體精神境界的高妙與神采,因此才有所謂“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至此《列子》音樂本體落實在自然無為的人生境界上,“真樂”成為聲、情、道三者統而為一的本真之樂,使萬物得以自然而然地顯現,既沒有語言、空間形式,也沒有某種物質載體自身特殊性的束縛,因此在表現非個別物、普遍存在性方面更具有直接性,這與中國人以感應的方式進行的審美發生方式相互印證,也與中國特有的形而上學相互契合。這也正是《列子》關于音樂欣賞論述的真正終點,即對音樂自然本體的思考。
總之,在《列子》一系列與音樂相關的故事敘述中,有這樣的一條由現實感受而至于藝術境界的思維路徑。音樂欣賞的內容不局限于純粹的自然事物的意象,更在于音樂意象背后音樂創作主體內在的生命追求,這種生命追求使音樂欣賞主體在音樂聯想中回返自身、重新發現內在的自我,并在音樂的激發中以個體獨特的情感去主動容納和跟隨音樂,達到主體間情感的融合和美感共鳴。這樣的藝術共鳴在《列子》看來,是在感覺山水意象的瞬間,因音樂的引導而體悟世界萬有生命形象的深層節奏的起伏。大自然無形的生命力在音樂音響傳遞中得到充分表現,內含著主體的人對于歷史、人生、宇宙的情思,使有限的主體進入澄明的境界,這個境界蘊含著渾沌的生存意識,以及人生和宇宙的哲理,不是對宇宙生存的抽象概括,而是一種神秘的感悟,因音樂表現的不受拘束于任何具體物象和語義限制的特性,展現出無限性的本體特征。《列子》把音樂意象提升到境界的層面,萬變歸一的終極自然之道,使作為技藝的音樂藝術通過最初的感知到達虛實之間的領悟,這是深層的審美分析,也是對生存之娛的最根本看法,成為《列子》全部生存理論的具體出入口,從而完成了在本體層面對音樂的最后界定。
倘若我們能細致地清理這些見諸各類著述中的音樂美學思想,特別是在哲學史上偏于一隅的一些作品,如《列子》文本中的音樂美學思想,總結歷史文著中的音樂實踐經驗,有助于科學地評價傳統文化中的音樂學遺產,進一步豐富我國現有的音樂史學資料,提高對本民族文化的認識,更好地為豐富社會主義民族音樂服務。
注釋:
①楊伯峻《列子集釋》,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77頁。下引此書只注篇名。
②《列子·湯問》。
③《列子·仲尼》。
④《列子·湯問》。
⑤(清)秋瑾:《詠琴志感》。
[1] 朱光潛.文藝心理學[M].上海:廣益書局,1936.
[2] 呂不韋.呂氏春秋[M].高誘,注.上海:上海書局,1986.
[3] 張前.音樂欣賞心理分析[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3.
[4]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