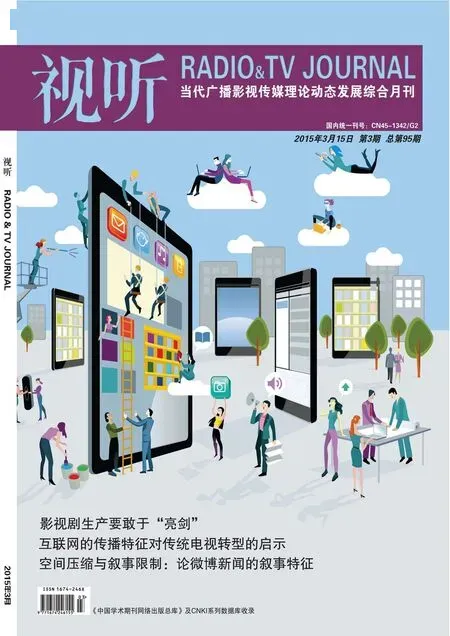淺析議題設置理論對紀錄片創作的影響
□ 王鵬飛
淺析議題設置理論對紀錄片創作的影響
□ 王鵬飛
隨著中國紀錄片進入市場化時代,紀錄片的創作活動日趨豐富。在帶來了市場繁榮的同時,紀錄片傳播價值的高低成為了決定紀錄片是否能占有一定市場、彰顯自身文化價值的關鍵。而與紀錄片傳播價值息息相關的一個傳播學理論就是議題設置理論。因此,在此時對紀錄片創作活動與議題設置理論的互動關系進行研究,具有創新性和功效性。本文對議題設置理論進行了闡述,從兩個時代下中國不同的議題設置模式入手,著重分析了正向和逆向兩種議題設置模式下紀錄片創作話語權的不同及其對紀錄片創作活動的影響,指出兩種議題設置模式各有利弊,互相不能取代,以期在紀錄片創作者進行紀錄片創作時起到一定的指導作用。
紀錄片;議題設置模式;話語權;傳統;逆向
議題設置理論(theagenda-settingtheory),也稱議程安排,是傳播學領域中的一個概念。最早是由美國傳播學者麥克姆斯和唐納德·肖提出。這一理論的核心觀點就是認為大眾傳播對社會某一事件——即議題的著重強調程度和該議題在公眾中受重視的程度構成強烈的正比關系。換句話說就是在大眾傳播媒介中越突出某一事件,對其進行大量、多次的報道,這一事件就會越因此而突出,形成議事日程。進而在一段時間內在受眾中形成對這一事件的集中議論,營造出一種輿論、意見的氛圍。這方面鮮明的例子可以用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李彬在《傳播學引論》中的一段話來闡釋:“某段時間內媒介把一個大國發生的軍事政變當成頭號問題對待,醒目的標題、突出的版面、號外、插播等接連不斷,于是公眾便覺得這場政變是眼下最重要的國際事件,一時間圍繞這個話題議論紛紛。公眾之所以重視這場政變,這么熱心地、急切地談論它,并非由于它真是當時最重大的問題,而僅僅是由于媒介給予它以最突出的地位而已。總之媒介報道什么,公眾也就越關心什么,這就是議程安排的基本思想。”議題設置雖然不能直接決定人們對事物的具體思考,但它通過大眾媒介的宣傳活動,賦予各種議題不同的顯著性,從而影響著人們對周圍世界的大事及重要性的判斷。紀錄片作為大眾傳播媒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身上必然擔負著議題設置所賦予的媒介輿論導向功能。因此,議題設置的變化將直接影響到紀錄片的傳播效果,再往深看一步,也就是說誰掌握紀錄片議程設置背后的話語權,出于某種傳播的目的決定某一議程,誰就給紀錄片的傳播效果劃定了一個限制范圍。紀錄片創作者或主動或被動地在這個限制范圍內進行紀錄片創作并傳播,完成議題設置的全過程。
在中國,很長一段時間里,紀錄片議程設置的話語權是掌握在國家統治階級手中的。這一方面是由于一個國家需要在群眾之間建立起一種積極的、向上的主流精神來維護和鞏固其政權。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用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念團結人民,實現共產主義社會是我國的國家政策和歷史使命。而紀錄片具象真實的受傳方式,讓其具備了很強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進行群眾性的、有效性的政治宣傳方面時展現出了強大的潛力,使它肩負了向廣大人民解釋國家政策、宣傳國家主張、傳播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任務;另一方面是受限于當時的社會環境,信息傳遞單向且封閉,受眾的認知范圍有限,并沒有主動參與到傳播中來,往往是消極盲目地被動接受和認知媒介傳遞來的信息,主體意識受到壓迫。兩方面原因的綜合導致了官方或者政府機構對紀錄片議程設置話語權的控制。在此前提下,當統治階級在一定階段內想達到特定傳播效果時,就通過議題設置過程來達到目的。首先選擇、編輯和提供符合議題的信息,給處于大眾傳播媒介一方的紀錄片創作者,然后由創作者根據包含議題的信息,在議題劃定的限制范圍內選擇可表現議題的題材,制作多部紀錄片并傳播出去產生議事日程。最終達到公眾對議題的關注和產生議論,并在潛移默化中接受發動議程設置一方所希望傳播的社會主流意識形態。例如,關于展現歷史偉人的紀錄片,像《毛澤東》《周恩來的辦公室》《忘不了的鄧小平》等,是從一個人的角度來講述中國的現代發展史,告示后人莫忘革命前輩所作出的艱苦奮斗,珍惜現在;樹立先進人物的紀錄片,如《人民的好兒女》《永遠的先鋒戰士》《道德之光——全國道德模范人物志》等,是為了展示時代精神,引領人們的行為規范;最多的是記錄重大事件的紀錄片,諸如《新中國的誕生》《讓歷史告訴未來》《解放》等,是展現建國過程,弘揚紅色精神,《香港滄桑》《澳門歲月》是反映國家政策——一國兩制的正確性,《揮師三江》《汶川大地震》都是對突發事件下國家的應急反應及全國人民對受災群眾的熱心幫扶的最好例證;即便是自然歷史類紀錄片,如《話說長江》《絲綢之路》《森林之歌》等,也暗含著深沉的民族自豪感的和炙熱的愛國精神。所有的這些紀錄片,都是在反映國家提倡的主流意識形態,是傳統話語模式下議題設置的正向傳播,占據了紀錄片市場絕大多份額。但隨著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加速轉型,這一情況發生了改變。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開始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積極轉型,政府對媒介的嚴格控制逐漸放開,大眾傳媒身上的政治氣息開始變淡,轉為向市場規律靠攏。雖然這并不意味著大眾媒介拋棄了其所擔負的傳播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社會使命,而是變得比以往更需要考慮收視率等市場因素對自身發展的切身影響,也就是說考慮受眾的消費心理。另一方面,政府對大眾媒介的態度由過去的“圈養控制”到現今的“散養控制”,這導致了輿論環境的開放,受眾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放,主體意識增強。他們不再滿足于被動地接受外界塞給他們的信息,而是渴求主動去探尋、去選擇自己想要的信息。這兩方面的共同作用讓傳統話語模式下的議題設置受到了頗大的沖擊,新興話語模式下的逆向議題設置開始興起。
新興話語模式下的話語權不再是掌握在官方或者政府機構手中,而是由受眾控制。新興話語模式下紀錄片的創作工作從受眾產生預期議題中開始,預期議題也就是受眾可能會感興趣的事件或他們正在感興趣的一類事件,他們想要知道這些議題的后續及更多的信息,但他們卻無能力直接影響大眾媒介發揮議題設置功能,甚至沒有發覺自己正在制造預期議題;然后,紀錄片創作者收集他們通過各種途徑獲得的不同預期議題,分析、預判出哪些議題更有吸引力,會在更大的受眾群體中找到共鳴、產生議程,亦或是更有力量,與創作者自身心靈產生強烈碰撞,讓創作者情不自禁想把該預期議題實現,在這些議題的限制范圍內選擇題材并拍攝成片;最后傳播給受眾時是由多部紀錄片同時在受眾中產生討論和思考,當不同創作者選擇了同一預期議題時,就形成了針對該議題的議程。
從中不難看出,傳統話語權模式下紀錄片議題設置的產生者和推動者是統治階級,實行者是紀錄片創作者,接受者是議題作用的廣大受眾。而新興話語權模式下議題設置的推動者和執行者都是紀錄片的創作者,強調了創作者的對預期議題的判斷、分析、挖掘的能力,議題的產生者和接受者都是受眾,但卻是兩個不同概念下的受眾:一個是產生預期議題的無意識小眾群體,一個是接受最終議題的有意識大眾群體。這兩種議題設置模式更大的區別在于,傳統模式下是一個推動者,對多個實行者的正向議題設置,很容易達到議題設置的最終目的,傳遞某一特定的意識形態,但不易被受眾真心喜愛和接受;而新興模式下是多個推動者,對多個實行者的逆向議題設置,每個受眾都很容易從中找到自己喜歡的議題,卻也因受眾的分眾選擇而讓推動者的意識形態難以最大程度地形成議程。在現實社會中,傳統的議題設置與新興的議題設置共同存在,紀錄片創作者只是出于自身傳播目的、所處位置等的考慮,選擇不同話語權下的議題,進而影響到自己的題材選擇過程,實際上兩者各有其利弊,誰也不能替代誰,共同影響著紀錄片的創作過程。
1.唐晨光.新中國60年紀錄片美學形態之流變 (之三)轉折期(1979-1989):紀錄片美學形態及特征[J].電影評介,2010(12).
2.李墨田,王東玲.從《馬背諜影》看選題人文觀[J].中國電視(紀錄),2010(9).
3.魯佑文.把鏡頭對準社會及其主流人群——中國紀錄片贏得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節點 [J].聲屏世界,2004 (5).
4.宋繼昌,劉敬東.用我們的紀錄片到世界上發言[J].北京廣播學院學報,1996(1).
5.邵雯艷.在功利與唯美之間——傳播視野中的紀錄片選題[D].蘇州大學,2003.
6.李楊.新世紀歷史文化電視紀錄片研究[D].廣西大學,2008.
7.李斫.國際視野下的中國紀錄片 [D].東北師范大學,2010.
8.鄒毅.當代中國語境下紀錄片的發展及其創作原則[J].吉林藝術學院學報,2005(3).
(作者單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學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