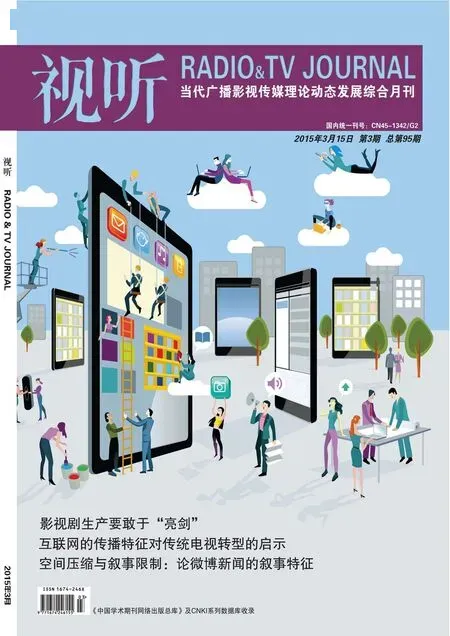以編碼解碼的視角淺析明星真人秀節目
——以《花兒與少年》為例
□張然
以編碼解碼的視角淺析明星真人秀節目
——以《花兒與少年》為例
□張然
自湖南衛視真人秀節目《爸爸去哪兒》取得高收視率、高網絡點擊量和高社會關注度的豐碩成果后,國內各級衛視意識到明星類真人秀節目蘊藏著巨大的市場潛力,紛紛著手打造以明星參與為核心的真人秀節目。四川衛視《兩天一夜》和浙江衛視《爸爸回來了》《奔跑吧兄弟》等明星真人秀節目出現在觀眾的視野。然而,這些重金打造的高收視率節目大部分都是引進韓國電視臺的節目版權,明星真人秀的節目策劃、制作形式甚至制作團體大多來自韓國電視媒體的指導。《花兒與少年》這檔明星真人秀打破了這一局面,它由湖南衛視于2014年第二季度推出。作為國內一檔全新的原創節目,《花兒與少年》收獲口碑、收視雙豐收,被贊“國內頂級真人秀”,此節目團隊所展現出的創新能力、執行能力、制作能力以及創造熱點話題的能力值得業界學習。本文試從文化研究的編碼解碼理論為視角,淺析《花兒與少年》節目成功背后的緣由以及值得國內媒體借鑒的要素。
一、編碼/解碼理論
在傳播領域廣為人知的編碼/解碼理論,由當代文化研究之父斯圖亞特·霍爾提出,他將電視話語意義的產生分為三個階段:編碼階段,即電視節目制作中對傳遞信息的編排設計;成品階段,指電視作品制作完成后,在播出時變成一個開放的、多義的話語系統;最后是解碼階段,即觀眾在收視過程中對所傳遞信息的解讀。①通過對電視明星真人秀節目的編碼/解碼模式分析,可以更好地認識此類節目在傳播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以及如何做到傳播效果的最大化。
二、《花兒與少年》的“編碼”特點
(一)設定情景:境外旅行的情境下放大人際關系的沖突
《花兒與少年》真人秀的主題是旅行,拍攝地點途經意大利、西班牙兩國共六個城市。節目中對異國風景的攝制大量采用航拍等技術,節目配樂、字幕和畫外音對異國風情的注解抓住了受眾的求知好奇心理,不少受眾收藏節目中出現的旅游景點、路線、旅館等信息,表示這些可直接作為境外游的攻略。節目組正是抓住目前國民對幸福體驗的追求,設置了一個滿足受眾信息需求的情境。
利用境外旅行的情境,節目組把境外旅行中陌生的異國、不習慣的習俗、不相通的語言等環境因素融合規則貫穿于節目中,對其展現人際關系沖突的主線有放大效應。例如第一期節目中,行李眾多的明星們下飛機到達羅馬,在機場到旅館的一路中充斥著生疏、語言不通等因素而造成明星們之間的意見不合,這些矛盾的爆發正是由于明星對異國的陌生、語言不通的原因造成并放大的。這一片段作為預告片反復出現,也是這期節目的收視高點。而之后各期節目中呈現出的矛盾也都有環境因素的放大效應。
(二)選擇參與者:覆蓋各年齡層受眾群,精準定位突出個性
《花兒與少年》的嘉賓布局中,女性明星嘉賓在20歲到60歲之間,以每隔十年的年齡差選一位,每一位的生長環境和觀念意識都有很大差異,這既可以體現當下各個年齡層的想法和差異,也覆蓋到各年齡層的受眾群體。
節目組對于參與真人秀的明星嘉賓均有定位,按照定位選擇明星。《花兒與少年》的總導演廖珂在《我的紀錄片》中回顧對李菲兒的選擇時談到:“我們需要一個年輕、活潑、漂亮、自理能力沒那么強的姑娘。在接觸過的(候選人)里面,她比較符合我們的想法。”可見嘉賓的個性定位節目組早已規劃,符合該個性的候選明星只需對號入座。節目組把差異化女星組合與青春少年之間的多重人際關系進行疊加,組成了微縮版的人際代表圈。
(三)節目設置:設定“求生存型”規則以制造節目最大看點與矛盾爆點
《花兒與少年》節目的亮點不是七位嘉賓明星享受歐洲旅行的經過,而是他們在無經紀人、無助理、無智能手機且限制費用等規則下的自助“享苦”旅行。規則的設置即矛盾的鋪墊,它使明星們進入一個求生存型的現實體驗,把觀眾帶入觀看一場明星們與陌生環境不斷奮斗、平衡各種人際關系的真人秀。節目內容在這些規則的作用下變得緊張激烈,充滿看點與爆點。
規則下的旅行不再只是玩樂,而是變為普通生活的一部分,需要掙扎、斗爭與思考。細數節目中各項“求生存型”的規則,緊湊密布。其一,全程自理。上交錢包、智能手機等一切工具性的幫手;不允許經紀人、助理等任何相關的幫助;為期十五天的旅行全部由明星自助規劃,自行預訂酒店、餐廳、旅行景點等。全程自理的規則旨在把明星置于無人可求的環境,明星只需到達這個陌生又沒有援助的環境下即可產生看點、摩擦矛盾,明星們掙扎生存的畫面吊足觀眾胃口。其二,限制經費。由于嘉賓明星們對團隊境外游的陌生,各項支出難以達到合理規劃已成必然,而限制性的經費更使旅行變得捉襟見肘,沒錢的窘境進一步加劇節目的戲劇性,觀眾帶著“旅行還能走多遠”的心態全程鎖定節目。以上規則的設定足以可見《花兒與少年》節目組高水平的策劃能力和制造熱點話題的能力。
(四)后期剪輯:集中突出定位個性,放大剪輯傳播效果
《花兒與少年》總導演廖珂在一次采訪中曾談到,節目組拍攝“平均每天的素材量是103個小時,一共拍了17天,節目一共8期,每期約90分鐘,平均2天剪輯成一期”。②在有限的時間內以何種視角呈現何種內容,后期剪輯對節目成品有重要決定作用。
從節目的播出情況來看,節目組剪輯的視角主要放在突出明星嘉賓的定位個性。正如節目第二期的導入畫外音所概括的各位明星定位:面對眾多麻煩的“導游”、“角斗士”般的大姐、“隨時地震”的二姐、“嬌美率真”的三姐、“強迫癥完美賢妻”四姐、“缺根筋”的五妹、來自火星的會計弟弟。《花兒與少年》導演李超曾在《我的紀錄片》中說道:“我們在人物設定上從很多因素考慮,前幾期對華晨宇笑點部分的表現集中在吃、發呆。這些部分是因為剪輯上的一些東西會放大,其實華晨宇在整個旅行中做了很多事,沒法在完整的九十分鐘成片里去展現。”可見,華晨宇由于他火星弟弟的定位,表現其性格其他面的鏡頭就會被剪掉,而留下展現火星呆萌特質的鏡頭則被集中放大傳播,以引起熱點。
三、觀眾的“解碼”特點
斯圖亞特·霍爾提出,電視作品播出后,就要經歷最后一個階段,受眾的“解碼”解讀。具體來說,受眾的解碼模式可能有偏好解讀、協商解讀、對抗解讀三種模式。③偏好解讀即受眾對節目組所傳達的立場、內容等信息意義的全盤接受,編者的“編”與受眾的“譯”完全對等;協商解讀指受眾對節目組所傳遞的意義持協商態度,既不完全接受,也不完全否定,贊同節目部分話語權利的同時堅持表達自己對節目的解讀;對抗解讀則是指受眾以一種截然相反的方式思考與質疑節目組所傳遞信息的意義,與節目所傳達的價值觀或意識形態對立,對其持批判或抵制的態度。
以上三種解讀模式是相互聯結的,正如觀眾對《花兒與少年》真人秀也同時存在三種模式的解讀一樣。隨著節目的播出,觀眾參與節目中不同話題的討論,表達著偏好接受、協商中立、對抗反思的各種立場,闡釋著代表自己理解的解讀意義。
針對觀眾不同模式的解碼解讀,《花兒與少年》節目制作組抓住了傳播過程中受眾的“反饋”這一環節,在最后一期的呈現中對觀眾的解碼進行了一次“再編碼”。節目制作組大膽革新,破除往期節目單線剪輯、表達單一主導意義的模式,以“日歷”為載體,用倒敘結構把最后的素材剪輯成三個平行的故事,變單一結局為多樣開放式結局,讓每一種解讀都有了自己的個性,收獲了觀眾的熱烈討論與業內人士的交口稱贊。由此可知在傳播過程中,編者重視受眾的“解碼”,并善于利用解碼進行再次編碼,可以收獲更大與更優的傳播效果。《花兒與少年》真人秀節目最后用開放式結局對主題意義的升華,體現了節目組高水平的創新能力與執行制作能力。《花兒與少年》這檔明星真人秀節目的成功“編碼”與“再編碼”值得媒體同行們的學習與借鑒。
①③羅鋼,劉象愚.文化研究讀本[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②黃柏雪.“花兒”為什么這樣紅[J].綜藝報,2014(5)
(作者系江西師范大學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