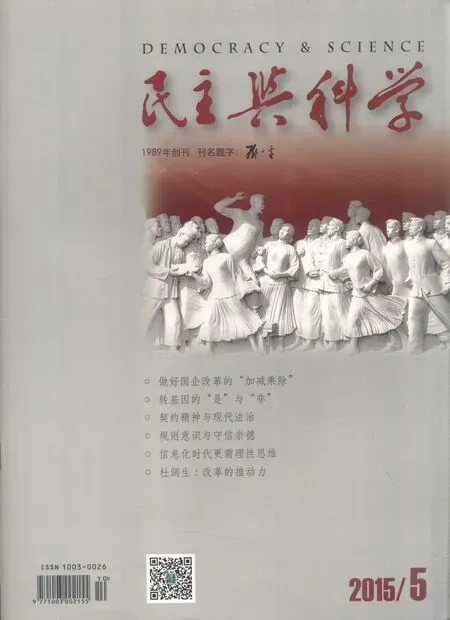王卓然與斯諾的《前西行漫記》
■ 王世鐸
王卓然 (1893—1975),字回波,遼寧撫順人。民國時期東北著名教育家,張學良將軍的重要幕僚。早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曾任東北大學教授、東北大學秘書長、代理校長,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理事,東北救亡總會主席團成員,《東方快報》社長,《反攻》雜志社社長,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等職。1947年赴日本,1951年回國定居天津。1955年任國務院參事。“文革”入獄,含冤去世。
王卓然的名字與九三學社發生關系,最早見于1946年5月9日重慶《新華日報》所載的報道,稱王卓然在九三學社成立大會上發表自由演說,并被選舉為九三學社理事。
1948年,中聯出版社刊印的一本《中國黨派》小冊子,在九三學社章節中,列舉了褚輔成、許德珩、王卓然、張西曼等4人,對王卓然的介紹是:“王卓然系遼寧人,曾任東北大學校長,與張學良關系密切,亦系不滿政府者。”除此之外,關于王卓然的更多活動,卻是難覓蹤跡。
隨著九三學社中央搶救史料工作的開展,2007年5月,筆者在王卓然的故鄉撫順蓮島灣村,意外獲得大量信息。1975年,王卓然在北京秦城監獄保外就醫時去世。“文革”后平反,骨灰歸葬故鄉。1993年張學良將軍在海外特為亡友題寫了墓碑。另外發現,村中小學赫然矗立著王卓然家屬捐建的“卓然圖書館”,館內樓上辟有 “王卓然紀念室”……更為慶幸的是,通過村長提供的一個信封,竟在北京朝陽門東大橋斜街的一處公寓,尋訪到3年前從美國歸來定居的王卓然長子——王福時先生。

當時,王福時先生已經96歲,如此高齡,卻是記憶清晰,精神矍鑠。說起父親王卓然,樁樁件件,如泉水噴涌。其間,王卓然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親密交往的軼事,便從漫漶的歷史背景中,不期然地迎面走來……
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1905—1972),1928 年 由大洋彼岸來到中國上海,擔任《密勒氏評論報》助理編輯,后兼任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特約通訊員,也曾在燕京大學兼任講師。
1936年6月,斯諾沖破重重障礙,進入陜北蘇區采訪,寫出了舉世聞名的《紅星照耀中國》。然而,多不知曉,斯諾能夠進入陜北蘇區采訪,與張學良的幫助有著密切關系。更鮮有人知,在《紅星照耀中國》和中譯本《西行漫記》出版之前,還另有一部中譯本《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在國內出版——《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2006年重印改稱《前西行漫記》)的出版發行,比英國戈蘭茨出版公司出版的英文版《紅星照耀中國》早6個月,比胡愈之先生在上海以復社名義出版的中譯本 《西行漫記》早9個月——此書在北平一經出版,便迅速傳遍大江南北,又先后在上海、陜西等地被秘密翻印,廣為傳播。多種版本均被國民黨政府列為禁書。
然而,這部先聲奪人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以下簡稱《印象記》)的出版發行,與王卓然以及其子王福時有著直接關系。
1936年6月斯諾赴陜北蘇區采訪,所見文獻幾乎都講斯諾是在宋慶齡的聯系幫助下,冒著生命危險,經西安進入陜北蘇區的。而在有關王卓然的史料中,卻有“王卓然護送斯諾去延安采訪”之說(見遼寧人民出版社《王卓然史料集》1992年12月出版),具體細節卻語焉不詳。據王卓然《自傳》和年譜,他于 1936年5、6月間,兩次由北平赴西安、洛川,晉見張學良。之后便回北平,由東北大學去職,準備出國考察。其間,并無去過陜甘寧邊區的記述。
不過,斯諾的陜北之行,得到了張學良的幫助,則是不容質疑的事實。要知道,那時蔣介石正在督令西北加緊剿共,對陜北蘇區的封鎖十分嚴密。如果沒有張學良將軍批準,取得通行證,一個美國記者是很難通過封鎖線,從“白區”順利進入“紅區”的。
1991年5月,美國華美協進會在紐約為張學良90大壽舉行祝壽宴,張學良的親友、老部下紛紛赴會祝賀。斯諾的第一任夫人海倫·斯諾聞訊,專門寫了一封賀信,托人呈遞張學良。信中特別強調,如果沒有張學良的幫助,他們夫婦當年不可能試圖冒險去陜北紅區:
親愛的張學良少帥:我最后一次見到您是1936年10月在西安,當時我28歲,1907年出生,現年83歲,而您已年過9旬了。經歷漫長的危難歲月,居然您的身體還如此之好,實是一個奇跡,我們以其他中國人所沒有的禮遇歡迎您到美國來。我常常回首1935年—1936年在北平和西安的日子……我的丈夫埃德加·斯諾,1972年因癌癥逝世,他始終認為你是一位重要和杰出的東方人物,你在1936年雙十二軟禁蔣介石,確實是扭轉危局的一大壯舉。如果沒有您,埃德加·斯諾決不會試圖去保安,完成一本他的經典圖書《紅星照耀中國》。并且,我也不可能試圖在1937年獨自去闖延安……(《海倫·斯諾給張學良的信》見《前西行漫記》補錄四,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6年出版)
據斯諾《印象記》,他是于1936年6月從北平乘平漢線火車到達鄭州,然后轉隴海線抵西安的。這之前,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方針。4月9日張學良與周恩來在延安會談,就紅軍和東北軍在抗戰中所擔負的責任、對日作戰的戰略、兩軍互不侵犯、互相幫助和經濟通商等問題進行了討論,達成相應協議……西北“剿匪”副總司令張學良的這些秘密轉變,使斯諾一直無法實施的“紅區”采訪計劃,成為可能。然而,遠在北平的斯諾是如何獲悉這種極為機密的變化的?代為聯絡的人又是誰?由于考慮當時的政治情勢,斯諾在書中沒有透露。
王卓然與斯諾夫婦在北平早就熟識,而王卓然又是張學良極為倚重的助手。雖然王卓然陪同斯諾進入陜北采訪之說不足采信,然而,王卓然居中牽線,為斯諾采訪計劃取得張學良的批準,卻是極有可能。海倫在致張學良的同一信中就提到:
我期望趁您記憶尚好的時候盡快出版一本自傳,因為這一段是本世紀中國歷史最主要的關節之一,從1931年日本接管,引起1936年的政策改變,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整個階段。你的很多東北同鄉常來我們北平的居所,如東北大學校長王卓然先生和他的兒子。我們在北平有許多東北朋友,那時北平的家經常是支持你的人聚會的中心……
1937 年“七七事變”后,斯諾在北平的住處成了難民庇護所。到他家避難的,就有王卓然。
據王卓然《自傳》,也可看出他與斯諾的交誼非同一般:
7月7日爆發 “盧溝橋事變”,戰事突起,到了7月28日,南苑失守,趙登禹陣亡,日本人即將入占北平城。我們這個抗日小集團,為了免遭日寇毒手,采取緊急措施,《東方快報》與《外交月報》全體人員發給雙薪及路費,各覓安全辦法,約定在天津租界集合。平津火車已斷,我的家人早去天津,我避到東交民巷美國記者斯諾家里,許多重要珍貴的抗日文件與資料,也藏到他那里。在他家住了兩星期,到8月15日,我與斯諾同去天津。我有一只很寶貴的手槍,是漢卿先生贈我的紀念物。斯諾說他將再去陜北采訪,我請他將手槍代贈給毛主席,以后是否捎到就不知道了……(見《王卓然史料集》)
王卓然的長子王福時,1931年在東北農學院讀書。“九一八”事變,參加反日示威,流亡北平,參加反帝大同盟。先在燕京大學借讀,1932年考入清華大學社會學系,1935年畢業。
王福時回憶,斯諾夫婦在北平先后住過3處地方:煤渣胡同、海淀燕京大學附近、還有盔甲廠13號——即現在建國門內北京火車站的位置。1935年爆發“一二·九”學生運動,那時,學生領袖黃華、黃敬、宋黎和姚依林等,經常在盔甲廠斯諾家集會,策劃推動更多的外國記者把事件真相向全世界進行報道。王福時回憶:
我是在清華畢業后結識斯諾夫婦的,常和一部分學生到他們家議論時政,我還將郭達介紹給斯諾當秘書。雙十二“西安事變”后,我主持發行油印《公理報》,介紹“西安事變”真相,歡迎紅軍北上抗日,更是常去他們家探聽消息……1937年“七七事變”……許多躲避日軍拘捕的抗日人士藏到他們的家,其中有我的父親王卓然。鄧穎超大姐也是在他們的掩護下偽裝乘火車到天津,進入英法租界,再搭船南下的。有些在他們家避難的學生,趁黑夜越過城墻到郊區參加抗日游擊隊,還有游擊隊將搞到的珠寶,經他們介紹變賣,以籌集資金。(見王福時《前西行漫記》重版前言和補錄一 《我陪海倫·斯諾訪問紅色延安》,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6年出版)
海倫·斯諾于1991年給王福時的信也提到:
你是那個 “真誠而高尚”年代的一部分,我腦海中一直記著這樣一幅畫面,您坐在我們家的一個角落里,沉默不語,但你眼中有一種“威爾士”感覺的風度,被遺棄、孤獨、受挫和尋求鼓舞的眼神……(見《前西行漫記》補錄七)
1936年10月,斯諾訪問陜北回到北平,把一大堆大包小包交給海倫。海倫立即到一個德國人開的照相館將幾十個膠卷沖洗出來,同時把毛澤東在江西的舊照片進行了翻印。斯諾一面忙于寫作,一面到處開座談會作報告。海倫也忙著整理資料,寫文章和核對全部照片的說明文字。斯諾很快將整理出來的一部分英文打字稿交給王福時。王福時拿到了稿子,意識到這批新聞報道和文章十分重要,應該盡快發表。時間緊迫,他組織斯諾的秘書郭達、《外交月報》工作人員李放和李華春,一起立即翻譯。請東北流亡北平的學生康德一幫助按陜北帶回的原圖繪制出紅軍長征路線圖,照片則去虎坊橋附近一家印刷所制版。大家通力合作,爭分奪秒,常常是邊翻譯邊排版邊校對,交叉進行。王卓然則安排《東方快報》的印刷工人加班加點積極配合,于短短的2個月內完成了印刷裝訂工作。他們將這部譯著定名《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避開北平,以“上海丁丑社”名義,于1937年3月至4月間秘密出版發行。
王福時還補充說:
當年促成斯諾夫婦去延安,張學良起了不小的作用。同時,《印象記》的出版與張學良將軍也有一定的關系,他委托并資助我父親王卓然主持在中南海出版 《外交月報》和《東方快報》。而出版《印象記》一直得到王卓然和他手下員工的支持,從經理到車間主任,不少人參與了工作,且整個工作是在中南海 《東方快報》印刷廠內進行的。至于斯諾夫婦,他們不僅無償供給我書稿和資料,還給予經濟贊助,并提供一部分紙張……(見《前西行漫記》重版前言)
9個月后,胡愈之先生在上海根據英文版翻譯出版了《西行漫記》。《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與《西行漫記》略有不同,即是節譯本,又有不同內容。《印象記》全書共300頁,包括34幅照片、10首紅軍歌曲、《西行漫記》所沒有的幾篇重要文章,其中有毛澤東與斯諾4次長談的訪問全文,斯諾在北平的一次講演,譯載了美國經濟學家韓蔚爾發表在《亞細亞》雜志上的3篇有關四川紅區情況的文章,毛澤東與美國記者史沫特萊關于《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的談話——斯諾把這篇稿子交給王福時,并未提到史沫特萊,所以文前沒有標明作者,后來才知道此件十分重要,是毛澤東托人送給斯諾的——此外,還附載了署名廉臣的《隨軍西行見聞錄》。可以說這本書與 《西行漫記》各有所長,珠璧互見。
《印象記》首次發表的署名廉臣的 《隨軍西行見聞錄》,實為陳云之作。他假托一名隨紅軍長征的被俘國民黨軍醫,記錄下長征的足跡,描述了沿途所見所聞,多次戰役和突圍,如強渡烏江、金沙江和大渡河。舉凡官兵作風,軍事形勢,山川地形,風土人情,軍民關系,以及行軍中的毛澤東、周恩來和其他一些紅軍領袖,都描寫得繪聲繪色,是記錄紅軍長征的第一手寶貴資料。
《印象記》所載34幅有代表性的照片,既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徐特立、林伯渠等中共領導人的身影,也有紅軍戰士、文工團員、護士等日常生活寫真,加上斯諾夫婦精心編寫的說明文字,生動幽默,饒有情趣。如“妙齡女匪”“匪也會玩網球”等,今日讀來仍然充滿神奇的魅力。
“文革”時期風靡全國的毛澤東戴紅軍八角帽的照片,就是憑借此書首次面世的。且看照片的說明:
毛澤東——蘇維埃的巨人。他是紅黨的最高領袖,1934年被舉為蘇維埃主席。毛氏在1893年生于湖南一貧家,其經歷與性格頗類似林肯,最初在農家當雇工,因奮斗的結果,長沙師范讀書,后入北京大學,與李大釗相識,參加國民革命,為當時國民黨中委。國共分家后,遂轉戰華南各省,從事擴大蘇區運動。其為人寬大、誠懇、頗富民主精神及對弱者之同情心。毛氏自奉甚簡,衣食住皆與士兵同,中央曾懸賞25萬元捉之,他此次領導了有名的長征,可見其軍事天才殊不下于其政治經驗也。
再如周恩來、賀子珍照片的說明:
周恩來——軍委會副主席。雖然生了滿面胡須,但是他還很年輕,剛37歲,他曾一度做蔣介石的幫手,革命把他們分開,成了死對頭,而10年后的今天,借著雙十二的機會,又與蔣氏在西安會見,商討在共赴國難的旗幟下,把兩黨重新結合。這張照片是在白家坪照的。
毛澤東的太太——她名叫賀子珍,湖南師范畢業,在1927年參加共產黨,做宣傳工作,后來毛澤東的妻子被何鍵殺了,她便與毛澤東結婚,10年來從事戰斗,身上受過18處槍傷,但是仍然很健康。
《印象記》書中配發的10首紅軍歌曲(包括曲譜),后來多已失傳。如鄧穎超在陜北慶祝平型關大捷大會上領唱過的《紅軍勝利遠征歌》,歌詞已記憶不全。直到新華出版社在王福時家看到他保存的原版《印象記》,才將歌詞補充完整。
1936年秋,海倫想步斯諾后塵,通過封鎖,進入陜北蘇區采訪,未能如愿,唯一的收獲是在西安事變前,采訪了張學良將軍。
1937年4月,王福時義務擔任海倫的翻譯,陪同海倫作第2次西北之行。這次沒有了張學良的幫助,海倫冒著極大風險,在西安擺脫軍警監視,終得進入陜北。在云陽,海倫受到彭德懷的熱情款待,并邂逅了李伯釗和丁玲。第2天,他們融入了有成千上萬手拿紅纓槍的農民列隊參加的“五一”節慶祝大會。王福時還與彭德懷進行了一次乒乓球交鋒。
我陪同海倫到達西安不久,一柳條箱《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也隨后到達。毛澤東在延安會見我們時,我把這本書送給了他。在場的黃敬說,那時他們本來也想出一本類似的書。我和陳翰伯在延安停留10多天,回西安的路上同蕭克將軍搭同一輛車。我也把此書送給他1本,他對紅軍長征路線圖看得特別仔細。后來毛澤東發表《論持久戰》,當中引用毛澤東和斯諾關于中日問題的談話,毛選注釋說明是引自 《印象記》一書……(《前西行漫記》補錄一,王福時《我陪海倫·斯諾訪問紅色延安》)
王卓然與王福時父子主持翻譯出版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在當時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正如1979年4月,海倫給王福時的信中所說:“……可以想象,你所出版的埃德加的書中譯本在中國猶如閃電一擊,使人們驚醒了。”這本書給千千萬萬青年提供了思想滋養,許多青年學生看了《印象記》或《西行漫記》,紛紛從四面八方奔向延安,奔赴抗日前線。后來,斯諾在《大河彼岸》一書中說:“當年的年輕讀者今天與我重逢時,很多已成為中國第二級或第三級領導人了。”
當筆者訪問王福時先生時,恰值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為了紀念中國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將《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更名為《前西行漫記》重新出版。當年主持翻譯此書的青年,如今已是皤然老翁。王福時先生珍藏的那本頹舊的《印象記》,與散發著油墨清香的新版《前西行漫記》,并列在書架上。兩個時代,半個多世紀的光陰在此悄然會聚,見證著王卓然父子與美國記者斯諾夫婦的友誼,縈回著那段崢嶸歲月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