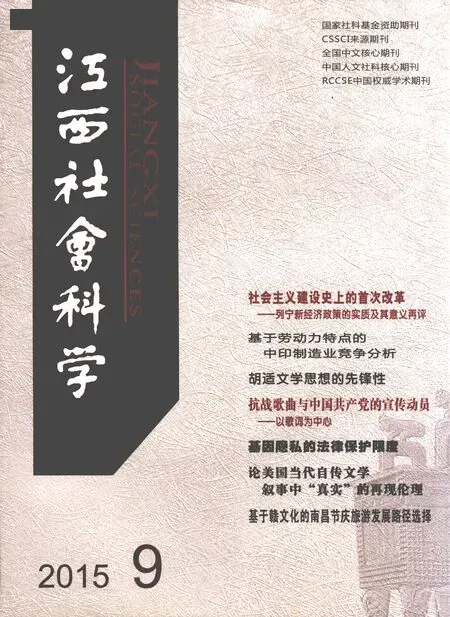審慎地啟蒙:從“有用性”角度看黑格爾對啟蒙的批判
■胡 芮
啟蒙構成德意志古典哲學的思想根基,18世紀德國古典哲學的集大成者黑格爾就生活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和思想語境之中。黑格爾的啟蒙觀與其對康德理性啟蒙思想的反思具有某種聯系,同時,宗教改革的大歷史背景同樣影響著這位德國古典哲學大師。作為黑格爾學術氣質的代表著作——《精神現象學》以人類精神現象、意識為研究對象,旨在揭示精神運動發展的軌跡。在黑格爾看來,由于精神自身內在地包含著自己的否定性,因而能不斷地運動和發展,啟蒙正是出現在“倫理——教化——道德”的辯證發展過程之中,確切地說是精神自我異化和分裂(教化)的結果。[1](P46)這與啟蒙思想家高揚理性的做法具有明顯的區別,因此,重新檢視學術資源,便成為正確理解啟蒙的必要環節。
一、直面現實的“啟蒙運動”
啟蒙運動在歐洲的發展有四個主要區域,即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意大利的啟蒙運動主要集中在藝術領域,和黑格爾思想發展的聯系不大。其他三國的啟蒙運動在思想領域催生了大量的哲學作品,它們均在不同的方面對黑格爾的思想產生著影響。黑格爾從來沒有在自己的著作中肯定啟蒙運動對其思想的影響,也找不到康德似的對啟蒙的熱情肯定,黑格爾對啟蒙的態度是批判和揚棄的。學術界對于黑格爾與啟蒙的關系出現兩種截然相反的論點,亦即黑格爾對啟蒙思想究竟是接受還是批判。不論黑格爾從思想上接受啟蒙的觀點與否,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啟蒙事實上對黑格爾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啟蒙運動的現實起點是對歐洲教會統治的反叛。馬丁·路德對宗教的批判之所以具有力度,原因就在于他的批判不僅從思想層面,更為重要的是從現實的層面揭示了教會的墮落。奧古斯丁以來,強調屬神靈魂“圣潔化”的傾向事實上割裂了現實倫理生活與 “上帝之城”的聯系,教會作為“上帝之城”的代表統治世俗世界,卻并沒有將神的恩典惠及大眾,反而在神恩的幌子下產生了大量的罪惡。這種“圣潔精神”與罪惡現實的巨大反差不能從神學理論中得到合理的解釋,所以,身為牧師的馬丁·路德特別在意“譯經”事業,他十分清楚輝煌的教堂如果不是立足于世俗生活的勞動實踐便不可能熠熠生輝,這種肯定世俗勞動兼具倫理和宗教意義的傾向具有重大影響。宗教開始一改逃離現世義務、冷漠無情的形象,轉而變得更加關注現世生活,其實質在于協調神圣靈修和世俗生活之間的巨大張力。
經濟問題看似是一個實踐領域的話題,而在中世紀之后的歐洲歷史語境中卻有相當深刻的倫理意蘊。在亞里士多德那里,“經濟”無非只是“家政學”或者“理財術”一類的東西,在正統的基督教文化中,經濟活動從本質上講是罪惡的。直到啟蒙之后,“天職”觀逐步形成,勞動、經濟關系才開始和倫理發生聯系。韋伯曾感慨道:“世俗職業生活的這種倫理意義是宗教改革、特別是路德最重大影響的成就之一,這實際上是毋庸置疑的,而且簡直可以視為一種老生常談。”[2](P36)啟蒙運動開始將以奧古斯丁為代表的“上帝之城倫理”拉回人間,宗教改革之后的倫理逐步朝著“市民倫理”的方向前行。作為啟蒙運動重要環節的宗教改革事實上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時代,這個時代的哲學最重要的特征便是肯定“世俗”的神圣意義,并為世俗生活的權利提供理論支持。古典時期的“德性”開始向現代意義的“自由”轉變。
宗教改革釋放出了巨大的社會動力,一個生機勃勃的歐洲開始展現出其獨特的人文之美。然而,改革同樣帶來了舊秩序的崩潰,社會動蕩、思想紛爭的局面造成了巨大的社會災難。舊秩序崩解之后歐洲社會亂象以政治騷亂、宗教戰爭等殘酷的形式表現出來。因此,德國啟蒙哲學家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要回應在宗教權威墜地之后,如何通過理性將德意志民族重新帶回統一的歷史進程之中。這一時期的德意志哲學家萊布尼茨開創了現代倫理社會的經典秩序設計,其理論精髓在于倫理——政治的高度耦合。這一時期的理性所具有的特點是:論證具有自由個性的“單子式”的個人如何與其他主體實現同一。由此可見,德意志啟蒙哲學家雖然高揚理性的利刃以破除舊秩序的荊棘,但背后卻依然眷戀著神權一統下的穩定社會。因此他們對待啟蒙的態度普遍是曖昧的:一方面既肯定啟蒙理性的價值,另一方面又擔憂啟蒙理性可能招致的混亂局面。
黑格爾對待啟蒙的態度體現了啟蒙時期哲學家的普遍特點,他對啟蒙一直持審慎的批判態度。為了避免過度夸大啟蒙的作用,黑格爾一開始就將啟蒙定義為追求實效的意愿,將其作用的發揮限定在實踐領域。這里體現出他與康德的巨大不同。一般認為,在康德的觀念中,理性實現了人類的啟蒙。而黑格爾則相反,認為啟蒙最終達成了某種理性。兩者的不同源自他們對理性的不同理解,有學者指出:“康德認為理性是人類的主體能力,具有先驗性、普遍性、終極性。而黑格爾的理性就是意識確知它自己即是一切實在的這個確實性。”[3](P71)理性是人類所具有的特殊意識,也是人類意識發展的一個階段。人類意識發展的終極目的在于理性自由地擁有和把握自身。
黑格爾將啟蒙視為掃除宗教信仰陰霾的重要利器,他認為:“純粹識見使用概念的力量去對付的這個獨特的對象是信仰。”[4](P79)18世紀之前的新教改革發揮了同樣的啟蒙作用,黑格爾認為改革后的新教已經把有限與無限分開來對待,不再是中世紀那種樸素的主觀信仰。在《耶穌傳》中,黑格爾借耶穌之口這樣表達他對啟蒙與宗教的看法:“當他進一步反復思考了在這樣一些條件下所僅能獲得的一切后果時,即使人們占有這些東西其用意只在于用來達到人類的福利,其后果也不外降低自己的品格使屈從于自己的和異己的情欲,忘記了自己較高的尊嚴、棄絕了自我的尊重。”[5](P150)這說明了黑格爾對啟蒙之后世界的基本認識是,追求自由的行動很容易滑向滿足欲望的泥潭,在這一過程之中放棄永恒倫理法則也是有極大風險的。因此,黑格爾認為,啟蒙不是人類的終極目標,人類的終極目標在于對理性自由地把握、擁有理性自身。黑格爾啟蒙觀的核心是:“啟蒙既不是理性的結果,也不是理性的目的,相反,啟蒙只不過是理性自身展開過程的人類特定意識和現實歷史的有限階段。”[3](P71)也就是說,啟蒙事實上只是一個具有工具價值的歷史概念,它的主要作用要通過有用性這一特點得以呈現。
二、對信仰的否定及其分裂
在與信仰的斗爭中,啟蒙通過傳播“純粹識見”而悄無聲息地占領了天真意識(信仰)的寶座。黑格爾在審視這一過程中發現了一個隱微的秘密,亦即,識見在面對信仰時,首先把它當做純粹識見,并且由于對自己本身不認識,就把這對象宣布為謬誤。啟蒙對傳統宗教信仰的批判起點是有問題的,因為作為“天真意識”的宗教信仰本身就不可能是理性的對象。啟蒙的目的在于推倒宗教信仰的統治地位,具有極強的功利主義傾向。黑格爾對啟蒙的精神哲學分析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的批判之中。
首先,黑格爾認為啟蒙雖然宣稱自己的純粹性,卻在實際中體現出對精神的褻瀆。他說:“啟蒙,自稱是純粹性的東西,在這里把精神所認為的永恒生命(永生)和神圣精神(圣靈)都當成一種現實的、無常的事物,并以屬于感性確定性的一種本身毫無價值的看法加以玷污。”[4](P91)啟蒙極力掩蓋的是信仰作為一種天真意識本身所具有的純粹性,這種思維活動將個人與神直接聯系在一起,從某種意義上說,實現了人格的崇高,只不過這種崇高是以消融自我主體性為代價的。其次,黑格爾認為啟蒙對信仰批判的現實起點是認為教會的腐敗體現了信仰的物質功利性,而事實上,啟蒙卻絲毫不掩飾自己在物質占有、物質享受方面的欲望。啟蒙認為:“舍棄享受和犧牲財產是既不公正又不合目的的。”[4](P103)這說明啟蒙對宗教在物質方面的批判是虛偽的,所以黑格爾一針見血地指出:“啟蒙認為,拋棄一筆財產以便自己感覺到并向別人顯示出自己一概擺脫了財產,戒絕一種享受以便讓自己感覺到并向別人表現出自己一概超脫了享受,這乃是笨拙的、不合目的的做法。”[4](P103)結合宗教改革之后的具體歷史背景,我們也可以看出,黑格爾對待物質功利主義的警惕態度與清教節制、簡樸的人生觀不謀而合。
需要指出的是,黑格爾所說的“功利主義”與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們所倡導的“功利”是有巨大的不同的,但啟蒙對理性價值的高揚卻與經濟學中“理性經濟人”的設定極其相似。斯密的《道德情操論》早于《國富論》多年發表,通過這種倫理與經濟并重的案例可以窺見歐洲啟蒙思想家對功利主義的態度是清晰的:作為工具理性的功利主義具有極高的效率,但同時也有其天然的缺陷,道德領域的“善”并不能通過功利主義達到。在《精神現象學》中,黑格爾同樣對功利主義的人生觀提出質疑。他認為,啟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人的功利追求,并通過理性的力量“祛魅”以實現世界萬有的高度對象化。物質的利益性成為解釋和評價的基礎,價值體系下降為以人類欲望的滿足與否為標準。當然,在這一過程之中,傳統信仰必然坍塌,因為這種“天真意識”往往不能在現世兌現人的功利訴求。然而,對物質的追求和功利的人生態度卻有可能產生新的信仰,而且還是可怕的拜物教!
在功利世界中,有用性就是真理性,而真理性同樣也是自身確定性。[4](P103-104)這就是說,在啟蒙之中“有用性”是衡量價值的尺度,事物的真理性通過現實功利的實現得以彰顯。所以,可以看出啟蒙的倫理觀天然蘊含著一種功利主義的道德。善的實現并不依賴人的良心的宰制,而是成為一種外在的規定,善惡的評價標準就是依照功利的目的是否實現來判定。黑格爾對這樣的人生觀表示憂慮,他認為,啟蒙所高揚的理性價值在追求功利的過程中被拋棄了,這樣,理性啟蒙就走向了他自身的反面而產生了對理性的背離。黑格爾說:“歡樂過度就對它的本性有損,或者更確切地說,他的個別性本身也包含著它的彼岸。”[4](P113)在這里,辯證法大師黑格爾給我們指出了理性啟蒙自身可能出現的背反,他認為理性是一種有用的工具,可以適度地約束它而實現啟蒙的歷史使命。
約束理性的力量是意識。在黑格爾看來,啟蒙主張的有用概念雖然有滑向功利主義的隱憂,同時也在另一方面強調了人的主體地位。在功利主義的評判中,人的意識才是最終的法官,對人的價值的高揚彰顯了人文情懷,也肯定了人對功利追求的正當性。有用的內涵是指一切東西的存在都要被他物所利用,成為他物的存在,最終才能使他物為己所用。人的獨特性就在于,人能意識到“有用”的這種本質。從這個意義上講,人作為自然的存在,這種自在的存在方式對他者而言是可以利用的。同時,人能夠意識到自身存在的絕對性,即是說,人可以使他者呈現出有利于自己的屬性,別的一切東西都可以為他的歡愉而存在。黑格爾這樣描述人的獨特高貴:“而他就像剛從上帝手中制造出來的天之驕子,逍遙于世界之上如同游逛于一座專門為他而培植的花園里一樣。”[4](P97)啟蒙的重要價值在于,高揚人的主體價值,使得原先要通過神的恩典才能彰顯的高貴復歸于人間。但是通過啟蒙的觀點看待這個世界,一切存在者的意義只能通過有用性來體現,這難免會造成價值觀的庸俗化、物質化,也極容易滑向利己主義和享樂主義,所以黑格爾要強調意識的調節作用。
在理性的主體性原則得以確立的啟蒙語境之下,高踞于理性和知識之上的宗教就成為啟蒙必然顛覆的對象。純粹識見之所以是“純粹”的,原因就在于它不以財富和權利作為對象,而是以自身作為對象。這種思想表明黑格爾意識到,宗教信仰坍塌之后的世界必然要面對意識與世界分化的問題。他希望在純粹識見里去尋找自我同一性,或者說,希望通過哲學的方式謀求形而上學與現實世界的同一。啟蒙所確立起來的理性原則事實上只是精神通往終極倫理實體的一個環節,這個理性并不具有終極意義,而事實上理性只是一種知性,是一種不整全的思想。黑格爾認為:“純粹識見的概念認為自己是不同于它自己對象的一種別的東西 (他物),因為正是這個否定性規定, 構成著對象。”[4](P97)這說明,純粹識見是一種先驗的主觀意識和反思的主觀意識的綜合,認識只有到達純粹識見的高度才具有真理性。
要言之,以“有用性”為基本概念的啟蒙思想,其本質在于建立起對理性原則的信仰。這種信仰與啟蒙之前以上帝為信仰對象的宗教信仰從本質上來講并無二致。但是啟蒙的真理性在于,啟蒙本身是通往主體意識與客觀世界同一的必由之路,啟蒙是精神發展的一個必要的環節。啟蒙的使命是從“混沌”的世界中分化出清晰的對象來,這種對象化從某種程度來講是一種物質化。與此同時,對象化的世界意味著分裂。黑格爾用拉摩的侄兒作為這種分裂狀態的典型,在他的語境中,“明智和愚蠢的一種狂誕的混雜,是既高雅又庸俗、既有正確思想又有錯誤觀點、既是完全情感錯亂和丑惡猥褻,而有時極其光明磊落和真誠坦率的一種混合物”[4](P67)。或許這種比喻過于文學化而略顯荒誕,不過這種形象的描述還是給我們清晰地揭示了啟蒙及啟蒙自身的復雜性、過渡性特征。
三、由分裂走向同一
在與信仰的斗爭中,識見通過使用理性的力量贏得了勝利。在黑格爾看來,這一結果是由于啟蒙對信仰環節的歪曲,但這些顛倒和歪曲卻具有正當性。究其原因,是因為啟蒙是為了實現“人世的權利”和“人的自由”。啟蒙本身也意味著行為主體的自由,所以在對信仰的批判中總是贏得勝利。也正是因為如此,啟蒙與信仰一樣都具有某種話語的霸權,但是卻不能避免啟蒙自身帶來的分裂。這種分裂的局面意味著理性啟蒙還處于一個未完成的階段,如何將分裂的意識世界和物質世界同一,是啟蒙必須要解決的重大理論危機。
黑格爾敏銳地發現各種理論從本質上來講并沒有不同,從意識對象的角度來看,它們都是以“純粹識見”為內容的空談,而忽視了現實世界的維度。黑格爾認為這些概念都沒有達到笛卡爾形而上學的高度,不是一種“純粹的抽象”。笛卡爾通過預設上帝存在作為保證思維世界與自然秩序和諧一致的保證,而啟蒙則是通過“有用性”概念將思維與存在、主體與客體聯系在一起。這種“有用性”的價值標準又建立在人的功利觀之上,世界不再是自在的,而是為我的。雖然人的價值得到高揚,但是這種形而上學把人的主觀意識、精神拔高到宇宙中心的位置也是隱含著人類中心主義風險的。在這樣的理論前提之下,任何其他存在者,包括人自身都有可能成為滿足目的的手段。
有學者認為,黑格爾哲學中的啟蒙教化是一種去自然化,它使人“人為地”成為經濟人或公民。[6](P51)誠哉斯言,黑格爾從未將啟蒙當做一種終極性概念予以對待,而是將啟蒙視為倫理世界之中的一段歷程。他認為啟蒙是近代市民階級反抗傳統教會、爭取現實功利人生和表達自由愿望的歷史階段,因此,啟蒙之中的主體——人,并不是大寫的類人,而是具體的、有著現實歷史背景、由近代第三等級發展而來的市民階層。將黑格爾的思想重新拉回歷史現實,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他的啟蒙觀具有濃厚的反抗強權、爭取自由的印記。18世紀的歐洲大陸涌動著抗爭的熱潮,反對宗教壓迫、爭取功利人生、爭取自由權利的思潮最終匯集成巨大的歷史洪流。法國大革命滌蕩著中世紀神權統治的沉渣,卻又以“紅色恐怖”的方式宣布啟蒙歷史的終結,啟蒙在理性的辯證運動中走向精神的新高度。
啟蒙雖然在歷史中被揚棄,然而“有用性”對黑格爾來講依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它是純粹識見的實現,并且有用性概念的提出取代了信仰對象空洞性、彼岸性的特點。合理地使用“有用性”的概念是人平等相處并最終建立共同體的重要基礎,因而自有其合理性。在教化世界之中,人們通過合理節制個人自然欲望以求得自身“有用性”的實現,并在這一條件下實現個人目的。黑格爾適度的功利觀所要達到的目的與盧梭是接近的,在盧梭看來,每個人讓渡出他的全部自然權利以換取公民地位。權利讓渡的目的也是為了解決具有自由意志的個體如何與共同體在一起的問題。個體作為公民體現了自我承認與他人承認的統一,公民身份同時也意味著個人與他者的相互承認。這種相互承擔義務、相互尊重獨立的公民身份體制本身就是一種在“有用性”原則之下建立的,這表明,工具性本身意味著合法性,啟蒙所提倡的功利原則是社會秩序、政治制度產生的原初性概念。
但是,黑格爾認為這種因“有用性”而具有的真理性是片面的。黑格爾與盧梭要達到的目的是相似的,但在國家起源論上,他堅決否定盧梭的契約論:“他(盧梭——筆者注)所理解的意志,僅僅是特定形式的單個人意志,他所理解的普遍意志也不是意志中絕對合乎理性的東西,而只是共同的東西,即作為自覺意志的這種單個人意志中產生出來的。……為了反對單個人意志的原則,我們必須記住這一基本概念,即客觀意志是在它概念中的自在的理性東西,不論它是否被單個人所承認或為其偏好所希求。”[7](P255)黑格爾認為,盧梭錯誤地通過契約論將倫理實體與市民社會直接等同,契約論隱含著原子論的風險必須以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古典共同體主義予以糾正。也就是提倡整體大于并優于部分,個體應當在國家中獲得真正的自由。[8](P41)
由是觀之,黑格爾對“有用性”概念的使用是極其慎重的。在他看來,要面對分裂世界的重重矛盾還要將“有用”和“有用性”概念區別開來。他說:“有用仍然是對象的一個賓詞,還不是主體自身,換句話說,還不是主體的直接和唯一的現實。”[4](P114)“有用” 作為功利主義的特征,過度的強調隱含有被物質主義奴役的危險,這也是在18世紀的歐洲社會最為嚴峻的歷史問題之一。強調“有用性”,即是在強調主體的價值和作用,這種“有用性”是人的理性通過辯證發展之后能夠以純粹識見關照世界產生的體驗。黑格爾說道:“功利,在信仰看來,或者在情感看來,或在那專為自己制造自在存在而稱自己為思辨的抽象看來,盡管是那么的丑惡……在這里,純粹識見不復否認它的對象,而且也不認為它的對象只具有空洞無物或純粹彼岸的價值。”[4](P110-111)他的意思是,純粹識見作為存在著的概念自身,其實質就是一種簡單的純粹的自我意識,有用性是純粹識見的一種表達,這種自我意識自在自為地存在于一種直接的同一性之中。在啟蒙教化之后的世界看來,純粹識見包含著對自身的反思,還很難達到普遍本質的高度,還不是真正自為的普遍概念;在信仰世界之中,信仰是唯一具有完滿內容的天真意識,但這個純粹識見無法反思自身的現實確定性而只能淹沒在一個普遍本質的世界之中。純粹識見在信仰世界之中所缺少的現實確定性只能通過功利世界的“有用性”得以彌補,“因為它在功利中達到了肯定的對象性;純粹識見因此就是一種現實的、在自身中滿足了的意識”[4](P113)。由此可見,黑格爾提出“有用性”概念的目的就是彌補純粹識見的現實確定性不足,將教化世界和信仰世界在自我意識中求得同一,亦即實現功利世界。
可以說,“有用性”概念是黑格爾讓分裂的世界走向同一的橋梁。在對這一概念的批判中,黑格爾試圖解決啟蒙之后人類生活分裂、多種新秩序之間紛爭不斷的局面。他認為,在功利世界里,有用性成為純粹識見的確定性內容,真理具有自身確定性。信仰世界中缺失的真理性內容在理性的作用下得到補足,于是自我意識“在這樣一種關系中直接具有對它自己的普遍確定性、對它自己的純粹意識,在這種關系中,真理性以及現在和現實性是結合起來了的。兩個世界達到和解,天地相互交接,天國降入人世”[4](P113-114)。黑格爾的樂觀是有道理的:法國大革命雖然產生了“紅色恐怖”,但由于人類對和諧秩序的天然肯認,理性很快重新奪回統治。這種大革命,或者說這種思想的啟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混亂,但是卻在另一個新的高度為人類社會的重新統一鋪平了道路。在黑格爾看來,啟蒙是人類歷史的必然,這是歷史精神自身的辯證發展軌跡所決定的。不論人類是否愿意,啟蒙都會隨著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啟蒙客觀地改變著人類的精神世界,塑造著社會的面貌。但啟蒙的“有用性”和缺陷不能被超越和克服,由于啟蒙自身具有功利傾向,這種否定性力量將使其自身不可挽回地消失在人類歷史長河的奔流之中。因此,唯有以審慎的態度對待啟蒙,才能更好地面對人類的現實與未來。
[1]趙素錦,趙素欣.黑格爾啟蒙觀的精神哲學解讀——以《精神現象學》為學術資源[J].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0,(3).
[2]楊國榮.以現代精神為鰥夫——從德國宗教改革運動看宗教現代性與現代倫理問題 (上)[J].道德與文明,2010,(5).
[3]張政文.康德黑格爾啟蒙觀的差異與文化批判[J].哲學研究,2005,(12).
[4](德)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下卷)[M].賀麟,王玖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5](德)黑格爾.黑格爾早期著作集上[M].賀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6]張汝倫.黑格爾與啟蒙——紀念《精神現象學》發表200周年[J].哲學研究,2007,(8).
[7](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M].范揚,張企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8]陳良斌.啟蒙現代性敘事與黑格爾的承認哲學[J].江西社會科學,2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