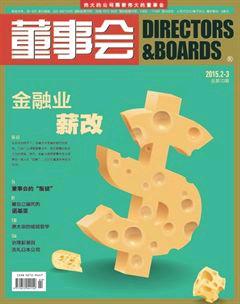我國金融體系為什么不足以支持創新?
創新,是決定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升級能否成功的關鍵所在。這一點,社會各界有著高度的共識,但對創新受阻、創新不足的個中緣由,卻有著不同的解釋。從資金的角度來看,金融體系的發展滯后于經濟增長和社會轉型,是一個不能忽視的重要原因。
盡管政府多年來一直號召銀行要創新金融產品,為新興企業、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融資便利,但銀行自身的風險管控要求和盈利模式限制了中小企業間接融資的規模。無論銀行如何變換花樣,創新出怎樣的金融產品,這些產品的背后都是需要有信用抵押的。這一特點決定了銀行不可能獨自成為支持創新的主力,即使是在利率完全市場化的國家,銀行也不是新興企業的主導性融資來源。
按照經濟學原理,解決這一問題的出路有兩條:一是公共補償,因為創新活動具有正向外部性,市場機制本身是無法補償創新者的投入和所面臨的風險的,所以必須要依靠公共部門,通過提供公共資金補助、成立創新支持基金或定向創新企業的信用擔保平臺等方式,解決資金來源不足、創新激勵不足的矛盾;二是建立多層次的金融體系,主要是建立與創新型企業的資產特點、風險結構和成長性相匹配的資本市場,用市場機制引導風險偏好型資本流向創新型企業。
公共補償的最大難題是信息甄別。在不計其數的創新活動中,到底什么是“有前途”的創新方向呢?哪些是外部性最大的創新活動呢?如果私人投資部門都無法回答這些問題,又怎能指望政府官員的“行政頭腦”呢? 何況在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行政體制下,公共決策往往取決于決策者的偏好而不是市場需求,很多投資項目都是“政企合謀”的結果。全國各地大量出現空置的科技園、創業園,一些產業投資扎堆過剩,而真正要進行技術創新和升級的中小企業卻得不到資金支持,都是因為補償決策機制出了問題。
此外,我國還沒有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創業板市場。由于行政色彩濃厚,上市制度和交易制度的不完善,目前我國的創業板和新三板市場對新興企業的融資支持非常有限,與美國納斯達克股票交易市場的差距很大。與此相關,天使資金、私募資金在本土市場的積累和沉淀也受到極大影響,從而拖累了整個社會創新資本的有效、持續供給。
金融體系對創新能提供多大支持,說到底還是要落實到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上。政府要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在制度、法律的建設和完善以及審慎的政策支持上,而其余的事情皆應交給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