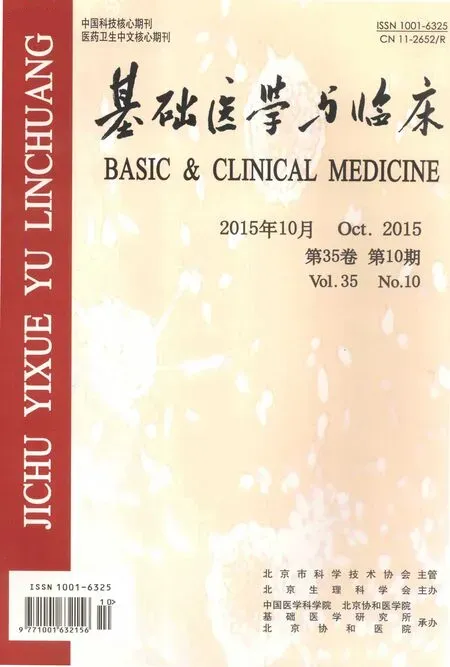淺談美國醫學教育的臨床教學反饋
丑 賽,趙 峻,楊 萍
(中國醫學科學院 北京協和醫學院1.臨床醫學專業;2.臨床學院 教育處;3.教務處,北京100730)
2014年8月在北京協和醫學院短期出國交流計劃的支持下,筆者有幸以訪問學生的身份對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教學醫院灣區醫學中心(Harbor-UCLA Medical Center,HUMC)進行為期4周的訪問學習。作為洛杉磯灣區最大的教學醫院,這里承擔了醫學生實習,住院醫師和專科醫師培訓的任務,整個加州大學系統內的醫學院均可申請到這里接受培訓。作為教學醫院,HUMC 非常重視教學,教學活動不僅內容豐富、形式多樣,而且非常具有針對性和計劃性,幾乎每個專科都有常規性、面向非本專科從業人員的教學活動和針對不同階段教學對象的系列課程。本文將從HUMC 參觀過程中經歷的教學實例出發,探討教學反饋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特質、效果及其帶來的思考。
筆者訪問期間,主要跟隨HUMC 心內科會診團隊學習。在心內科的會診名單上有1名妊娠32 周的重度二尖瓣狹窄患者,因急性左心衰竭等妊娠并發癥收入婦產科病房,請心內科協助診治。HUMC的心內科會診團隊由1名主治醫師、1名專科醫師和2名低年資住院醫師組成,一般認為主治醫師為小團隊教學中的主要引導者。在住院醫師簡要匯報完病歷后,主治醫師首先提問住院醫師:“對于心臟瓣膜疾病患者如何決定是否能夠妊娠?何時應該終止妊娠?”當住院醫師正確說出瓣膜病患者妊娠相關禁忌證后,主治醫師繼續提問,“如何評估此類患者的預后呢?”剛輪轉到心內科的低年資住院醫師如實回答,“對不起,我不知道”。主治醫順勢請該名住院醫師查閱相關文獻,并提出了新的問題,根據該名患者目前的狀況,在查體時可能會有哪些陽性發現?針對兩名住院醫師給出的不同答案,主治醫師并沒有做出直接評價,而是分享了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基于臨床情況的瞬息萬變,這一問題本身并無標準答案。而在討論的最后,主治醫生提出了新的問題,“對于這樣一個有著明確終止妊娠指征卻仍舊堅持妊娠的患者,應該如何去管理和交流呢?”
這是一個典型的基于問題的教學(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1],其核心問題是嚴重心臟瓣膜疾病患者妊娠的臨床管理。從教學中教學反饋的方法上來看,學者傾向于把教學反饋分為集中式形成性教學反饋和開放式形成性教學反饋[2]。前者源于教師試圖判斷學生是否已經知道、理解或預習過相應的知識,而后者側重于發現學生知道什么、理解什么和可以做什么。最初的兩個問題具有集中式形成性教學反饋的特征,主治醫師試圖判斷住院醫師對相關知識的掌握,并以此決定本次教學的內容、方向和難度。而接下來的問題則為開放式形成性教學反饋,側重于發現住院醫師潛在的知識薄弱點。因為住院醫師現階段完全有能力自學、掌握相關內容并深入探討。隨著不同層次教學的展開,主治醫師借助其知識儲備的優勢,選擇性探討部分問題,而對另一些問題則采取了留白。一方面幫助住院醫師構建知識框架[1],另一方面根據心理學的蔡格尼克效應加深住院醫師對知識的記憶并調動其主觀能動性[3]。而從教學反饋發生的主體來看,PBL教學反饋特點主要是真實性和雙向性[4]。從教學內容上來看,包括疾病本身的臨床表現、診斷、預后和治療,也包括醫學的“人本”主義核心[1],對倫理學和社會學方面的問題給予學生更多的思考。
通過這一案例,不難體會臨床教學反饋中明確性、及時性、真實性、針對性、雙向性和多樣性的特征[4],亦可以從HUMC的教學實例中得到諸多啟發。
首先,就臨床具體病例討論的引導來說,教學結構更偏向以疾病為起點,以串聯的形式整合疾病發生發展規律的知識點。而反觀國內許多臨床教學活動仍以單個知識點出發,多停留在知識點灌輸、反復強化知識框架本身。產生這種現狀的原因既有教師對教學反饋理解的差異,也有國內學生主觀能動性較差的原因。
其次,教師對于學生的反饋方式來說,HUMC的教師對學生的答案并沒有明確的預期,也很少有“正確”、“錯誤”、“應該”等明顯帶有預估色彩的評判詞語,答案言之成理即可。教師評估學生反饋的方式及積極性,并以此指導教學[5]。國內的PBL 盡管也采取開放的形式進行學習討論,但以教師為中心的考核色彩仍然較重,后者的反饋常常起到“督查”而非“啟發”作用。
第三,學生對于教學反饋的認識上,HUMC的住院醫師對擔任教師角色的主治醫師所給予的反饋更多采取開放的態度。因此,學生愿意接受教師正面或負面的反饋。而國內的學生仍然處于需要被認同的焦慮中,當無法得到教師的肯定時,容易陷入焦慮和自我懷疑的情緒中。馬斯洛理論的最高層次為自我實現,而認同行為本身能極大滿足人們的這一需求[1]。但長期需要通過認同才能維持學習動力的方式并不適合強調終身教育的臨床醫學。醫療發展日新月異,自我鞭策才是保持知識更新的恰當途徑。學生的這種心理模式也與長久以來應試教育的教學模式及國內考核評估體系的影響密不可分,學生常常因過分追求所謂的“正確答案”而忽略了學習過程本身。
最后,恥感文化與罪感文化在教學反饋中的作用。一般認為恥感文化在東方文化中較為突出,而西方文化中以宗教色彩的罪感文化較為明顯。后者并非完全不存在恥感文化,只是其最終也需借助于罪感發揮作用。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七原罪都不涉及“羞恥感”。在HUMC的教學案例中也可以看到這樣的文化特點。一方面,主觀能動性發揮主導作用意味著更好地調控自己的行為;另一方面,自我中心的結果是外界很難對其行為進行干預和影響。而國內因為恥感文化的存在,教學的負反饋會引起一定的自我懷疑和對自我評價的修正。這種心理在激勵學生完善自己的知識結構的同時,也會引起一定的焦慮,從而影響其在教學活動中的表現[1]。因而,文化背景也會影響學生在教學活動中的表現和目標規劃,最終影響教學目標。
總結此次HUMC 之行給筆者帶來的思考,首先教學反饋作為教學觀念的外在化表現形式,其本身反映了教學團隊對教學行為的理解和定位。其次,合適的反饋方式選取可使教學效果事半功倍。譬如在培訓初期框架性理論知識和特征性知識點的補充,無疑對低年資住院醫師是必需的。與之對應的是在專科醫師的培養中,溫習疾病的發展、預后,更新診療相關的理念及知識將對工作大有裨益[1]。因此,根據不同醫學培養階段、不同教學場景等情況,應隨機應變的采取不同策略。最后,教學觀念可以更新,教學理論可以發展,但對于有著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學對象,其自身特點所帶來特殊性則是相對固定。比如,亞裔文化中的壓抑、儒家關于“知恥”理論等潛移默化的影響,使得這種文化下學生學習的主觀能動性較弱,但對知識的識記能力較強。這些基于文化的特質與其強行改變,不如通過教學反饋等方法學上的調整以適應其特點,做到真正的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
因此,在臨床教學中應結合教學內容、學生素質等綜合考慮,采取靈活的教學反饋形式,以達到臨床教學目標,更好地利用現有資源培養高素質醫學人才。
[1]Dornan T,Mann KV,Spencer JA,et al.Medical education:Theory and practice[M].London:Elsevier Health Sciences,2010:211-229,229-257,317-339.
[2]張躍,王晶瑩.國外關于課堂教學形成性評價的研究[J].中小學教師培訓,2011,4:61-64.
[3]籍莉.蔡格尼克效應與課堂教學中的留白[J].基礎教育,2008,3:58-61.
[4]吳喜蓮.教學反饋:內含、特性與策略[J],讀與寫,2010,8:28-29.
[5]許華瓊,胡中鋒.形成性評價及其反饋策略[J].教育測量與評價:理論版.2010,1:23-26.
[6]王鋒.恥感:個體自律的道德心理機制[J].天津社會科學,2010,1:3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