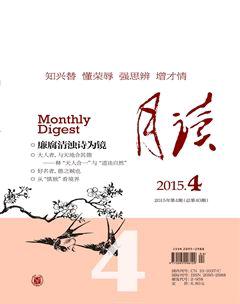晚明的歷史大變局
樊樹志
歷史的大變局并非僅限于晚清,晚明也以不同的形式出現過。突然提出晚明的歷史大變局,并非故意聳人聽聞,而是希望人們放寬歷史的視野,回過頭去看一看16世紀下半葉至17世紀中葉的中國曾經發生的巨變。
“全球化”初露端倪的時代
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世界歷史出現了大變局,歷史學家稱為地理大發現時代或大航海時代。歐洲的航海家發現了繞過非洲好望角通往印度和中國的新航路,以及美洲新大陸,標志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西方歷史學家把這一標志作為中世紀與近代劃分的里程碑,并非毫無道理。這一轉折,最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全球化”的初露端倪。從此,人們的活動不再局限于某一個洲,而是全球各大洲,包括新發現的美洲。人們的視野與活動所及,不再是半個地球,而是整個地球,因此稱之為一個“全球化”初露端倪的時代,是毫不為過的。
在一般人心目中,“全球化”似乎是20世紀末、21世紀初才出現的新事物,其實不然。美國學者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與約瑟夫·奈(Joseph S.
Nye)在他們的論著《全球化:來龍去脈》中,對“全球性因素”與“全球化”的界定是具有歷史縱深感的:“全球性因素是指世界處于洲際層次上的相互依存的網絡狀態。這種聯系是通過資本、商品、信息、觀念、人員、軍隊,以及與生態環境相關的物質的流動及其產生影響而實現的”;“我們認為,全球性因素是一種古已有之的現象。而全球化,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指全球因素增加的過程”。有的學者傾向于認為:“全球化”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5世紀末開始的地理大發現時代,此后世界市場從歐洲拓展到美洲、亞洲和非洲,世界各大洲之間的經濟聯系大大加強,國際貿易迅速增加,世界市場雛形初具,“全球化”初露端倪。
倘若以為這是初出茅廬者的一家之言,那么不妨看一看權威的見解。當代著名學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的一大貢獻就在于,它以一種歷史的深邃感闡述了“世界體系”的起源,即16世紀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開始以西北歐為中心,形成“世界性經濟體系”,它是嶄新的“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社會體系”。年鑒派大師布羅代爾在其巨著《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的第三卷中,闡述了“世界經濟”與“經濟世界”的形成過程,他認為,“世界經濟”延伸到全球,形成“全世界市場”,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它的轉折點就是15世紀末的地理大發現,“由于15世紀末的地理大發現,歐洲一鼓作氣地(或幾乎如此)挪動了自己的疆界,從而創造了奇跡”。
美國學者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震動國際學術界的著作《白銀資本》,其副標題就叫作《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而他所討論的時間段,恰恰是1500年至1800年。他認定,從地理大發現到工業革命之前的時代,已經是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如果問題到此為止,那么還不至于引起眾說紛紜的爭論。弗蘭克的創造性在于,突破歐洲中心論的窠臼,明白無誤地指出,1500年至1800年,“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是世界經濟的中心,換言之,當時的經濟中心不在歐洲,而在亞洲特別是中國。
晚明中國:貿易順差與巨額白銀資本的流入
在這個“全球化”初露端倪的時代,中國當然不可能置身
事外。
葡萄牙人繞過非洲好望角進入印度洋,占領印度西海岸的貿易重鎮果阿、東西洋交通咽喉馬六甲,以及香料群島以后,從1524年起,在中國東南沿海進行走私貿易。當葡萄牙人獲得澳門貿易的許可以后,澳門開始成為溝通東西方經濟的重要商埠,成為晚明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渠道,也是晚明中國在大航海時代與全球經濟發生關系的中介。它的意義,不僅對于葡萄牙,而且對于中國,都是不可低估的。澳門從16世紀80年代進入了黃金時代,一躍而為葡萄牙與印度、中國、日本貿易航線的重要樞紐港口。以澳門為中心的幾條國際貿易航線第一次把中國商品運向全球各地。澳門的轉口貿易,把中國卷入全球貿易網絡之中,使中國經濟首次面對全球(東半球與西半球)經濟的新格局。
晚明歷史大變局的帷幕慢慢揭開。
西班牙人的東來,大大拓展了這種歷史大變局的深度與廣度。西班牙人到達美洲以后,繞過美洲南端,進入太平洋,來到菲律賓群島。1580年以后,西班牙的馬尼拉當局,為生絲、絲織品、棉布、瓷器等中國商品,找到了一條通向墨西哥的航路——太平洋海上絲綢之路。這迥然不同于以往的海上絲綢之路,它不再局限于東北亞或東南亞,而是越過大半個地球,由亞洲通向美洲的遠程貿易。“馬尼拉大帆船”(Manila Galleon)滿載中國商品,橫渡太平洋,前往墨西哥。這就是馳名于歷史的、持續了二百多年的溝通馬尼拉與阿卡普爾科的大帆船貿易。馬尼拉大帆船運去的中國商品,特別是生絲與絲織品,在墨西哥、秘魯、巴拿馬、智利都成了搶手貨,并且直接導致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以本地蠶絲為原料的絲織業的衰落。
“馬尼拉大帆船”的貨源來自福建沿海的自由貿易港——月港(以后升格為海澄縣),由于它的繁榮,一直有“小蘇杭”的美譽。隨著貿易的發展,福建商人逐漸移居馬尼拉,專門從事貿易中介業以及其他工商業。因此史家評論說,馬尼拉不過是中國與美洲之間海上絲綢之路的中轉站,“馬尼拉大帆船”嚴格說來是運輸中國貨的大帆船。
稍后來到遠東的荷蘭人,為了和葡萄牙、西班牙展開商業競爭,1602年建立了統一的“聯合東印度公司”,這就是在遠東顯赫一時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它把總部建在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而把目光盯住東南亞、日本和中國。16世紀末至17世紀中,東方的商業大權幾乎為荷蘭人所獨占,他們以馬來半島、爪哇、香料群島為基地,向中國和日本發展,臺灣很快成為進口中國商品的固定貿易中轉地。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新興的歐洲強國,在與中國的貿易中,無一例外地都處于貿易逆差之中,而中國始終處于貿易順差之中。由于這種貿易以中國的絲綢為主角,因此被西方學者概括為“絲— 銀”對流。以葡萄牙而言,它從澳門運往果阿、里斯本的中國商品有生絲、絲織品、黃金、水銀、麝香、朱砂、茯苓、瓷器等,其中數量最大的是生絲;而它從里斯本、果阿運回澳門的商品有白銀、胡椒、蘇木、檀香等,其中數量最大的是白銀。這些白銀是墨西哥、秘魯生產的,由葡萄牙、西班牙商人運往塞維利亞、里斯本,再運往果阿。以至于當時的馬德里商人說,葡萄牙人從里斯本運往果阿的白銀幾乎全部經由澳門進入了中國。
這種結構性貿易逆差,所反映的決不僅僅是技術層面的貿易問題,而是貿易各方生產水平、經濟實力的體現。葡、西兩國及其殖民地無法用香料等初級產品與中國工藝精良的高級商品在貿易上達成平衡,必須支付巨額白銀貨幣。關于這一點,弗蘭克《白銀資本》說得最為深刻:“外國人,包括歐洲人,為了與中國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國人支付白銀,這也確實表現為商業上的‘納貢”;“‘中國貿易造成的經濟和金融后果是,中國憑借著在絲綢、瓷器等方面無與匹敵的制造業和出口,與任何國家進行貿易都是順差”。他進一步發揮道:“16世紀的葡萄牙、17世紀的尼德蘭(荷蘭)或18世紀的英國在世界經濟中根本沒有霸權可言”;“在1800年以前,歐洲肯定不是世界經濟的中心”。
弗蘭克的這種大膽論斷,引起了外國學者和中國學者的異議。作為一個學術問題,當然可以繼續討論。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它在某種程度上顯示了晚明歷史大變局的存在,以及中國在其中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這種情況是和晚清歷史大變局截然不同的。
不論你對此作何評價,巨額白銀資本的流入中國總是一個不容置疑的歷史事實。中國學者全漢升從大量第一手資料中提煉出結論:1571年至1821年間,從美洲運往馬尼拉的白銀共計4億西元(比索),其中二分之一或更多一些,流入了中國。全氏的這一研究成果受到西方學者的廣泛關注。
有鑒于此,弗蘭克對巨額白銀資本流入中國問題做了一個系統總結,他在《白銀資本》中認為中國通過“絲— 銀”貿易獲得了世界白銀產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相比較而言,弗蘭克的估計比全漢升保守多了,即便如此,也足夠令人震驚了。
這無論如何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輝煌!這種輝煌出現在晚明時期,它以無可爭議的姿態顯示,以往的所謂定論—— 晚明時期中國經濟已經走上了下坡路,是多么不堪一擊。
由于中國出口的商品如生絲、絲織品、棉布、瓷器等,主要來自太湖流域,以及東南沿海地區,巨額白銀資本的流入,毫無疑問刺激了這些地區經濟的蓬勃發展,市場機制的日益完備。全漢升不無感慨地說:“由此可知,在近代西方工業化成功以前,中國工業的發展,就其使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強大的競爭力來說,顯然曾經有過一頁光榮的歷史。”由此看來,在歐洲工業革命發生以前,中國江南的經濟水平是領先于歐洲的,至少并不比歐洲落后。
(選自《國史十六講》,中華書局。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明清史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