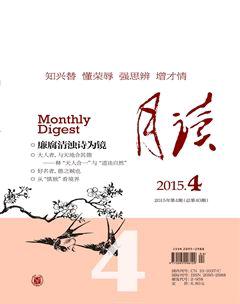從“慎獨”看境界
馬玉槐
慎獨在《大學》和《中庸》里都有論述,其主要含義有兩重:其一是說每個人都有其獨一無二的屬性,要尊重并珍惜自己和他人的這種獨特性。其二是說要謹慎地對待獨處,越是無人在側或無人監督之時,越要保持清醒和自重,這樣才能察覺到外在的風險和內心的偏斜,獨處時心猿意馬,自然談不上修齊治平。
獨處,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或許是一道永恒的考題,我們先拋開家國天下,也不談君子圣賢,僅就個人獨立意識的培養和進步來說,獨處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節點,因為它是一切品性是否成熟與穩定的試金石。
但獨處而不放縱并不容易做到,高唱自律未必能做到自律,更名八戒也不一定禁得住高老莊的美景入心。陪老僧入定,老僧入定了我們或許依舊心若飄風;隨真人辟谷,真人得道了我們可能仍在忍受饑腸轆轆。那么,怎樣才能做到慎獨呢?
想到過去曾聽人說要窮養兒富養女,為什么要這樣做呢?卻鮮有詳解,我在這里姑且妄斷一下這句老話傳于世的初衷。其所言之富養,大約首先是為了增長見識,超越茍圖小利的初級心理,不至于將來吃大虧甚至走歪路,若不明就里則可能養成貪慕虛榮,懶惰挑剔,凡事只能占先絕不吃虧的思維慣性,待蠻橫霸道、頤指氣使的品性養成之后,才悔不如當初窮養為好;而所謂的窮養,其本意則應該是為了培養堅忍擔當、大度寬容的品格,如不知所因,一味以洗腦和壓制為手段,以擊碎璞玉般的原生態自信和善良為目標,最后變成將欲望壓在心里,將貪婪寫進眼中,養成心性黯漠,仇視光鮮,以獨享為樂,以損人不利己為快的習性,到了如此地步是否又悔不當初?
可以想見,正直、善良、寬容、誠信等諸多品德并不是說說就能做到的,也不是單憑壓制和恐懼所能遏止的,指天發誓也未必會對所有人長期有效。
慎獨,就個體的養成而言,需要外在的長期培育和內在的不斷修養,而培育者只有知其然并能夠有知其所以然的通徹認識,以及耐心陪伴走過完整的自由意識成長過程的心態,才能慢慢成就出自由于內而中庸于外的慎獨意識。當然,這還需要培育者自身具有與時俱進的心態和不斷學習的精神才能長期擔當此任。
其實,慎獨之于群體的意義更大,因為正是由于每個人與眾不同的獨特性,才構成了群體內部豐富而深厚的多樣性,從而在群體結構上增強了內部的張力,使得整體由此變得堅韌而有彈性。如果把群體也比作一個人的話,秩序的確定性就像人的筋骨,而文化的多樣性則好比人的血脈,只有二者相輔,整體才會變得健康而充滿活力。儒家孜孜不倦倡導的為政者仁和為富者禮,就是要提倡最大限度地容納和保護這些個性化和多樣性,如此便可以讓秩序與和諧在同一個群體內并存和相互支撐。這就是中華民族傳統人本文化的精髓,就是中華文明延續至今的核心價值所在。
慎獨是儒家的一個基礎性概念,也是儒家一以貫之的精神倡導。可以說,在儒家的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這四科教育體系中,慎獨無處不在。
我們可以從儒家經典《論語·學而》說起:“當我們的所學經常能與所用相結合,當我們的朋友們從遠道而來的時候,我們的內心是否會感到由衷的快樂呢?當我們的才能和品行不為人所知的時候,我們會不會有所不快甚至是惱怒呢?”每個人的答案可能會有所不同,而這開篇就是在溫和地引導我們每一個人向自己的內心深處發問。在確立了個體的心路方向之后,就展開了儒家對社會結構穩定性的解讀:“下孝悌而上仁本”;再接下來便又是一輪對我們內心慎獨的精細化引導:“為人謀不忠乎?與朋友交不信乎?傳不習乎?”
由此可見,慎獨也許是一個會持續一生一世的發問,每個人的答案都可能不同,這是緣于每個人內心的境界不同,而每個人在不同的人生階段答案也會有所不同,即使同為忠信,其程度也難免會有所差異并處于變化之中。
儒家的先賢通過慎獨告訴我們:慎獨的關鍵就在于我們每個人內心的修煉,在于時時對自身心路歷程的觀照,而觀照的目的就在于讓我們的內心擁有不斷提高境界的意念。登高而見者遠,順勢而聞者彰。中華文明的三大主流根系儒釋道之所以能夠相容為一個整體,其內核的相通之處也許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