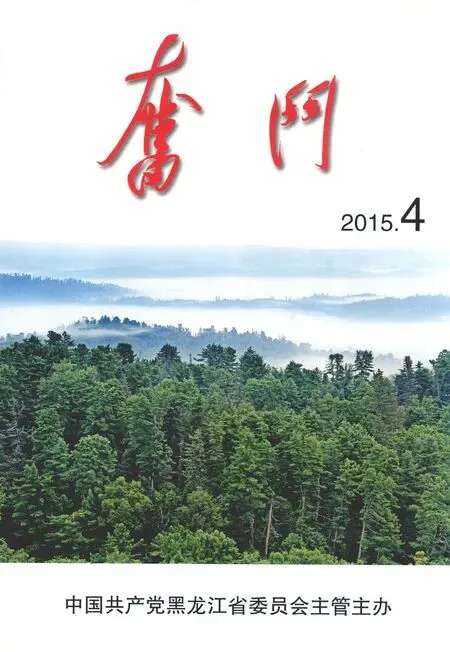昨天的歷史不能忘記
——訪哈爾濱抗戰文學作家雪墨同志
適 之
昨天的歷史不能忘記
——訪哈爾濱抗戰文學作家雪墨同志
適 之
在世界反法西斯和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即將到來前夕,我采訪了原哈爾濱市文化局局長王洪彬,也就是以創作哈爾濱抗戰文學而蜚聲中外的著名作家雪墨同志。
陽光透過飛揚的雪幕,從歐式的窗口流進來,斑斑駁駁地灑在哈爾濱市文管會的會議室,雪墨手捧一杯清茶,緩緩地向我講述他創作哈爾濱抗戰文學的歷程。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迄今,雪墨在工作之余特別是在離開工作崗位之后,潛心研究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哈爾濱抗戰的歷史,由此擴展到對于近代史以來中日關系問題的研究,開始了卷帙浩繁的以反映哈爾濱軍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長篇小說的創作。在不足十年的時間創作出版了《哈爾濱保衛戰》《大雪谷》《夢斷虎頭》和電視劇《荒原城堡》《帝國軍妓》,話劇《魂歸何處》,以及反映韓國民族英雄安重根刺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歌劇《安重根》,2009年又用兩個月的時間,創作了揭露日軍731部隊進行細菌戰罪惡的長篇小說《人性悲歌》等等。
他的這些作品一經問世,就受到廣大讀者的熱贊,并被翻譯成日、韓等多種語言文字,在日本、韓國和亞洲一些國家出版或上演,立刻引發了這些國家政府和民眾的關注,一時間出現了“雪墨作品熱”或“哈爾濱抗戰小說熱”。
雪墨面對這些卻是十分的冷靜。他說:“創作的這一系列反映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罪行的文學作品,是捍衛國家獨立,維護民族尊嚴,反思過去歷史的需要,其目的是為了警醒現在,呼喚世界的永久和平。”因為,他深知:一個只有不忘記昨天的國家和民族,才能對于今天和明天更有責任感。
雪墨首先介紹了什么是哈爾濱抗戰文學,他說:“哈爾濱抗戰文學的時間起于1931年‘九一八’事變,止于1945年‘八一五’光復。”
他的系列作品都是從這一個特定的時間段內開始,以哈爾濱為中心,展現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和中國東北特別是哈爾濱人民反侵略那些驚心動魄的故事,表現了中國東北特別是哈爾濱人民“團結起來,赴國難,破難關,奪回我河山”那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
他的第一部反映哈爾濱抗戰文學作品的長篇小說,就是創作于1985年的《哈爾濱保衛戰》。
他常常憑窗眺望夜色中和平、安靜的城市,思緒飛揚到已經凝固的歷史硝煙之中。此時,他的眼前出現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哈爾濱漫漫長夜的血雨腥風,他的耳畔間還仿佛回響著哈爾濱軍民抵抗日本侵略者進攻哈爾濱的隆隆炮聲,他仿佛看到東北軍和哈爾濱人民奮力抵抗日軍的壯烈畫面。
他全身心地投入寫作時,就會忘記饑餓和困倦,忘記一天的案牘勞形。他奮筆疾書,向世人展示了1931年哈爾濱軍民在“鞏我疆土,保我主權”的神圣旗幟下,戮力抗擊日本侵略者向哈爾濱進犯的戰斗場景。
他與歷史中的人物交流,達到息息相通的境地,從而在小說中塑造了眾多個性鮮明的人物,表現了李杜、馮占海、張作舟、趙毅等一批愛國將領的形象。還根據廣大人民群眾的英雄群體,塑造了極具典型性的眾多普通人物,有送子抗敵的老母親,有無數犧牲在保衛哈爾濱前線的士兵,還有以楊照理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人物形象,等等。這些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在國難當頭之際,表現了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價值取向的一致性。這是這些犧牲的人們,用自己的鮮血和年輕的生命鑄就了哈爾濱抗戰的精神世界。
這部第一次記載哈爾濱抗戰的長篇小說,經過半年多日夜的艱辛創作,于1990年出版后,即刻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
他從中得到了啟示,獲得了力量。之后,他又把目光聚焦在日本開拓團上。多次到日本開拓團比較集中的方正縣,實地考察,采訪了尚存的老百姓和日本遺孤,在掌握了豐富的第一手素材后,創作了名為《大雪谷》的長篇小說,全景式地反映日本開拓團在中國東北的罪行,以及他們背井離鄉的痛苦和面對戰爭的憂傷,歌頌了中國東北人民的無私和善良。
他在工作中也時刻關注與哈爾濱抗戰有關的歷史事實。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他作為哈爾濱市文化局長到虎林市走訪,并參觀了虎頭要塞。
那天,在晨光的映照下他站在五十多年前,蘇聯紅軍和日本關東軍決戰的舊戰場,清風習習,陽光熙熙。而他的腦海里卻是戰火硝煙、炮火嘶鳴、生死別離,卻是正義和邪惡的較量。
回到哈爾濱坐在辦公室里,而思緒仍在虎頭要塞、仍在與日本關東軍進行生與死的血肉決戰的畫面之中。利用工作之余,他再次走到虎頭、再次走到海拉爾,對于二戰終結地進行了全面的考察,做了大量的筆記,為了使作品更加的真實,利用一切時間在圖書館查找歷史資料。在此基礎上,開始創作實錄世界反法西斯和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終結的長篇小說《夢斷虎頭》。
他以嚴肅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生動形象的描述,充滿深情的文學筆觸,向全世界介紹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后一役的內幕。為了求得歷史的真實,他還請工匠在家里打造了最后一役敵我雙方態勢沙盤,為了一個細節他會像軍事指揮員那樣,對照歷史資料演示,直到達到歷史的真實為止。在小說中再現了這場驚心動魄戰爭的宏觀大局和微觀細節,熱情謳歌了蘇聯紅軍和中國官兵不怕犧牲,前仆后繼,英勇戰斗的反法西斯精神,刻畫了一批中、蘇軍人的形象,講述了中國勞工的苦難和悲慘。同時,揭露了以黑浜為代表的日本侵略者的頑固、殘忍、變態,并從人性的角度分析了日本軍人中的不同心理狀態,表現了普通士兵和家人、避難的開拓團的農民,在日本軍國主義的荼毒下的凄慘境遇。
他說:“中國需要這樣一部文學作品。不管是組織要求我進行這個主題的創作,還是自己主動為之,這都是我作為一名黨員作家應該自覺擔負起的歷史責任和義務。”
1935年,雪墨出生在吉林省扶余縣的一個小村。那正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踐踏東北大地的時候,也許正是他的幼年和童年飽受了“亡國奴”的切膚之痛,使他要以文學反映哈爾濱抗戰這一段歷史的宏愿,始終揮之不去整日繾綣在胸。他說:“也許會有人笑我使‘圣潔’的文學過于使命化和目的化了。然而我不悔,我會沿著特定的‘開拓帶’耕耘下去,直到爬行不動為止!”因為,他已經把自己的命運和哈爾濱抗戰文學緊緊地連在一起。
雪墨在平房地區工作時,從當地老人的口中知道了許多日本侵華731部隊研究細菌戰、制造細菌武器的事情。這引起他的研究興趣,但隨著他更多的挖掘采訪,更深入的考察研究,一向謙和儒雅的雪墨震驚了、憤怒了。為了那被凌辱的歷史,為了那些慘死的人們,1987年,他和齊燕濱、張國城、駱仲林共同創作了電視劇《荒原城堡——731》。
2011年,雪墨又以中東鐵路的建設為歷史背景,創作了長篇小說《遠東角斗場》,以文學的表現形式真實地記錄了全民保衛哈爾濱的歷史。它和長篇小說《哈爾濱保衛戰》遙相呼應,再一次歌頌了哈爾濱軍民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壯舉。
雪墨站起身踱步到窗前,望著外面飄飛的雪幕,目光茫然又陷入思索之中,沉默了良久后,說:我們這一個在歷史上曾被宰割的、痛苦的民族,到了現在還沒有一部像列夫·托爾斯泰反映1805年俄羅斯衛國戰爭,把拿破侖所統帥的法軍趕回法國的《戰爭與和平》這樣的史詩性的文學作品,來全方位真實立體反映中國人民自1840年以來抗擊外辱,特別是全景式反映中國抗日戰爭戰場,以及中國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反法西斯侵略,所作出犧牲和貢獻這段歷史的文學作品。
“國家的苦難不該忘記,民族的血淚應當記憶。嚴肅地思考過去,才能科學地規劃未來。這是我們當代每位文學工作者應該自覺肩負的歷史責任。”
雪墨說: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文學作品不僅要有高原,還要有高峰。這為我的哈爾濱抗戰文學創作指明了方向。我雖已年逾古稀,但思想在運動、精神仍然青春。我要深入挖掘哈爾濱抗戰的歷史,創作出既要有高原,也要有高峰的反映哈爾濱抗戰精神的、中國的《戰爭與和平》,實現總書記的殷切期望,獻給世界愛好和平的廣大讀者。
我們的采訪結束了,他健步走在紛揚的雪幕里。我望著他高大的背影,祝他健康并實現他的宏愿。我漫步在潔白的雪中,回想到1993年在哈爾濱市組織的“雪墨作品研討會”上,他發言中的一段話:“我寫這些不是為了過去,而是為了現在和將來——一個不忘記昨天的民族,才能對于今天和明天更有責任感。”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
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世世代代不能忘記過去的昨天。
責任編輯/張博zhangbo@fendouzazhi.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