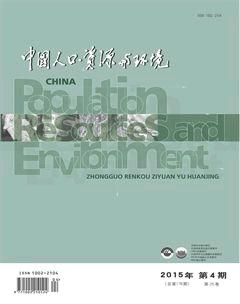農村居民點整理適宜性評價及其分區管制
郭杰等



摘要
農村居民點整理適宜性評價是農村居民點整理方案制定及分區調控的基礎。本研究以揚州市區106個行政村為對象,開展農村居民點整理的農戶意愿調查,從整理政策、人際交往、生活習慣、經濟壓力等方面評價農戶意愿大小,結合經濟、社會及區位等因素構建農村居民點整理的適宜性評價指標體系,根據適宜性大小劃定農村居民點整理適宜性分區,并制定分區管制措施。研究發現:農戶整理意愿區域差異明顯,研究區域北部和東部由于經濟發展速度較快,且農村居民點整理政策設計較為完善,如槐泗鎮鳳來村的農戶意愿分值高達36.5,而南部、西部的整理意愿相對較低,如瓜州鎮鞠莊村的農戶意愿分值僅25.9。研究表明:①將農戶意愿引入農村居民點整理適宜性評價中,不僅考慮到社會、經濟等宏觀因素,而且綜合了微觀農戶意愿,評價方法更為科學。②可拓展空間衡量居民點整理潛力,農戶意愿和人口經濟狀況是影響整理適宜性的關鍵因素,而較好的基礎設施狀況將降低居民點整理的適宜性等級。③應考慮土地利用、社會經濟、農戶意愿等分區特征,從整理模式、中心村建設和土地利用策略等方面構建差別化的分區管制政策。優先整理區可采取一次性搬遷策略,將零星村莊整體遷并至中心城區、鎮區或中心村;重點整理區應以遷村并點及閑置居民點復墾為主;適度整理區應走“滾動式”農村居民點整治之路;優化調整區應逐漸將靠近城區和鎮區的居民點納入城鎮管理體系,加速其城鎮化進程。本研究將為農村居民點整理重點區域選擇和區域差別化的管制政策制定提供參考。
關鍵詞農村居民點整理;適宜性評價;農戶意愿;分區管制
中圖分類號F31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5)04-0052-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4.007
農村居民點是中國農村土地利用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數量與結構特征影響著城鄉建設用地結構的調整與優化[1]。農村居民點整理可以優化城鄉建設用地布局,改善農村居民生產條件和生活質量,提高農村建設用地利用效率,緩解經濟發展與耕地保護的矛盾。而農村居民點整理適宜性評價是農村居民點整理時序安排、分區管制的基礎。農戶是農村土地利用的基本決策單元,作為經濟“理性人”和社會“理性人”的綜合體,其居住與生活環境的改變決策是追求生存、經濟、社會等綜合效益的均衡[2],農戶意愿直接影響農村居民點整治的決策行為。因此,從微觀行為主體的角度分析農村居民點整治的農戶意愿,研究農村居民點整理適宜性及其分區管制措施,可為差別化的農村居民點整治決策提供參考。學者從不同視角研究了農村居民點整理的相關問題,研究領域涉及借助RS和GIS技術分析農村居民點空間分布特征與動態變化,并運用GIS的空間分析功能實現其布局優化的輔助決策[3-6],探討農村居民點整理潛力的測算方法[7-9],研究農村居民點整理的實現機制[10-12]。并進行農村居民點整理適宜性評價[13-15]及分區研究[16-18],并從農用地征用[19]、農地流轉[20]和農村居民點整理[21-22]等方面開展了農戶意愿的影響因素研究。現有研究多從自然、社會經濟條件等宏觀因素出發評價農村居民點整理適宜性,但從農村居民點利用的微觀行為主體——農戶的角度,將農戶意愿應用到農村居民點整理適宜性評價的相關研究較少。本文以揚州市區106個行政村為研究區域,選擇影響農村居民點整理適宜性的社會、經濟及區位等宏觀因素,結合農戶意愿調查評價農村居民點整理的農戶微觀意愿水平,構建更為合理的農村居民點整理適宜性評價指標體系,根據評價結果劃定農村居民點整理適宜性等級分區,并提出區域差別化的農村居民點整理管制政策,為農村居民點整理重點區域的選擇和整理時序的安排提供參考。
1研究區域及數據
1.1研究區域概況
揚州市地處江蘇省中部,是南京都市圈和上海經濟圈的節點城市,素有“竹西佳處,淮左名都”之稱。2011年,揚州市地區生產總值2 630.30億元,可比價增長12.2%。揚州市區農村居民點布局呈現出典型的大散居、小聚居的特點,2011年人均農村居民點用地為222.42 m2/人,遠高于150 m2/人的國家標準。考慮到揚州市中心城區農村居民點規模較小,且隨城市化被逐步占用,因此本文研究區域為中心城區外的市區范圍,評價單元包括106個行政村。
1.2數據來源與處理
基礎數據主要包括:1∶5 000揚州市土地利用現狀圖(2011年)、揚州市交通現狀圖(2011年)等,基于Arc GIS9.3提取評價單元的土地總面積、農村居民點用地面積、農村道路面積、距離重要城鎮及交通干道的距離等評價指標值。2012年揚州市、邗江區、廣陵區統計年鑒,獲取評價單元的總戶數、常住人口數和農民人均年收入等社會經濟指標。
農戶意愿分析主要依據問卷調查數據和基層干部、農戶的訪談結果,調查時間為2012年9月和2013年3月,共開展兩次分村的實地調查,調查范圍涉及揚州市區中心城區外的106個行政村。課題組通過各鄉鎮政府召集各行政村的村干部,現場講解并確認調查內容,收集包括行政村基本情況(土地閑置率、基礎設施狀況、房屋成新率等評價指標值)。并從農戶基本情況、農戶對農村居民點整理意愿及需求、農戶對農村居民點整理政策認知等方面設計了“農戶整理意愿調查表”。每個行政村進行隨機抽樣調查了5-10戶農戶,調查采用問卷訪問方式,由訪問員在村干部不在場的情況下對農民進行面訪,通過現場講解、指導問卷填寫,以核實農戶的農村居民點整理意愿,實際完成相關問卷848份,其中有效問卷622份。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可從整理政策、人際交往、生活習慣、經濟壓力等四方面,運用綜合評價法定量測算農戶整理意愿的大小。
2基于農戶意愿的農村居民點整理適宜性評價
2.1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農村居民點整理適宜性評價是從利用現狀、社會經濟條件等方面綜合評估農村居民點整理的適宜性等級。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是提高評價質量的基礎,考慮到評價區域自然環境的大體一致性,根據綜合性、可比性、代表性、可操作性的原則,參考相關研究,本文從可拓展空間、人口經濟狀況、基礎設施狀況、區位條件四個方面[13-15]選擇11個社會經濟評價指標,從整理政策、人際交往、生活習慣、經濟壓力等方面選[21-22]取8個農戶整理意愿的評價指標,據此構建基于農戶意愿的農村居民點整理適宜性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可拓展空間是農村居民點整理挖潛數量的測度因素。本文選取居民點分散度、土地閑置率和戶均居民點用地面積三項指標來表示。居民點分散度反映居民點的離散情況,土地閑置率反映村莊空閑用地的比例,戶均居民點用地反映戶均宅基地占地面積。
人口經濟狀況是衡量農村居民生活、收入狀況的因素。本文選取常住人口比率、農民人均年收入、房屋成新率三項指標來表示。常住人口比率反映農村居民點用地的實際利用效率,農民人均年收入衡量整理的經濟基礎,房屋成新率反映整理的拆遷補償成本。
基礎設施狀況是反映居民點配套設施的完備程度的因素。本文選取道路狀況、自來水保證率、寬帶/電話/有線電視通達率三項指標來衡量農村居民點基礎設施建設狀況。
區位條件是衡量居民點通行便利程度的因素。本文選擇距重要交通干線距離、距主要城市距離兩項指標來衡量農村居民點滿足現代生活的便利程度。
農戶意愿指標是基于農戶心理來評價農村居民點整理的適宜性。農戶作為整理主體其態度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農村居民點整理是否能順利進行。農戶整理意愿本質上是一種不確定環境下的決策行為,生存環境的不確定性、社會經濟的不確定性、政策的不確定性綜合影響農戶整理與否的決策行為。因此,本文從整理政策、人際交往、生活習慣、經濟壓力四方面來評價農戶整理意愿的大小。整理政策包括民意保證率和補貼滿意度,整理政策的順利施行,需重點考慮尊重民意,并強化農戶補貼;人際交往包括從眾心理程度和鄰里關系狀況,聚居生活的村民之間感情較為密切,從眾心理在農戶決策行為中占重要的地位,鄰里關系狀況也會顯著影響農戶整理意愿;生活習慣包括生活滿意度和舊宅保留意愿程度,農戶對當前的生活越滿意其整理意愿越低,而大多數留守老人仍有較強的保留舊址不愿拆遷的心理;經濟壓力包括安置房購買承受度和異地安置生存壓力,農戶購買安置房的經濟壓力顯著影響農戶的整理意愿,而異地安置生活方式、環境改變導致的生存壓力也是制約農戶整理意愿的重要因素。
2.2評價方法選擇
擬采用多因素綜合評價法,首先用極值標準化方法對指標值進行無量綱化,然后用特爾菲法結合層次分析法確定指標權重,最后測算農村居民點整理適宜性的分值。
3農村居民點用地分區調控
3.1基于適宜性的農村居民點整理管制分區
3.1.1農戶整理意愿
農戶意愿測度指標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2。經計算,揚州市區整理意愿區域差異明顯,槐泗鎮鳳來村的農戶意愿分值高達36.5,而瓜州鎮鞠莊村的農戶意愿分值僅25.9。市區北部和東部由于邗江汽車產業園、環保科技產業園、維揚經濟開發區等板塊經濟區建設的加速推進,農村居民點整理政策的制定、被整理農民住房及長期安置的制度設計更為完善,農戶整理意愿相對較高,而南部、西部的整理意愿就相對較低。
3.1.2整理適宜性分區
綜合可拓展空間、人口經濟、基礎設施、區位條件和農
戶意愿,以行政村為評價單元,計算研究區域農村居民點整理適宜性(見表3),運用總分頻率曲線法對綜合分值進行頻率統計,根據適宜性分值選擇頻率曲線波谷處作為等間分界,考慮各行政村整理能力和整理迫切度等實際情況的差異,劃定揚州市區農村居民點整理適宜性區,將各分區命名為優先整理區、重點整理區、適度整理區和優化調整區(見圖1)。
3.2基于農村居民點整理適宜性的分區管制措施
3.2.1優先整理區
包括開楊、和玉、桑園及歐陽等共23個行政村,主要分布在方巷鎮和公道鎮,以及槐泗鎮和泰安鎮等靠近中心城區的部分。優先整理區2 086.38 hm2,占總規模的1870%。該區域農村居民點布局分散、規模較小,土地閑置率高、房屋陳舊,基礎設施配套不完善且離中心城區或交通干線的距離較遠,農村居民點整理的農戶意愿最強烈,該區域也不具備人口和產業集聚的條件,農村居民點整理潛力較大,實施過程中的阻力也較低。該區可作為揚州市區農村居民點整理實施的優先區域,可采取一次性搬遷的策略,將零星的村莊整體遷并至中心城區、城鎮鎮區周邊或就近的中心村。同時加強中心村等集中安置點的規劃建設,結合“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與農村居民點減少相掛鉤”和“萬頃良田”建設工程等政策,拓展整理資金來源,統籌城鄉土地利用,推進土地資源集約與節約利用。
3.2.2重點整理區
包括王集、迎新、柏樹及黃橋等共35個行政村,主要分布在揚州市區東南部的杭集、李典和頭橋三個鎮,以及公道鎮和方巷鎮除優先整理區的部分。重點整理區3 639.15 hm2,占總規模的32.62%。該區為城郊都市農業區,部分區域為“萬頃良田”建設工程實施區域,但該地區耕地整理補充耕地能力和整理迫切度較低。整理方式以遷村并點及空置居民點復墾為主,整理區要注重耕地質
量建設及都市農副產品供應基地的建設;中心村的選擇要遵循合理布局、節約用地的原則,重點對村內舊宅基地、閑散地進行整理改造,提高土地集約化利用水平,使分散的自然村逐漸聚集,節約土地資源,重構鄉村土地利用空間。
3.2.3適度整理區
包括國王、友誼、新龍及方集等共34個行政村,主要分布在揚州市區西部的瓜州、楊廟和楊壽三鎮。適度整理區3 932.96 hm2,占總規模的35.25%。該區距離中心城區的舊城區較近,區位條件和經濟發展良好,建設用地外延擴展趨勢較快;農村居民點整理的農戶意愿強烈,但居民點集中且房屋成新率高,整理成本較高,不適宜大拆大建。該區應選擇基礎設施條件較好的位置建設中心村,農村居民點整理應以內部挖潛為主,遏制住宅用地侵占村邊良田;鼓勵農戶循環利用村落中的舊宅基地、閑置宅基地和廢棄的“工業大院”,走“滾動式”農村居民點整治之路。同時結合農村綜合改革,著眼特色、優質與高效性,加速農業產業化和農村城鎮化進程。
3.2.4優化調整區
包括戚橋、趙莊、陳祠及人民灘等共14個行政村,主要在揚州市中心城區的周邊鄉鎮、各鎮區所在行政村穿插布局。優化調整區1 498.13 hm2,占總規模的13.43%。該區域居民點用地位于城鎮區邊緣,交通便捷,地區經濟發達,人口密集,基礎設施較完善,村莊功能不斷強化、規模不斷外延,農戶整理意愿較低,具有實現農村城鎮化的現實可能性,是揚州市未來農村居民點保留與發展的重點區域。同時村內新房比例高,且大多已進行拆遷并村,布局規模化,較不適宜進行整理。該區應著眼于現有居民點
的優化調整,靠近城區和主鎮區的居民點應逐漸納入城鎮管理體系;具有一定規模、對周邊農村居民點具有輻射和帶動作用的居民點應作為中心村重點發展;在村莊建設上應汲取城鎮集中建設的經驗,制定村莊建設規劃,統建聯建公寓式農宅,引導鄉村工業向小城鎮或者工業園區集中,加速農村居民點的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
4結論與討論
(1)通過農戶意愿調查,結合相關文獻梳理,發現農村居民點整理農戶意愿受整理政策、人際交往、生活習慣和經濟壓力等農戶微觀心理因素影響。本研究將農戶意愿引入農村居民點整理適宜性評價指標體系,不僅考慮到社會、經濟等宏觀因素,而且綜合了微觀農戶意愿,評價方法更為合理。
(2)本文從可拓展空間、人口經濟狀況、基礎設施狀
況、區位條件四方面選擇11個指標,從整理政策、經濟壓力、人際交往、生活習慣等農戶意愿視角選擇8個指標,構建農村居民點整理適宜性評價指標體系。可拓展空間可衡量居民點整理潛力,農戶意愿和人口經濟狀況是影響整理適宜性的關鍵因素,而較好的基礎實施條件將降低農村居民點整理適宜性等級。
(3)不同區域農村居民點整理適宜性差異較大,本文基于農村居民點整理適宜性評價結果,并結合整理能力和整理迫切度等實際情況,劃定了農村居民點整理適宜性等級區域,包括優先整理區、重點整理區、適度整理區和優化調整區。應考慮農村居民點土地利用、社會經濟、農戶意愿等分區特征,從農村居民點整理模式、中心村建設和土地利用策略等方面構建差別化的分區管制政策體系。
(4)農村居民點作為農村人地關系的核心表現之一,其整理適宜性還應受當地歷史因素和人文景觀等因素的影響,由于數據獲取的原因,本研究尚未對此類因素進行定量分析。如何完善農村居民點整理適宜性評價指標體系,以及指標的量化等問題(如更科學的農村居民點整理農戶意愿的定量化研究),有待進一步探討。
(編輯:李琪)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曲衍波, 張鳳榮, 姜廣輝, 等. 基于生態位的農村居民點用地適宜性評價與分區調控[J]. 農業工程學報, 2010, 26(11): 290-296. [ Qu Yanbo, Zhang Fengrong, Jiang Guanghui, et al.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Niche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Use Suitability Assessment and Zoning Control [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2010, 26(11): 290-296.]
[2]周婧, 楊慶媛, 張蔚. 貧困山區不同類型農戶對宅基地流轉的認知與響應:基于重慶市云陽縣568戶農戶調查[J]. 中國土地科學, 2010, 24(9): 11-17. [ Zhou Jing, Yang Qingyuan, Zhang Wei. Different Types of Farmers in Poor Mountainous Areas of Cognition and Response of the Homestead Circulation:Based on the ChongQing YunYangXian 568 Farmer Households Survey [J]. Journal of China Land Science, 2010, 24(9): 11-17.]
[3]Hill M. Rural Settlement and the Urban Impact on the Countryside[M]. Tianjin: Hodder and Stoughton, 2003.
[4]Inge T, Jan U. Modeling Residential Location Choice in an Area with Spatial Barriers[J]. Regional Society, 2002, 36(6): 13-64.
[5]姜廣輝, 張鳳榮, 譚雪晶. 北京市平谷區農村居民點用地空間結構調整[J]. 農業工程學報, 2008, 24(11): 69-75. [Jiang Guanghui, Zhang Fengrong, Tan Xuejing. Spat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of Beijing Pinggu District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2008, 24 (11): 69-75.]
[6]陳振杰, 李滿春, 劉永學. 基于GIS的桐廬縣農村居民點空間格局研究[J]. 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 2008, (2): 45-49. [Chen Zhenjie, Li Manchun, Liu Yongxue. Tonglu County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Based on GIS Spatial Pattern Study[J]. 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Yangtze River Basin, 2008, (2): 4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