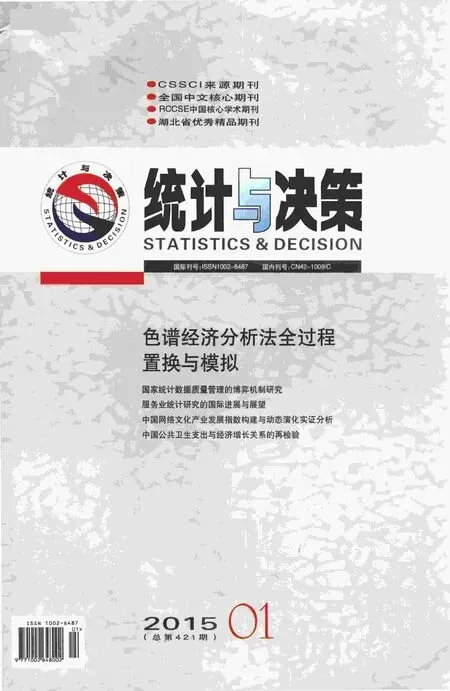我國生態環境質量的變化與地區差異分析
呂雄鷹
(湖南商學院 經濟與貿易學院,長沙410079)
0 引言
目前中國整體的生態環境質量是提高了還是降低了?中國各地區的生態環境質量水平又是如何變化?地區間生態環境質量變化是一致的,還是存在明顯差異?對于以上問題的分析,不僅能夠讓我們了解我國生態環境質量的現實狀況,還能為全面理解我國生態環境質量變化過程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本文從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的壓力—狀態—響應模型(Pressure-State-Response,簡稱PSR)出發,構建一個包含16個基礎指標的生態環境質量指標體系,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我國以及各地區1997~2010年間的生態環境質量水平進行測算并做出分析。
1 我國生態環境質量指標體系構建
生態環境質量不是一個簡單的環境指標,而是一系列因素的綜合反映,測度生態環境質量必須是多方面、多指標所構成的一個指標體系。目前,生態環境質量指標體系的框架比較多,其中,壓力—狀態—響應模型是研究環境質量問題常用模型之一。20世紀70年代,加拿大統計學家David Rapport和Tony Friend提出壓力—狀態—響應模型,并用于生態系統健康評價問題的分析。隨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將其發展,并用于生態環境質量問題的研究。壓力—狀態—響應模型采用“原因—效應—響應”的思路,體現了人類與生態環境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從而更好地對生態環境質量這一復雜系統進行評價。因此,壓力—狀態—響應模型能夠較全面地衡量一個地區的生態環境質量水平。依據壓力—狀態—響應模型,我國生態環境質量指標體系應該包含3個二級指標,即生態環境質量壓力指標,生態環境質量狀態指標,生態環境質量響應指標。其中,生態環境質量壓力指標用來說明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造成的負擔與產生的潛在負向影響;生態環境質量狀態指標用來說明在壓力下自然資源和生態系統要素的變化狀態;生態環境質量響應指標則用來說明面對環境壓力時人類處理環境問題的能力與采取的措施(韓峰,玉琢卓,2010)。依據我國全國層面和區域層面已有的統計數據,本文選取人均工業廢氣排放量(噸/人)、人均工業廢水排放量(億標立方米/萬人)、人均工業固體廢棄物產生量(噸/人)、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人均生活用水(噸/人)、化肥施用強度(%)、人均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噸/人)等7個指標作為生態環境質量壓力指標;選取森林覆蓋率(%)、萬人擁有廁所(座)、人均水資源擁有量(立方米/人)、自然保護區占轄區比重(%)、人均公共綠地面積(平方米/人)等5個指標作為生態環境質量狀態指標;選取工業廢水排放達標率(%)、工業廢氣處理率(%)、工業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工業三廢綜合利用產值(萬元)等4個指標作為生態環境質量響應指標,見表1。
2 數據來源與測算方法選擇
本文選擇1997~2013年我國30個省份、自治區和直轄市(不包括西藏)省際面板數據以及全國層面的數據,個別缺失數據采用上下年均值估測得出。全文共包括三大類指標,生態環境質量壓力指標有7個基礎指標,生態環境質量狀態指標有5基礎指標,生態環境質量響應指標有4個基礎指標,一共16個指標。
(1)生態環境質量壓力指標。人均工業廢氣排放量、人均工業固體廢棄物的產生量、人均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通過當期總量除以當期期末口總數計算獲得,原始數據來源于歷年各省市統計年鑒與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化肥施用濃度等于化肥施用量除以有效耕地面積,化肥施用量與有效耕地面積數據來源歷年各省市統計年鑒和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人口密度等于區域人口總數除以行政區域面積,原始數據來源歷年各省市統計年鑒和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人均日生活用水數據直接自歷年各省市統計年鑒和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表1 我國生態環境質量指標體系
(2)生態環境質量狀態指標。森林覆蓋率、人均公共綠地面積、自然保護區占轄區比重、萬人擁有廁所等數據來源各省市統計年鑒和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人均水資源擁有量等于水資源總量除以人口總數,其中,全國水資源總量1997~1999年數據參照國家水利部1997、1998、1999年水資源公報,2000~2013年數據來自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各省市水資源總量1997~2003年數據來源于歷年各省市統計年鑒。
(3)生態環境質量響應指標。工業廢氣處理率、工業廢水排放達標率、工業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工業三廢綜合利用產值等數據來源歷年各省市統計年鑒和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目前,在測算環境類綜合指數中,主成分分析法是非常普遍和常用的一種方法。因此,本文也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來測算我國全國層面和區域層面生態環境質量綜合指數。
在進行主成分分析時,如果指標系統中各子指標變化方向與系統的總體方向存在差異,即有些指標是體現生態環境質量的正向發展,而有些指標則體現生態環境質量負向發展,如果不對指標進行相應處理,就不能判定最終生態環境質量綜合指標數值增大是反映生態環境質量的提高,還是降低。因此,這需要采用一定的方法對部分子指標進行處理。本文參考鈔小靜等(2011)的處理方法,對表1中所有逆指標均進行倒數化處理,從而使所有指標對生態環境質量的作用力都是一樣的。另外,各指數量綱不同可能會帶來變量取值分散的影響,若直接采用原始數據進行分析還會造成主成分向較大方差或較大數量級指標偏倚,因此做主分成分析前還對各指數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
3 我國生態環境質量綜合指數的測算與分析
3.1 各級指數的統計特征
主成分分析的基本思想就是降維,從眾多的原始變量中合成少數的主變量,用主變量替代原始變量。各主成分的權數(貢獻率)能科學客觀的對多變量進行綜合分析,可以代表研究事物的特征。主成分分析基本步驟是:首先,將數據進行標準化;接著,求出相關系數矩陣、特征根、特征向量和貢獻率等;其次,依據相關原則提取主成分因子(一般選取前m個主成分累積貢獻率超過85%的指標定義為主成分);第三,計算主成分;最后依據主成分的相應權重計算綜合指數。所得結果見表2。
表2描述了我國生態環境質量綜合指數、生態環境質量壓力指數、生態環境質量狀態指數、生態環境質量響應指數的統計特征。由表2可以發現,壓力指數第一成分方差貢獻率為78.105%,第一、二成分的累計方差貢獻率91.626%;狀態指數第一成分方差貢獻率為72.219%,第一、二成分的累計方差貢獻率88.483%。依據提取主成分因子的原則(累積貢獻率超過85%),壓力指數和狀態指數采用第一、二成分來確定相應權重具有較強的合理性。同理,根據這一原則,響應指數采用第一成分來確定相應權重,生態環境質量綜合指數采用第一、二、三成分來確定相應權重。

表2 各級指數的統計特征
3.2 我國全國層面生態環境質量的測度結果
根據圖1可以發現:自1997年以來我國整體層面的生態環境質量水平基本上呈現下滑的態勢,其中1997~1999年這一階段生態環境質量水平基本保持平穩,下滑的幅度很小,2000~2007年這8年生態環境質量水平處于一個快速下滑的階段,2008年生態環境質量水平有小幅度回升,2009年又出現較大幅度的下滑,而2010~2013年則基本保持平穩,沒有出現明顯的下滑。我國整體層面生態環境質量呈現這樣的變化其主要原因在于:近年來我國人均工業廢氣排放、人均工業固體廢棄物、人口密度等變量出現快速上升的趨勢,人均工業廢水排放、化肥施用濃度等變量也出現一定幅度的上漲,環境壓力很大,而且這些壓力類基礎指標在計算主成分又占有較大比重,所以最后導致我國整體層面生態環境質量出現下滑趨勢。從圖1也可以看到,1997~1999年生態環境質量壓力指數變化不大,在1999年以后,該指標呈現出明顯的下滑趨勢,其變化趨勢基本與生態環境質量綜合指數保持一致。另外,1997~2013年我國生態環境質量狀態指數及響應指數則基本呈現出上升的趨勢。這表明,雖然我國在環境問題治理方面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效果并不十分明顯,其原因在于人們為了社會發展施加給生態環境太多的壓力,最終導致我國生態環境質量水平處于下滑的狀態。

圖1 我國1997~2013年我國生態環境質量測算
3.3 我國區域生態環境質量的測度結果
表3描述代表性年份我國各地區生態環境質量綜合指數的變化趨勢。根據表3可以發現,我國各地區生態環境質量綜合指數變化存在很大差異,大致呈現出4種不同的變化趨勢:
第一種是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變化趨勢,例如,北京、天津、重慶、四川、貴州、陜西、甘肅、青海、寧夏等9個地區,它們的生態環境質量開始在波動中上升,然后出現下降的趨勢。其中,轉折點大概都出現在2007年左右,具體而言,北京、天津、重慶、四川、貴州、陜西、甘肅是在2008年后環境質量水平開始出現下滑,青海、寧夏是在2007年后環境質量水平開始出現下滑。由于2008年北京要舉辦奧運會,因此政府非常重視北京及其周邊地區的生態環境治理,因此在1997~2008年之間北京、天津地區的生態環境質量基本處于一個上升階段,而在2008年后,缺乏外界壓力和監督,生態環境質量開始出現下滑。除北京、天津兩省外,其他省份均屬于經濟較為落后的西部地區,工業經濟并不發達,因此環境壓力并不大,所以出現生態環境質量上升的趨勢。但是,近年來,隨著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出現飽和,許多工業產業開始向西部轉移,從而導致這些地區環境壓力增大,出現生態環境下滑的趨勢。
第二種是呈現波動中上升的變化趨勢,例如,河北、上海、福建、廣東等4個地區。其中,河北在剛開始還出現略微下降的變化,2000年后才出現上升的趨勢,目前上升幅度并不大,2013年生態環境質量綜合指數保持在2.115。廣東開始呈現快速上升的過程,而在2004年后生態環境質量基本保持穩定,上海、福建則一直基本保持平穩上升趨勢。這些地區經濟基礎良好,社會環保意識強烈,環境污染防治投資力度很大,因此生態環境質量較好。
第三種是呈現波動中下降的變化趨勢,例如,山西、吉林、內蒙古、新疆、遼寧、安徽、黑龍江、江西、云南、湖北、山東、湖南、河南、廣西、海南等15個地區。這些地區在經濟發展和污染治理方面表現不均衡,比如山西、內蒙古等地區經濟不算發達,但是作為資源大省在源源不斷向外輸送資源的同時,環境質量也承受著巨大壓力。另外,近年來,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一些中部地區經濟出現快速,工業企業數量增加,工業“三廢”污染現象嚴重,導致環境質量出現下滑。
第四種是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變化趨勢,例如,江蘇和浙江2個地區。雖然江蘇和浙江生態環境質量水平目前是處于上升階段,但是其上升幅度都并不大,與1997年相比,它們的生態環境質量水平還是下降的。這說明,近年來,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江蘇和浙江已經開始真正重視環境問題,加大對環境污染的治理。

表3 代表性年份我國各地區生態環境質量綜合指數的變化趨勢
3.4 我國地區生態環境質量的差異


圖2 我國地區生態環境質量的差異
由圖2可以發現,1997~2013年σ系數波動呈現出“V”型變化,1997~2003年呈下降趨勢,2004~2013年呈上升趨勢。這說明,1997~2003年我國地區生態環境質量差異在減小,而在2004~2013年我國地區生態環境質量差異在增大。σ系數波動呈現出“V”型變化其主要原因在于,1997~2013年我國有些地區的生態環境質量水平是在提高的,例如,河北、上海、福建、廣東,還有北京、天津、重慶、四川、貴州、陜西、甘肅、青海、寧夏等地區也算是生態環境質量水平在整體上是有所提高的,而有一些地區的生態環境質量水平是在下降的,例如,山西、內蒙古、吉林、遼寧、云南、安徽、黑龍江、新疆、山東、江西、湖北、河南、廣西、湖南、海南。
4 結論
經濟的快速增長雖然大幅度地提高了人們收入和生活水平,但是其背后隱藏的環境問題也不容忽視,人們也越來越關注環境問題。本文依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發展的壓力—狀態—響應模型,構建一個包含16個基礎指標的生態環境質量指標體系,并運用主成分分析法來測算我國全面層面和區域層面的生態環境質量水平。其研究結果表明:(1)雖然我國在環境問題治理方面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人們為了社會發展施加給生態環境太多的壓力,最終導致我國生態環境質量水平處于下滑的狀態,即,1997~2013年我國全面層面的生態環境質量呈現下降趨勢。(2)我國地區間的生態環境質量變化并不相同,呈現4種變化趨勢,例如,先上升后下降的變化趨勢,波動中上升的變化趨勢,波動中下降的變化趨勢,先下降后上升的變化趨勢。(3)衡量地區間生態環境質量水平差異的σ系數呈現“V”型的變化形態,即,1997~2013年我國地區生態環境質量差異呈現先下降后增大的變化趨勢。
[1]鈔小靜,任保平.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時序變化與地區差異分析[J].經濟研究,2011,(4).
[2]高珊,黃賢金.基于PSR框架的1952~2008年中國生態建設成效評價[J].自然資源學報,2010,(2).
[3]管衛華,孫明坤,陸玉麒.1986~2008年中國區域環境質量變化差異研究[J].環境科學,2011,(3).
[4]郭天配.中國環境質量與經濟發展階段性關系的實證研究[J].財經問題研究,2010,(4).
[5]韓峰,玉琢卓.產業結構變遷對生態環境質量的影響研究——以湖南省為例[J].科技與經濟,2010,(4).
[6]李曉秀.北京山區生態環境系統穩定性評價模型初步研究[J].農村生態環境,2000,(1).
[7]劉耀彬.江西省城市化和生態環境關系的動態計量分析[J].資源科學,2008,(6).
[8]梅卓華,方東,宋永忠.南京城市生態環境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研究[J].環境科學與技術,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