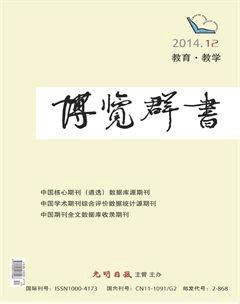車.城
傍晚,冷,車水馬龍。我提著像是塞滿石頭的行李包,掛著過膝的長款羽絨服,向從遠處來漸顯輪廓的一輛輛笨重龜行的車投去無奈的目光,心中默念著一些熟悉的數字。
前面的路是堵了吧。我默默收回目光。車站邊的候車人不少,他們肅立在肅殺的寒風中,形色各異,任憑初上的路燈光把他們或年輕或滄桑的身影拉得老長——活像一根根棍。說他們形色各異還是不恰當的,因為他們的赫然是一副被冷風冰凍住的樣子,默無表情,疲倦。他們齊刷刷地站向馬路,任憑一根根吐著溫暖骯臟煙氣的排氣管在他們身邊留下漸漸彌散在昏暝里的濁污,不言不語。他們都還保持著直立的形態,大概是在他們眼中,比起疲憊不堪地靠在臟兮兮的路燈邊上,順便染一件土灰色的新衣服,腿腳那點酸痛算不上什么。
我突然就留戀起剛剛撤下的斜陽了。起碼它蹭過的云層都還沾染著有白天溫度的氣息,雖然那像極了被血水洗過。暖橘色的燈光沒能驅散入夜的驚悚和寒意,并且這燈光打在人們臉上更是顯出一種詭譎的色彩——加重他們疲憊的色調。他們的思緒何去何從?白天的枯燥委屈,劣于他人的穿著用品,還是即將面對的一些些無聊瑣事。他們的視線散亂而毫無目的,甚至沒有焦距。我的臉似乎是凍僵了。冰冰涼的風連綿不斷地侵襲著我暴露在冗長服飾之外的面部。我試圖做一些奇怪的表情,抬升和擴張幾乎沒有知覺的面部肌肉,沉重的感覺襲來,我慶幸我還沒被凍成面癱——像黯淡的人們那樣。所幸也不會有人關注到這一幕,他們仍苦苦等待,心里默念著一個個本身毫無意義的數字,松懈了目光,或者把了無生氣的臉對著手機屏幕,任憑手機在臉上映出詭譎的可怖熒光。所以他們并不會突然調轉過頭來看一個對著馬路上方的空氣齜牙咧嘴、擠眉弄眼,身材臃腫衣著冗長抱著行李四處張望的小姑娘。
終于有車駛來,可惜太擁擠,可惜不是我能乘坐的。不過人群總算躁動起來。一個背包的小伙子刮掉了攜公文包大叔的手機,小伙不住地道歉,大叔撿起手機擺擺手便不再理會。一聲聲“不好意思”順著夜風漸遠,飄上了擁擠的車,隨著引擎聲駛出可關注的范圍。而一個穿黑色長服的老女人把目光瞥向那里,撇撇嘴,又斜回眼去,默念她的數字。
車的擁擠程度幾乎“前門擠上,后門擠下”的飽和。但在我的眼中,他們空虛得很。一張張鍍上路燈冷漠顏色的居高臨下、目光放空、無所適從、各懷心事的臉對著窗外,候車人的所在,然后視線近乎無轉動地隨著車行而平移,沒有任何關注點,沒有一點生氣在臉上。那一車百無聊賴了無生氣的人或憑或立,他們之間沒有任何的交談,哪怕是視線的交集。
我坐車的時候又何嘗不是這種神態,這種態度呢。面對一車死氣沉沉,誰都不想搭理誰的人,再激昂流溢的神采也只得乖乖收回肚里,換上一副帶著面具似的表情。
近乎凝固的氣氛在一個小男孩闖入后變得奇怪。他不住地哭喊,說著一些含糊得恐怕只有摯親能聽懂的話。他在我們身邊竄來竄去,可惜人們也只是瞥去一些意味不明的目光。他的媽媽還是把他捉了回去,他被摁在草坪邊,也失了言語。
好不容易有所流動的氣氛又一次僵板住。冷和餓大概是人類一生抗爭的主題。這里據海邊不遠,沾染了海風氣味的空氣逆風爬過高峻冰冷的高層建筑物,到達這里時也只剩下了干冷和僵硬。想到這里竟嗅到些許酸澀的氣味。
我總也不能永遠停留在這里。車門滑開,潮暖污濁的空氣打在臉上,竟讓面部肌肉緩和起來,可此時的我卻不想用它來演繹任何表情了。照明燈被引擎聲嚇得丟了魂。車廂一片漆黑和死寂。我想起幾年之前被要求天天寫日記的日子里,有事就寫寫,沒事也得扯幾扯。從行云到晚霞,夜幕的沉降拉開一片思緒。
確實很久沒有這樣的體會了。幾經波折已經在單元樓下。燈都沒亮。或許他們回家了,只是沒開燈呢。胡思亂想,嫻熟地摸出鑰匙開門——媽,我回來了。空氣幾乎是粘滯的,因為它在這一刻靜止。一片漆黑,空曠寂寥。爸,我回來了。我毫無意義地對著沒有生氣的房間叫嚷。只是靜。耳邊也只有空氣相互摩擦的細微聲響。我索性扔了包在地上,打開電腦。開始只屬于自己的奮斗。
作者簡介:邵蔚(1998-),女,籍貫:山東省即墨市,山東省青島第二中學 。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