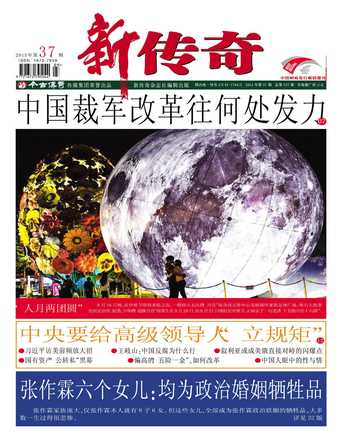偏高的“五險一金”,如何改革
有專家認為,對“五險一金”的改革,需要很多與社保服務措施相配套的細則,涉及到利益調整的因素非常復雜,不是一個簡單的降低稅率標準的數字游戲,而是一個牽一發動全身的社會制度方面的調整。
8月30日,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聯合清華大學民生經濟研究院發布《2015年中國企業家發展信心指數(上半年)》報告,稱近八成企業家認為“五險一金”的支出負擔過重且稅負過高。針對“五險一金”過高的費率,“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降低稅率標準的數字游戲,而是一個‘牽一發動全身的社會制度方面的調整。”財經評論員劉艷表示。
社保費率總體偏高
我國城鎮職工繳納的“五險一金”中,“五險”指的是養老、醫療、失業、工傷和生育保險,通常稱之為“社保”;“一金”是指住房公積金。
李建是河北某地一家中小企業的負責人,公司的員工不到10人。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坦言,在當前市場行情不好的情況下,“五險一金”帶來的壓力更加明顯。
“現在用的多是臨時工,上一天班給一天的錢,年底再發點獎金,沒有交‘五險一金。這樣企業壓力小,員工到手的錢多,雙方都能接受。”李建說。
“不可否認,在目前我國經濟處于下行通道的時期,眾多企業本身已經肩負著相對較高的稅負負擔,同時還需長期扛著占工資比例較高的‘五險一金支出,確實疲憊。”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社會研究所副研究員單菁菁表示,這甚至造成部分企業尤其是使用農民工占比較高的企業通過漏繳、少繳社保費用降低企業生產經營成本的現象頻現。
在去年12月舉行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馬凱在回答委員詢問時表示,現在的養老保險繳費水平確實偏高,“五險一金”已占到工資總額的40%至50%,企業覺得負擔重。工資總額是指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直接支付給全部職工的報酬總額,并非職工個人所得工資。
企業在多交錢的同時,員工到手的錢也在變少。
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張育彪就以深圳為例算了一筆賬:養老保險繳費比例為22%;醫療保險為8.7%;失業保險2%;工傷保險0.8%;住房公積金則為10%至40%之間,單位和個人各承擔一半,最低繳納10%;以上“五險一金”合計最低繳納比例約為43.5%。也就是說,企業給員工加薪100元,員工所得拿不到60元。
“目前我們國家各項社會保險的總費率超過40%,總體是偏高的。”今年1月23日,人社部有關人士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這樣的繳費比例在全球也屬偏高。同樣關注這個問題的全國人大代表謝子龍通過調查了解到,在全球125個國家中,繳費比例超過40%的只有11個國家,除了中國,其他10個都是高福利的歐洲國家。
養老保險與公積金負擔感最重
劉艷在接受采訪時認為,人們對于“五險一金”負擔重的感受,除了繳費過高帶來的經濟壓力,更主要的是擔心將來的收益與當下的付出不對等。在“五險一金”中,養老保險與公積金帶來的這種負擔感最重。
人們對于養老保險負擔重的感受在于支付的過多。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就業與社會保障中心研究員封進指出,我國企業社保繳費比占到工資總額的40%至50%,其中最高的繳費項目就是養老保險,占到20%。
封進介紹,1997年國務院26號文,規定企業統一建立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養老保險制度。但由于此前我國沒有社保制度,企業和職工從未繳納過社保,所以當時的退休人員的社保賬戶成了“空賬”。為了有充足的財力贍養企業已退休的人員,填補財政“窟窿”,我國的養老保險就規定為20%這樣一個相對比較高的繳費比率。
“我國養老保險歷史欠賬問題沒有解決,已退休職工的養老金需要由在職職工負擔,而在職職工還要為自己的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繳費。”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副院長鄭春榮副教授也表示,欠賬問題是導致其費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鄭春榮認為,導致養老保險費率過高的原因還有其他因素,包括:繳費基數不實,許多參保人實際工資遠高于繳費基數;中斷繳費的參保人數量較多,造成繳費人群的負擔較重;退休年齡較低;地方政府缺乏養老保險征繳的積極性,認為嚴格征繳會影響招商引資。
公積金最讓人詬病之處則是使用率低。
截至2014年年底,住房公積金已經覆蓋全國1.1億城鎮職工,總額超過7.03億元。在劉艷看來,與養老保險相比,公積金交的額度也不算低,但在使用率上,卻比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差很多。人們對于公積金負擔重的感受,不是感覺錢不應該繳納,而是認為自己繳納之后不能享受到相應的回報。
劉艷指出,公積金使用率低,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因為不能全國聯網而導致的資源浪費。公積金如果不能聯網使用,人們進行跨地區擇業時,就只能重新計算公積金,這對勞動者是不公平的,也變相成為了地方政府的小金庫。
直到今年3月,全國主要100個城市住房公積金才基本實現聯網監控。而這一被住建部推動的工作,從計劃到實現耗時3年,其間更是被至少3次推遲。
“盡管這樣,也只是實現了全國主要100個城市的信息聯網。公積金不能全國聯網使用,不僅造成大量社保資源的流失,也降低了大家繳納費用的意愿。”劉艷說。
諸多復雜的利益調整
“企業和個人同時感覺到負擔重和不公平,是對社保的滿意度和公平感最直接的信息反饋。此時,就應該對這項社會政策的不合理之處進行反思。”在劉艷看來,“五險一金”從對應的種類上來講,是符合國情的,但是總體的比例控制可能還不是特別科學。
馬凱在上述會議上坦言,問題的解決有些難度,現在社保基金收入增長幅度慢于支出增長幅度,這又是一個矛盾。“一方面企業反映繳費水平太高,一方面降低繳費水平又會影響當期的收入,這個兩難矛盾怎么解決,需要研究。”
事實上,“五險一金”的改革,并不只是解決上述兩個矛盾。
“以醫療保險為例,基本醫保制度覆蓋人數已經超過了13億人,全民醫保體系基本形成,今年的工作是全面推行大病醫保制度。醫療保險需要從普及向高質量轉變,而這也需要長時間的過程才能完成。如果降低費率,勢必會影響到這方面的進展。”劉艷強調,單一的調低費率繳納標準的提議并不科學,會影響到福利。
“社會平均工資的認定不夠科學合理,致使低收入人群感覺社保繳費負擔重,這就需要調整薪酬結構;企業負擔重,是因為在‘五險一金之外,承擔了過高的稅負和其他隱性成本,在還未享受到福利的時候就被稅費壓垮,這就需要繼續‘減稅降費的改革;公積金的癥結在于資源浪費與效率低下,既要繼續公積金全國聯網的工程建設,也要加強服務意識以提升人們的滿意度,這就需要加強政府職能轉型。”劉艷指出,改革勢必會涉及到財稅改革、企業減負、職能轉型等多個領域。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靈也認為,不能籠統地降低繳費率,因為會影響待遇。更應該通過提高統籌層次和規模效應來降低社保成本,在保證既定替代率基礎上,可以考慮一定程度上降低費率。
劉艷認為,目前來看,直接降低“五險一金”的費率空間并不大,但可以通過提升員工收入、減輕企業負擔等方式,來減輕“五險一金”所帶來的負重感。
“員工漲工資要建立在企業贏利的基礎上,而企業贏利則需要通過改革的方式來減輕負擔。因此,針對企業進行減負,成為整個改革的重要著力點。”劉艷說。
劉艷認為,在下一步的政策制定中,最核心的工作是建立企業的專項基金和大數據的聯網平臺。利用大數據把社保和企業的實際經營成本的信息關聯起來,將社保公司、稅務、工商等信息在互聯網的基礎之上設定出一個警戒參考值,以此作為政策制定的決策依據。同時,利用大數據的信息,更好地發揮企業的專項基金,通過補貼和補助的方式,給予中小企業特別是創投企業相應的扶持。這種差異化的扶持力度,將會給予依法繳納費用的企業更好的服務。
(《法治周末》201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