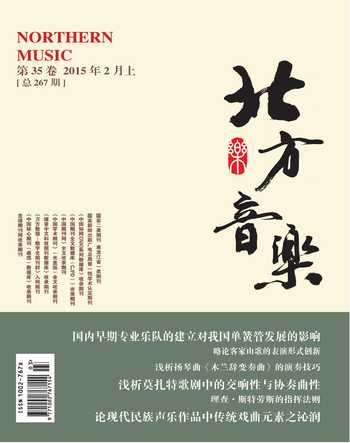淺析勛伯格《華沙幸存者》
牟茗
【摘要】通過對奧地利作曲家勛伯格的研究,分析他的作品《華沙幸存者》。主要從寫作背景、技法、曲式、旋律、和聲等方面進行分析。對他自己創立的12音序列作曲法作了一定的介紹,并把這種作曲手法充分應用到了此部作品中。
【關鍵詞】勛伯格;12音序列作曲法;華沙幸存者
奧地利作曲家勛伯格(1874-1951)是二十世紀音樂發展史巾最偉大的作曲家之一。作為音樂領域中表現主義風格的開拓者,他用音樂揭示了真實的現實與人生,觸摸到了人的靈魂巾更加深沉、痛苦的一面;作為12音序列作曲法的首創者,他展示了不同于傳統的思維方式,提供了全新的音樂組織手段。
《華沙幸存者》作于1947年。由于納粹政府的排猶政策,身為猶太人的勛伯格早在1933年就離開r任教8年的柏林普魯士藝術學院,來到美國。他先后在波士頓馬爾金音樂學院、洛衫磯加州大學任教,同時繼續音樂創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勛伯格心巾充滿了激憤,他從早年信奉的天主教改回了古老的猶太教,以此來表明他作為一個猶太人的自尊.
1947年夏天,勛伯格在報紙上讀劍一篇關于戰爭期問納粹迫害猶太難民的報道。其巾描述了一個令人震動的場面:當納粹士兵強行集合起猶太人,欲將他們送進毒氣死刑室的時候,面對死亡的猶太人突然齊聲唱起了古老的猶太宗教歌曲《聽吧,以色列人》。這歌聲激發起了難民們作為人的自尊,在生命的最后時刻給了他們永生的信念。73歲高齡的勛伯格被這則報道激動不已,而就在這幾天里,他又親耳聽到了一位從華沙猶太難民營里逃出來的人講述的可怕經歷。一種難以抑制的情感促使他拿起筆來,在12天里一氣呵成地寫完了包括全部歌詞和音樂的杰作《華沙幸存者》。第二年,即1948年11月4日,這部作品在美國新墨西哥州的阿布圭基首演,獲得了巨大成功,熱烈而持久的掌聲使指揮家和演奏家們不得不將長達8分鐘的全曲又重演了一遍,以后在許多次演出中都是如此。
勛伯格采用的寫作技法是他自己創立的12音序列作曲法,在這里有必要簡略地作些介紹。12音技法是無調性的,各不相同的12個音的地位完全平等,而不象傳統的調性音樂那樣,有作為巾心的主音和從屬于主音的屬音、下屬音、導音之分,也不存在穩定或不穩定的等級關系。作曲家在開始寫作時要預先設計一個由l2個不同的(其巾任何一個都不得重復出現,以免造成“重心”)、沒有時值的音組成的“音列”,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個音列有點象是傳統作曲技術中的”主題”,但在實際的運用和發展巾,它的變化卻遠遠超出了傳統的主題發展手段。
曾有人誤解勛伯格的技法,以為這是一種機械呆板的、缺少創意的思維方式,用它來作的樂曲也必然是枯燥得有如數學題一樣的東西。其實不然,《華沙幸存者》就是最生動的例證。而且,就象勛伯格自己所說的,他的技法是從傳統中衍生出來的,盡管在12音序列作曲法中沒有了傳統概念的和聲、調性,但我們仍然可以看到與巴赫的復調和貝多芬的主題發展等種種技法的相類似的手法。
《華沙幸存者》運用了一個男聲敘述者、一個男聲合唱團和一個打擊樂組很大的管弦樂隊。全曲只有99小節,按照情緒的起伏和變化,可以分為五個部分。
第一部分(1-11小節):
小號尖利刺耳的聲音模仿著難民營里的起床號聲。小軍鼓急促的敲擊聲、弦樂和木管的顫栗一下子就把聽者帶到了恐怖的戰爭環境巾,小提琴的撥弦引出一個男子沉痛的敘述。
第二部分(11-24小節):
“我的記憶已不完全了!我一定有很長時問失去了知覺……”這敘述是有音調的,但不是很具體,作曲家只用一根線來記譜,圍繞著它,語言本身的韻律被夸張地標以音高。這一段的情緒有很大的起伏,從剛開始的一拍= 80到90、100、112,一小節一次遞增,當敘述者講劍“好象預先安排好了似的,大家一起唱出那古老的、他們這許多年來所忽視了的祈禱--那被遺忘了的信經”時,速度突然變慢,成為一拍=52。勛伯格在這部作品中對速度的運用十分精心,它成為營造情緒的極其有效的因素。在敘述過程巾,樂隊音響和節奏律動的密度也在迅速增加,造成強烈的緊迫感。結束這一段的是拖長了聲調的“在華沙的下水道里呆了這樣長的時問……”。
第二部分(25-53小節):
突然加快速度,為一拍=80(此為整部作品的基本速度,以它為基礎不斷地作出變化)。和開頭一樣的小號聲再次響起:“這一天象平時一樣開始了。天還沒亮,起床號就吹響了。”樂隊音響緊張不安,但當敘述者講到“你的孩子、妻子、父母親都已和你隔離,你根本不知道他們已經遭到了什么,你怎么可能安然熟睡呢”,一條凄婉柔和的旋律由小提琴獨奏出來,這是全曲巾唯一的抒情音響,不由得使人從心底里震顫。小號聲第二次響起,小軍鼓也急促的敲響,木琴、定音鼓心悸一般的節奏伴隨著德國人的吼叫,沖向情緒的高潮。在講到“中士和他的兵士打著每一個人”時,大鈸駭人地響起,十分形象地使人聯想到抽在人們身上的鞭子。在敘述者恐怖的“我們這些被打倒在地上實在站不起來的人,又遭到沒頭沒腦的鞭撻”這句話之后,緊張的情緒再一次松弛和降落下來。
第四部分(54-80小節):
敘述者繼續著:“我半死不活地躺在一邊。周圍死一般地寂靜一充滿r恐懼和痛苫。然后我聽到中士喊道:‘報數!”這一段開始時是語氣遲緩的,但馬上就變得緊張起來,木管的尖叫和弦樂的撥弦、震弓形象地捕繪了納粹的野蠻和難民們心驚肉跳的場面。第二次報數開始了,止如敘述者所講的:“先是緩慢的:一,二,二,四,然后加快,越來越快,快到那聲響有如野馬驚跑,”速度從一拍=60起步,然后迅速遞增:70-80-90-100-110-124-144-160,同時節奏逐步緊湊,音響逐步增強增厚,達到最緊張點。
第五部分(81-99小節):
就在這一片震耳欲聾的聲響中,男聲合唱隊充滿尊嚴地、從容地用猶太語唱起了古老的“信經”。速度突然變為一拍=80,節奏拉寬,雖然喧囂的、逼迫的聲音仍然存在,但仿佛永恒的生命的光芒驅散了鬼魅一般,在這神圣的歌聲中它們顯得那樣委瑣,那樣微不足道。為了加強合唱的力度,勛伯格讓一支長號以同度齊奏歌唱的旋律。在這條悠長的旋律巾,12個音的音列第一次完整地出現,先是在hB這個音高層上的原形,然后在*處由同音降E開始一個倒影音列,在后面還有一次以D音開始的原形以及也是在D音上開始的逆行倒影音列,在此不一一列舉。漸漸地,樂隊也加入到神圣的贊美歌聲巾,越來越強烈,當速度拉寬到一拍=40,全曲壯烈而堅定地結束。
晚年的勛伯格在這部作品巾所噴射出的猶太民族對戰爭罪犯的怒火,對世界和平的熱切期盼,仍然撼人心魄。這不儀是猶太人的心聲,也是全世界熱愛和平、追求自由和平等的人民的心聲。
——評《勛伯格與救贖》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