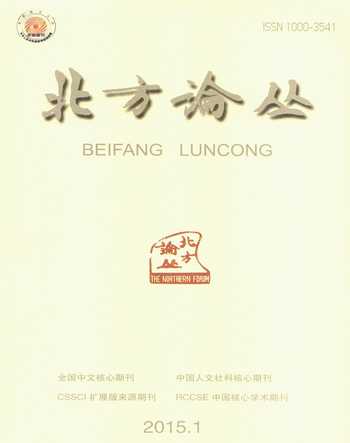《楚辭》“亂曰”探源
徐廣才
[摘 要]《離騷》《招魂》等結尾處的“亂曰”是《楚辭》研究中的一個難題,其含義及得名原因,眾說紛紜。根據《楚辭》自身發展規律及出土文獻材料,“亂”是古代樂歌體制的遺留,指樂歌的最后一章。從訓詁學、古文字學角度看,“亂”有“合樂”之義。樂歌最后一章的演奏形式為合奏,所以樂歌的最后一章可稱為“亂”。
[關鍵詞]楚辭;亂;出土文獻
[中圖分類號]2072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15)01-0058-04
《離騷》《九章》之《涉江》《哀郢》《抽思》《懷沙》,以及《招魂》等結尾處皆以
一段短歌結束,且每一短歌前皆冠以“亂曰”二字。“曰”字較好理解,而“亂”為何義,又因何而得名,學者意見較為分歧。本文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試圖做出新的解釋。
一、“亂”之含義
關于“亂”之含義,傳統上主要有五種說法:
第一,“治理說”。漢儒王逸為《離騷》之“亂”作注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其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敶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后結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洪興祖亦曰:“《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也。《離騷》有亂有重。亂者,總理一賦之終。”[1] (p.47)
第二,“樂之卒章說”。很多學者認為“亂”與音樂有關,指樂曲的最后一章。如李陳玉曰:“凡曲終曰亂。蓋八音競奏,以收眾聲之成。”[2] (p.700)高亨云:“亂,原是用在樂歌上的一個詞匯,一個樂歌的末端叫做亂,等于后代所謂‘尾聲。大概樂歌到了末端,是樂器雜作,大家齊唱,所以叫作亂。”[3] (p.46)
第三,“調合說”。還有一些學者將上引二說結合起來考慮,如游國恩云:“亂為節樂之名,亦有整治之意。”[4] (p.497)
第四,“字誤說”。郭沫若認為,“亂”是“辭”字之誤,“亂曰”即“辭曰”。[5] (p.41)
第五,“通假說”。易重廉認為, “亂”當讀為“申”。 [6] (p.57-60)路百占認為,“亂”當讀為“嘆”。 [7] (p.17)
在上引五種說法中,我們認為,第二種說法較為可信。第一種說法以“理”解“亂”,從訓詁上看是有根據的。《說文·乙部》:“亂,治也。”《書·皋陶謨》:“亂而敬。”孔安國注:“亂,治也。”《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武王有亂臣十人。”杜預注:“亂,治也。”雖然“亂”可解釋為“理”,但這并不意味著《楚辭》中的“亂”就一定要解為“理”。對此,蔣驥曾說過:“舊解‘亂為總理一賦之終。今按《離騷》二十五篇,亂詞六見,惟《懷沙》總申前意,小具一篇結構,可以總理言。《騷經》《招魂》,則引歸本旨;《涉江》《哀郢》,則長言詠嘆;《抽思》則分段敘事,未可一概論也。”[8](p.192)蔣驥結合文本內容,指出楚辭中“亂”的含義的復雜性,因此以“總理一賦之終”解釋楚辭中的“亂”,并不合適。
第三種說法是對第一二兩種說法的調和,似乎較為全面,但正如上文所說,第一種說法是有問題的,因此這種“調和”是不可取的。
郭沫若的“字誤說”也是不可信的。徐嘉瑞就曾對郭說提出質疑,其疑問主要有三點:第一,古書上說到音樂上的“辭”字的,何以都錯為“亂”?第二,《楚辭》中用“辭”的地方很多,何以都不錯為“亂”?而只有“辭曰”之處,都完全誤“辭”為“亂”。第三,《論語》是“始”“亂”相對,《樂記》也是“始”“亂”相對,又是“訓”“亂”相對。假如《論語》的“關雎之亂”,是辭誤為亂,那么“師摯之始,關雎之辭”怎么講得通呢?[9] (pp.74-79)徐氏的這些疑問切中要害,是郭氏無法解釋的。因此,郭沫若的說法并不可信。
易重廉、路百占等提出的“通假說”亦不可信。易重廉根據部分古文字學者的意見,認為出土蔡國銅器上蔡侯“申”的“申”字,銘文字形原作“亂”,通為“申”,因此,《楚辭》中的“亂”也當通為“申”。實際上,銘文中表示“申”的那個字形與亂字無關,此字應從裘錫圭說,釋為“紳”。 [10] (p p .418-428)路百占從六個方面證明“亂”當讀為“嘆”,其主要證據是難與亂相通,而難、嘆又可通,故亂與嘆可通。路文舉出亂與難相通的證據,是《列子·說符篇》“民果作難”《釋文》引難一作亂。實際上,正如作者自己指出的,“難、亂誼相應,難即亂也。”難、亂之間的關系,不是通假,而是義近。難、嘆、亂雖古皆為元部韻,但我們尚未見到它們相通的例證。因此,“通假說”也不可信。
我們認為,第二種說法較為可信。何劍熏曾說過,亂“乃音樂上之專有名詞,以通常義釋之,不妥”, [11] (p.321)實際上已經指出了解決問題的途徑。因此,我們在探討 “亂”的含義時,當把它與樂歌結合起來考慮。我們知道,《楚辭》是在楚地樂歌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獨具特色的楚聲楚歌,是《楚辭》的直接來源,故而《楚辭》的發展與樂歌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王國維《人間詞話》云:“《楚辭》之體,非屈原所創也……《滄浪》《鳳兮》二歌,已開《楚辭》體格。”[12] (p.37)李炳海說:“楚辭是從詩與歌相雜的綜合藝術中孕育生成的,因此,早期楚辭,亦即出自屈原之手的作品,或多或少地還保留歌詩的特點,具有它所脫胎的母體的痕跡。”[13] (pp.97-102)樂歌對《楚辭》的影響,一方面是,有些《楚辭》作品還能夠配樂演唱,如祭祀神靈的《九歌》;另一方面是,有些作品雖不能演唱,但樂歌的一些形式還保留著,如樂歌卒章的“亂”。對此,金開誠曾說過:“古時詩為樂歌,其末章之‘亂,僅指所配樂舞而言,與詩句文意并無關系。至于其后世出現的大篇辭賦,則顯已不能入樂,只具‘倡、‘亂等形式,仍是樂歌遺意。”[14] (pp.180-181)屈原的許多作品襲用這個術語,正表明了早期楚辭與音的樂密切關系。
亂為樂歌的一部分,以往學者多根據《論語》《禮記·樂記》中的一些記載予以闡發。現在我們更有了出土文獻上的證據。2008年清華大學入藏了一批戰國竹簡,其中有一篇自名為《周公之琴舞》,該篇共17支簡,簡背有編號。全篇十首詩,首列周公詩,只有四句,接下來是成王所作完整九篇頌詩,下面我們引其中的前兩首為例:
元內(入)啟曰:敬之敬之,天惟顯帀(師),文非易帀(師)。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其事,卑(俾)藍(監)在茲。亂曰:訖(遹)我宿夜不兔(逸),敬之!日就月將,學其光明。弼寺(時)其有肩,示告余顯德之行。
再啟曰:才古之人,夫明思慎,用仇其辟,允不(丕)承其顯,思修亡。亂曰:巳!不曹(造)哉!思型之,思曼紳(申)之,用求其定,裕皮(彼)頤不落,思衒。
這兩首詩在結構上明顯分為兩部分:啟與亂。啟是開始的部分,亂是結尾的部分。李守奎在分析上引第二首詩時說:“此詩以亂為界,前后兩部分截然分明而又文意相貫,前半首意在毖勸其輔臣繼承其先人之光烈,輔弼其君,亂的部分是講國家尚未安定,希望其興盛不落,永有光耀。”[15] (pp.66-76)從該詩結構看,“亂”這一部分并不是對上文的總結,由此也可看出前引王逸等人的說法是不可信的。
李學勤先生指出,《周公之琴舞》的性質是一種樂章。從篇題的“琴”和“舞”可以看出,這九首詩是與樂、舞相配的。由此我們推斷,啟是樂章的開始,亂是樂章的結束。
二、“亂”得名之由
“亂”得名之由,傳統上主要有以下三種說法:
第一, 源于“治理”之義。前引王逸、洪興祖等人認為,“亂”辭為辭賦之終,有總理一賦之作用,其含義正與“亂”字的“治理”之義相近,故可稱之為“亂”。但正如前文所說,“亂”辭并非皆有總理一賦之作用,故此說實不可信。
第二,源于“混亂”之義。吳仁杰說:“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胡文英說:“取未盡之意,不擇次序而并言之,故謂亂。”[2] (pp.700-701)蔣驥曰:“余意亂者,蓋樂之將終,眾音必會,而詩歌之節,亦與相赴,繁音促節,交錯紛亂,故有是名耳。”蔣說影響最大。文懷沙說:“我覺得蔣說亦頗能令人首可,繹文作尾聲,從蔣說亦甚允當。”[16] (p.99)黃仕忠曰:“蔣氏之說,一破拘于文辭之解,并從音樂的角度,進一步指明其音樂上的特點,可謂直入奧里,惜未能舉例列證,故今人猶有以賦與音樂有別而非之。愚以為亂之名實從音樂中來,確為‘眾音必會,而且‘繁音促節,交錯紛亂鐘鼓齊鳴,眾聲皆和。”“簡言之,因眾器并陳,眾聲俱作,‘交錯紛亂,故此得到‘亂這一名稱;又因雜亂中奏出統一的旋律,即雜多中含統一,所以‘亂又有‘理的特點。”[17] (pp.3-20)蔣、黃等能從音樂角度考慮問題,是其合理的地方,但將音樂與紛亂聯系在一起,與古人強調的“樂和”觀念不符,且“眾器并陳,眾聲俱作”并非即“交錯紛亂”,因此,“亂”之得名當與“紛亂”義無關。
第三,源于“音樂結束”之義。周葦風認為,“”有兩個來源,一個是“”,一個是。“亂辭”之“亂”所從的“”來源于后一形體,表示有人以手搖簴,而雙手搖簴,能發出聲音,添一表示停止的偏旁“乙”構成一個會意字“亂”,意思當然是指音樂的結束。因此,“亂”是指終了的樂章,亦即全曲的尾聲[18] (P.155-165)。
周氏之說比較新穎,但實不可信。首先,“”實際上只有一個源頭,這一點,周谷城、[19] (pp.1-6)楊樹達[20] (pp.138-139)等學者早已指出。其次,鐘磬等是通過打擊而不是通過雙手搖簴發聲的。《呂氏春秋·古樂》:“帝嚳乃令人抃,或鼓鼙,擊鍾磬、吹苓、展管篪。”鐘磬為打擊樂器,亦可得到出土材料的證實。1978年,湖北隨州曾侯乙墓出土了戰國初年的一架編鐘和一套石編磬。伴隨編鐘、編磬出土的還有演奏用的撞鐘棒、鐘槌、磬槌。鐘槌用以擊中層和上層鐘,撞鐘棒用以撞擊下層大鐘,經試奏證實,如不用撞鐘棒撞擊,就難以激發整個鐘體的共振,從而得到理想的音響效果[21] (pp.134-151)。第三,簴不是搖的。作為懸掛鐘磬的架子,簴需要穩固,因此其下方有起穩定作用的底座。如曾侯乙墓編鐘底座制成半球體,其主要目的之一當為求穩固。第四,從文字構形看,“亂”字所從的“”也與音樂無關。“”已見于金文,作“”(番生簋)形。郭沫若、[22] (pp.179)楊樹達、彭浩、[23] (pp.18)皆認為“”之本義與治絲有關。驗之于古文字字形, “(亂)”之本義當為治絲,與音樂無關。且清華簡《周公之琴舞》之“亂”字,與“乙”字毫無關系,因此,“亂曰”之“亂”與音樂停止無關。
我們認為,《楚辭》之“亂”既然源于樂歌,就應從樂歌之“亂”入手研究其得名原因。樂歌之“亂”有一個特點,即以合樂方式結束。姜亮夫說:“考‘亂皆在篇末,句韻短促,則亂蓋即樂節之終,所謂合樂是也。他篇或曰‘少歌,或曰‘唱,義例正同。樂將竟,則眾樂眾聲皆作,大合唱以終之。”[24](pp.111-112)蘇雪林曰:“亂本是樂曲終結時合唱。”[25] (p.167)古代合樂的場面是很盛大的。《論語·泰伯》:“《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概括了樂章結尾時的繁華情狀。《九歌》之亂辭《禮魂》:“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正是合樂盛大場面的描寫。
如果知道我們“亂”是卒章,以合樂形式結束的,那么“亂”之得名問題也就容易解決了。古“亂”有合樂之義。上引《論語·泰伯》“關雎之亂”中的“亂”,清代學者多認為是合樂之義。戴望《論語戴氏注》曰:“亂,謂合樂之時。”[26] (pp.711-714)劉寶楠《論語正義》注引劉臺拱《論語駢枝》曰:“合樂謂之亂。”[27] p.85)凌廷堪《禮經釋例》也說:“《關雎》之亂,謂合樂也。”[28] (p.267)結合上下文考慮,合樂之說較為允恰。《大招》:“叩鐘調磬,娛人亂只。”王逸注:“娛,樂也。亂,理也。言美女起舞,叩鐘擊磬。得其節度,則諸樂人各得其理,有條序也。”王夫之曰:“亂,曲終也,歌竟而人娛也。”[29] (p.154)湯炳正認為:“娛人,使人娛樂。亂,樂曲末章。此言最使人娛樂的,是樂曲最后的高潮。”[30] (p.250)王逸以“理”釋“亂”,并不合適。王夫之等將“亂”理解為樂曲之末章,從意義上看,要比訓為“理”合理。但這種說法也有問題。“投詩賦只”、“極聲變只”、“聽歌譔只”皆為動詞性短語,如果將“亂”解釋為“樂之末章”,則為名詞,如這樣,“娛人亂只”這句話就很難理解,大概只能如湯炳正那樣,將其處理為判斷句,但這種解釋又與本節文例不合。因此,“娛人亂只”的含義還需重新考慮。
我們認為,此處的“娛人”是名詞,指歌舞藝人,相當于漢代的樂人。《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歌弦之。”《呂太后本紀》:“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逸解“亂”為“理”雖不確,但能將“娛人”解釋為“諸樂人”,則明顯優于后世學者。
既知“娛人”為樂人,又據本節句意及句式特點,可知“亂”當為與音樂有關的動詞,故黃仕忠認為:“這‘娛人之‘亂是鐘盤齊鳴的。”黃氏將“亂”理解為動詞性短語“鐘盤齊鳴”,是其合理的地方,但不夠全面。據“二八接舞”、“聽歌譔只”,我們認為,此“亂”還應包括諸樂人的合唱合舞。下文“四上競氣,極聲變只”正是眾器齊鳴、眾聲齊唱、眾人齊舞場面的生動描寫。
“亂”有合樂之義,還可從字形上得到證明。古“”有“治”義,亦有“亂”義,同一字形表示“治”、“亂”兩相反義,給表達上帶來了不便。至西周初期,出現了以“”為意符的字,表示“治”及其引申義。而“亂”義則仍由“”字表示,如召伯簋:“余弗敢。”西周晚期,出現了“(毛公鼎)”字,表示“亂”意,該字下面的“止”形為“又”形之訛,該字當由“”和“”兩部分構成,可隸定為。至戰國時期,楚文字材料中,字大量出現,如郭店《唐虞之道》簡28、《尊德義》簡6、簡23、《包山》簡192、《楚帛書》乙、上博楚竹書《孔子詩論》簡22、《容成氏》簡43、《周易》簡42、《亙先》簡8、《弟子問》簡4、《鬼神之明》簡3;字形或省去“爪”,如郭店《尊德義》簡5、上博楚竹書《從政甲》簡2、簡9、《從政乙》簡3、《內豊》簡10、《鮑叔牙與隰朋之諫》簡8;還可省去“又”,如《內豊》簡6、《季庚子問于孔子》簡10、簡22。戰國楚文字材料中的,皆用為“亂”。魏三體石經《無逸》篇亦有字,該字是作為“亂”之古文刻寫上去的。
關于“”字的構形,郭沫若先生說,本像治絲之形,治絲時其聲囂騷,故字復從。季旭升認為:“可能以表示眾口喧亂的意思。” [31] (p.334)《說文·部》:“,眾口也。從四口。讀若戢,又讀若呶。”但徐鍇、桂馥皆認為,“呶”應該是字義。徐鍇《說文解字系傳》:“,一曰呶。臣鍇曰:‘呶,讙也。”[32] (p.42)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呶乃字義,非字音,不當言讀若。”[33] (p.186)據此,,當有二義:眾口;喧鬧。字從,當與眾口或喧鬧有關。因此,郭沫若、季旭升將該字所從之“”與“喧亂”之義聯系在一起,應該是可信的。但是,“”既然有眾口之義,那么“”也應該可以表示“合樂”之義,因為“合樂”與“眾口”皆與“眾”有關,尤其“眾口”與“合唱”之義關系更為密切。所以,我們認為,“”應既可表“喧亂”,亦可表“合樂”,或可以說,“”是為“喧亂”、“合樂”二義而造的字。
亂有合樂之義,應與亂之本義有關。上文已經指出,亂之本義為治絲。彭浩根據文獻及出土材料,對古代治絲的過程做了較為詳細的說明。從彭先生的闡述中,我們知道,在整個治絲過程中,較為突出的一個現象是“聚合”:若干繭絲聚合成一根生絲(繅絲);數根生絲合并成一個粗絲(并絲);若干經線分別聚合為兩束(牽經);兩根單股線合成一股(捻絲)。可以這樣說,所謂的治絲,就是聚絲、合絲。“亂”之合樂之義,當由此義引申而來。
綜上,亂有合樂之義,樂之卒章恰以合樂方式結束,故樂之卒章可稱為“亂”。
[參 考 文 獻]
[1]洪興祖.楚辭補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
[2]崔富章.楚辭集校集釋[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3]陸侃如,高亨,黃孝紓.楚辭選[M].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
[4]游國恩.離騷纂義[M].北京:中華書局,2008.
[5]郭沫若.屈原研究[M].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易重廉.楚辭“亂曰”義釋[J].學術月刊,1983(5).
[7]路百占.為《離騷》“亂曰”進一解[J].許昌師專學報,1990(1).
[8]蔣驥.山帶閣注楚辭[M].北京:中華書局,1998.
[9]徐嘉瑞.楚辭亂曰解[J].文學遺產增刊第1輯,1955.
[10]裘錫圭,李家浩.談曾侯乙墓鐘磬銘文中的幾個字[A].裘錫圭.古文字論集[C].北京,中華書局,1992.
[11]何劍熏.楚辭新詁[M].成都:巴蜀書社,1994.
[12]王國維著,黃霖導讀.人間詞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3]李炳海.楚辭語詞與楚地歌舞的關系[J].文藝研究,2001(5).
[14]金開誠,董洪利,高路明.屈原集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6.
[15]李守奎.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與周頌[J].文物,2012(8).
[16]文懷沙.屈原離騷今繹[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
[17]黃仕忠.和、亂、艷、趨、送與戲曲幫腔合考[A].文獻,1992(2).
[18]周葦風.楚辭“亂曰”新證[A].李國昌,趙昌平.中華文史論叢總第七十六輯[A]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9]周谷城.古史零證[M].新知識出版社,1956.
[20]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全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1]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22]郭沫若.金文叢考[M].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五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
[23]彭浩.楚人的紡織與服飾[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24]姜亮夫.重訂屈原賦校注[A].姜亮夫全集[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25]蘇雪林.楚騷新詁[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26]黃懷信.論語匯校集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7]劉寶楠.論語正義[M].清人注疏十三經.北京:中華書局,1998.
[28]凌廷堪.禮經釋例[M].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9]王夫之.楚辭通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30]湯炳正,等熊良智.楚辭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31]季旭升.說文新證[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32]徐鍇.說文解字系傳[M].北京:中華書局,1987.
[33]桂馥.說文解字義證[M].北京:中華書局,1987.
(作者系哈爾濱師范大學副教授,歷史學博士)
[責任編輯 洪 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