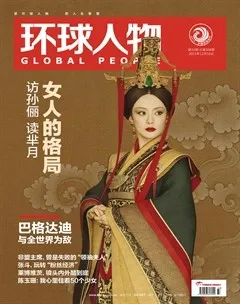朱小棣,靜品閑書 熱話紅塵
人物簡介
朱小棣,生于1958年,海外知名雙語作家,作品有《紅屋三十年》《新狄公案》《閑書閑話》《地老天荒讀書閑》等。

朱小棣是土生土長的南京人,本科畢業后去了美國,學的專業、后來的工作都與寫作無關,卻憑借一手好文筆征服歐美文壇,他的中文隨筆集也陸續在國內出版,可謂墻外開花兩面香。“忙里偷閑讀書寫作,無非性格命運所致。命運沒把我安排在風口浪尖的哨位,個性又讓我不甘寂寞沉淪,便只好以書為伴”。采訪中,他淡淡說道。
不想讓美國讀者誤讀中國
這次回國,朱小棣是為了出版父親的畫傳。他的父親朱啟鑾是一名中共地下黨員,1940年到南京從事情報工作,稱得上是南京秘密戰線的開拓者。解放南京前夕,他曾冒險渡江,親手把長江軍事部署圖送交人民解放軍總前委司令部。
不止是父親,朱小棣的長輩中,為革命打拼的不在少數。他的二叔曾是胡耀邦的部下;三叔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高級步兵學校政委;姑姑和姑父曾是周恩來、郭沫若領導下的敵后抗日演劇隊骨干。
1987年,朱小棣剛到美國,一位華人女士所寫的“文革”回憶錄出版,媒體廣為議論。有一天,朱小棣在報紙上看到一封讀者來信,說這本書好極了,只是尚有一點不明:為何這位資本家太太1949年之后能養尊處優長達17年之久,直到1966年才被抄家?朱小棣一下子明白了,美國讀者并不了解中國的歷史過程,不知道中國革命都有哪些磨難,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出災難的。“如果我把我們家庭的故事寫出來,會有助于西方讀者了解中國”。于是便有了朱小棣的英文處女作:《紅屋三十年》。
這本書寫的是朱小棣出國前30年的經歷和見聞,通過他們一家,尤其是父輩們的生活,展示中國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的歷史。出版后,立刻引起熱議,還入選了“杰出學術圖書”。遠在歐洲的韓素音女士也特意給他寫了封賀信,認為這是“最為全面客觀書寫這一段歷史的書籍”。
挖掘狄仁杰的內心
接下來用英文寫狄仁杰,對朱小棣來說,“是想繼續描繪中國的文化土壤、生存形態”。
20世紀荷蘭漢學家高羅佩曾著有系列偵探小說《大唐狄公案》,被翻譯成多國文字,讓狄仁杰成為“中國的福爾摩斯”。
朱小棣續寫狄仁杰時,也像高羅佩那樣,先去《棠陰比事》等古代典籍里找案例,“一看,才知道大部分好改的案子都被高羅佩寫完了。只有一個涉及字謎的案件,他沒把字謎轉換成英文。我嘗試了幾十遍,終于用英語寫成”。
在朱小棣眼里,高羅佩是學養極深的漢學家,“他能寫舊體詩與于右任等人唱和,豈是我輩能比。寫完后我才發現,他所描繪的服飾,還真是符合沈從文先生的考據,推翻了其他一些學者的結論”。
而從創新上來說,朱小棣覺得自己是“力圖在高羅佩已經成功塑造的狄仁杰身上,挖掘開拓其內心世界”。因此,他著力刻畫狄仁杰的日常生活,以及他與夫人、下屬、同僚、上司的關系。一字一句中,把一位喜食臭豆腐、愛飲茶養性的狄公展現于讀者面前,不正襟危坐,不樹碑立傳。
這本《新狄公案》被翻譯成法文出版后,獲得了法國歷史偵探小說大獎第四名。
文學于我從來不是溫室里的花朵
美國一家出版社曾做過一本名家選集,題為《母親》,只有一名華人入選,她就是《喜福會》的作者譚恩美。后來做續集《父親》時,也只有一位華人入選,就是朱小棣。和他一起入選的作者里,有在美國赫赫有名的約翰·厄普代克、《阿甘正傳》的小說原作者溫斯頓·葛魯姆等24位。
身為華人作家,朱小棣對同行與自己都有很清醒的認識:“譚恩美的小說之所以走紅,恰恰是因為她能夠同時用純正英語(她自己的)和蹩腳英語(她母親的)交織在一起寫作,讀來別有意趣。而哈金(第一個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華人作家,代表作《等待》)能夠得到青睞的一大原因,則是他的英語中機智地保留了許多中文元素,凡是懂中文的人都能夠看出其出處,忍俊不禁,西方讀者則在其曉暢英文中偶遇中文元素,大飽眼福。而我在努力學習英文的同時,一直在努力甩掉中文羈絆,盡管寫成流暢英語,卻再無語言特色可言。這大概也可以算是一種尷尬吧。”
朱小棣沒有書房,至今“蝸居”斗室,臥室內一張小小書桌,他覺得“也足矣”。
哈佛大學的圖書館算得上是他的書房。他看書口味獨特,喜歡冷僻的,很少碰風口浪尖上的暢銷書。他曾說自己與中國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天才散文作家梁遇春很相投:“年輕時最讓我動心的一面,是他懶得上課,懶得起床。他說自己腦子里所有那些聰明的想頭、靈活的意思,多半是早上懶洋洋地賴在床上想出來的。”這種閑適散淡,成了朱小棣讀書時的一貫風格。但同時,他也會像魯迅先生說的那樣,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都用來寫作。《閑書閑話》《閑讀近乎勇》等一系列以“閑”命名的隨筆集,就是他近年來的成就。

朱小棣說:“寫作本身,往往是在喃喃自語。每句話都是一邊在心里念,一邊用手敲擊鍵盤寫出來。”
在海外漂泊多年的朱小棣,說他的寫作,“并非想用獨特的東方故事融入美國社會,而是因為有些難以融入,所以希望讓美國人了解中國。我本來也未必有多少鄉愁,父母均已過世。讀書寫作,反倒勾起幾多對故鄉的思念”。
無論是自傳、小說還是隨筆,無論是用英語還是中文,朱小棣的寫作肯定都并非單純的文學嘗試,而是寫文化、寫中國。正如他自己所說:“從兒時看魯迅起,文學于我就從來不是溫室里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