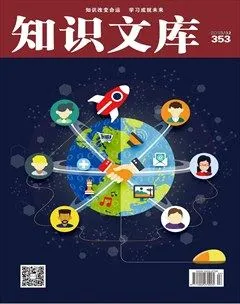清代河南生態環境的保護與改造
在清代,人們已經比較深刻的認識到森林植被遭破壞,水利失修所帶來的水土流失、沙堿、旱澇等一系列惡果。為改善生態環境,他們在植樹造林、興修水利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對河南生態環境的保護與改善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歷史條件限制和人們對生態環境保護認識的局限性,河南生態環境總體上仍朝著惡化的方向演進。
一、清代人們的生態環境意識
在古代,雖然由于時代的局限性,人們并未能提出明確的環境保護問題,但是對自然界的認識是在實踐中逐漸深化的,有些認識已經和現代非常接近。對于在山區持續的破壞森林、耕墾山坡,使生態環境日益惡化,從而造成水土流失、災害頻繁及其對農業生產的危害,人們早就有相當程度的認識。《漢書·禹貢傳》中說,“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以上”,“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云,斬伐林木亡有禁時,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此也。”明神宗萬歷年間,寧陵呂坤在談到山地開發存在的問題時說:“貧民砍荒山,斫古嶺,雖有三五畝新開之地,然石根土薄,旱則先枯,澇則雨沖,一時雖有青苗,久后仍成廢棄。”[1]
清代山墾的大發展,森林的亂砍濫伐,林木破壞所造成的惡果明顯多于前代。特別是一些愚昧貪婪之輩和迫于生存壓力入山的流民、棚民大肆破壞天然林,造成生態環境失衡,使當時一些有識之士對此生態環境破壞的后果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在《人口》中寫道“不數年間群山盡赭。…… 山木既盡,無以縮水,溪源漸涸,田里多荒”。在清代徽州的《驅除棚害記碑》中,有人對森林的破壞后童山濯濯、水源枯竭、河道淤塞及其引起的林木匱乏、災荒饑饉、糧價上漲等三個方面加以分析:“伐茂林,挖根株,山成濯濯,萌蘗不生,樵采無地,為害一也;山賴樹木為蔭,蔭去則雨露無滋,泥土枯稿,蒙泉易竭。雖時非亢早,而源涸流微,不足以資灌溉,以至頻年歲比不登,民苦饑謹,為害二也;山遭鋤挖,泥土松浮,遇雨傾瀉,淤塞河道。水運艱辛,米價騰貴,為害三也。”清人梅亮在《書棚民事》中記述他在安徽宣城調查鄉人后了解到開山墾荒前后的截然不同的情況:“皆言未開之山,土石堅固,草樹茂密,腐葉積數年可二、三寸。每天雨,從樹至葉,從葉至土石,歷石罅,滴滴成泉。其下水也緩,又水下而土石不隨其下。水緩,故低田受之不為災,而半月不雨,高田猶受其灌溉。今以斧斤童其山,而以鋤犁疏其土,一雨未畢,沙石俱下,奔流注壑澗中,皆填污不可貯水,畢至洼田中乃止;及洼田竭而山田之水無繼者。是為開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利無稅之傭而瘠有稅之戶也。”[2]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當時許多普通百姓已經認識到森林具有含蓄水源、保持水土、防止旱澇的功效,并且意識到山林被開墾后,水土流失嚴重、農田易旱易澇的不良后果。清人魯士驥在《備荒管見》中說:“凡田地之肥瘠,視山原之美惡,若其山多草木,郁積磅礴,其泉流必厚,而田受其滋。否則春秋多驟雨,沙石隨之而下,田雖本肥,受害既深,亦從而癮矣”。在河南這樣的認識同樣存在,如道光《舞陽縣志》指出:“先時林密土厚,遇雨即可消納,今樵采者眾,掘及根亥,以致土松,隨流而下,河身上源,盡被淤淺。”[3]咸豐五年(1855年),鞏縣核桃園鄉五指嶺人刻石立碑陳述濫采亂伐林木的后果:“平定寺官坡,林麓薈蔚,昔日固嘗美焉。但伐不以時,則山雖猶是,而今與昔異焉。何也?根宜養也,而人偏斬其根,木宜植也,而今輒拔其本。”[4]這些分析都抓住了問題的實質。
人們不僅對破壞森林的后果有了深刻的認識是,而且闡明了植樹造林、保護森林的生態效益。康熙年間,河南按察司僉事俞森撰《種樹說》提出種樹有八利:“一畝之地樹谷得二石止矣,一畝之地而樹木且十百計矣,十百之所入不數十石乎?其利一也;歲有水旱,菽麥易傷,榛栗棘柿不俱傷也,年豐而販易,歲兇則療饑,其利二也;貧人無薪,至拾鳥糞掘草根,種樹則落其實,而取其材,何憂無樵蘇之具,其利三也;造屋無木,以土墼為屋基,上覆草泥以避風雨,天雨稍久,比屋皆頹,率多露處,種樹則上之可以建樓,居下亦不致同土偶,其利四也;樹少則無器具,生無以為日用,死無以為棺槨,種樹則材木不可勝用,其利五也;豫土不堅,瀕河善潰,轉徙數里習以為常,若沿河栽柳,列樹成行,修竹茂材所在都是,則根株糾結已無隙地,堤根牢固,何處可沖,其利六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三代之時齊魯三晉之區無處不有也,故宅不毛者有里布,今皆移之吳越,余觀汴梁四野之桑,高大之若吳越遠不逮也,若比戶皆桑,大講蠶務,可兼吳越之利,復三古之風,其利七也;五行之用不克不生,今兩河南北樹木稀少,木不克土,土性輕揚,盡成沙礫,人物粗猛,日遠雅訓,若樹木繁多,則土不飛騰,人還秀飭,其利八也。”[5]這段話已經從經濟效益、防止災荒、固堤防沖、防塵固沙等方面對植樹造林將會產生的生態效益進行了詳細闡述。對于植樹造林、保護森林的好處,雍正時,河南巡撫田文鏡也曾著重指出:“多植桑棗,令其繁衍,俟其根深蒂固,可以堅土,枝多葉茂,可以蔽風。庶幾沙土凝結,以免隨風輕揚,尚堪耕種。”[6]清人魯士驥曾專門針對河南的情況說:“必也使民樵采以時,而廣畜巨木,郁為茂林,則上承雨露,下滋泉脈,雨潦時降,甘泉奔注,而田以肥美矣。”[7]其它從散見于當時各地方志中眾多的記載可以得到證明,如嵩縣人提出:“種草栽樹,可以固堤,可以制水。”[8]“凡山皆可封殖,栽松種竹,土石自固,利益自眾”。[9]此外,人們還認識到種草可以保持水土,“采草子,乘春初稍鋤,處處密種,俟其暢茂,雖雨淋不能刷土矣”。[10]
上述事例說明清代人們不僅認識到了森林涵養水源、保持水土和減輕災害的作用,而且還較全面地認識到森林具有凈化空氣、調節氣候的美化環境的功能。科學地闡明了水土與森林植被之間互相依賴、互利互存的辨證關系,與我們今天的科學知識不謀而合。類似的認識在一些護林碑上也有表現。咸豐年間,內黃人將“飛沙流行,田園荒蕪,五谷不生”的認識,刻石樹碑。這樣的認識在當時是比較進步的,即使在今天依然具有其指導意義。
二、植樹造林
河南境內的植樹造林活動歷史悠久,最遲在漢代就已經有造林活動。到了清代,清政府和一些地方官員繼續提倡和開展植樹造林活動。雍正皇帝就曾經飭令地方官勸督民眾在舍旁、田畔以及荒山不可耕種之處,“量度土宜,種植樹木,桑柘可以飼蠶,棗栗可以佐食,柏桐可以資用,即榛楛雜木,亦可以供炊爨,其令有司督率指畵課令種植”。為防止地方政府官員因植樹關系政績考評對百姓勒逼過嚴,而出現擾民的問題。雍正五年,朝廷要求各地方官必須“詳論勸導,令其鼓舞從事”,“不得繩之以法”。應該“切加曉諭,不時勸課,使小民踴躍興作”。[11]若地方官員怠忽不加勸導,或勒逼過嚴者,著學臣稽查奏報。從康熙到乾隆年間,在河南任職的官員都十分注意這項工作,并且付諸行動。俞森提出:“戶無分上下,一家種棗三十株,柿三十株,榆柳各百株,能逾格多種及廣栽雜樹者旌之,不如令者,罰無赦。”[12]河南巡撫田文鏡、尹會一等也都制定-規章和辦法,“飭地方官責成鄉地老農,多方勸諭,自桑柘榆柳,以至棗梨桃杏之屬,遇有閑隙之地不可種谷者,各就土性所宜,隨處栽植,加意培養”,[13]以推進植樹造林的發展。如乾隆二年(1737年)調任河南巡撫的尹會一提出:水利失修,“旱澇無備,全賴天時”,農田糞少,耕作不細,鹽堿沙地多,而且大半荒廢是當時河南經濟存在的其中的三個問題。因而他要求各地居民要根據當地不同情況,選擇樹種,種水田,植五谷;號召農民在田邊、村頭、屋角、溝邊多種樹木,規定凡能在一年內勸民種桑500株,梨、棗、雜樹1 000棵者,給予獎勵。這些措施施行的結果,使河南農業生產得到恢復和發展,全省種樹成活近200萬株。[14]鑒于黃河大堤土質疏松多沙,易被沖刷而決口泛濫,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河南巡撫李世杰奏疏:本省引河新筑南堤應該及時種柳,以資保護。沿堤岸每間5尺種一株,共163000余株。同年10月,清廷命令于黃河沿堤植柳,并嚴禁在近堤段取土以保護大堤和柳樹。
晚清時期,因社會動蕩、災害頻發,各地樹木被毀甚多,以致饑荒連年不斷。一些朝廷官員分析了這種形勢,提出了發展林業的建議。如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御史華輝上奏折指出:“……民力有所不足,必須官為補助者,可分為二大端:一曰廣種植,一曰興水利。……自兵焚以來,各省樹木芟伐殆盡,地之腴者忽瘠,民之富者忽貧。蓋果品材木足以供生人食用者,其利視五谷為尤豐。所謂一年之計樹谷,十年之計樹木也。乃上下因循,不知栽培愛護,往往山童壤赤,一望荒涼,小民亦菜色流離,無復承平景象。則官吏之玩視民虞也亦己久矣。夫種植之大利,……其在北方者二:曰蒲萄,曰棉花。……此四事者,辦有成效,立可行銷外洋,自收利權… …天下無論何土,必有相宜之處;無論何樹,必有可收之利。此則南北各省皆有之,皆宜之。”為此他建議定一勸民種植之法:“民間有能于舊有樹木外種樹至五萬株十萬株以上者,官為酌給獎賞以示鼓勵。”并請定一戕害樹木之禁,“有無故戕害樹木一株者,貧民罰種兩株,富民罰種錢千文以充公用。”[15]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重臣張之洞在給光緒帝的奏折中說:“查各省高山,無論多土多石,皆能種樹,真系不毛者甚少,故歐美各國從無無樹之童山。而考課林木之實在有效與否,尤為顯易。此事宜責成州縣,由總局委員依限往查,其山上有無樹木,一覽而知,不能掩飾。如此則山地之利開矣。”[16]上述分析和建議雖然并不是專門針對河南的,但同樣適用于河南造林事業的發展。
鑒于河南林木破壞嚴重、諸山皆童的問題,河南地方官員努力倡導因地制宜、植樹造林。但是造林面積,因缺乏記載,今天已很難得出全面而又具體的數字,我們只能從一些方志的零散記載中了解到一點情況。光緒三十年(1904年)河南省撫院命各州各縣種樹,寶豐縣栽樹2萬株,中牟縣植樹3.3萬株。商水、中牟、正陽、武陟等縣成立農林會、樹藝公司,由群眾集資造林。是年,正陽縣始有官辦苗圃,育桑、椿苗木供鄉民種植。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正陽縣官籌經費,令地方士紳辦理育苗種樹;滑縣北滹沱、北關、劉莊等8村,為加強對風沙環境的治理,自動建立治沙會,號召民眾植樹造林,制定護林防沙協約,銘石以昭后世。清代豫北沙區也曾有民間組織集資借債造林育林。從這些情形看,晚清時期河南造林仍然是以官方督促,民間集資自發造林為主,而且由于政治腐敗、經費無著,造林事業的發展十分薄弱。
從造林的方式看,河南省平原區一般實行農林間作的方式造林,據楊海蛟研究,清道光三年(1823年)歸德府寧陵縣后趙村開始實行白蠟條與農間作,株距0.6m,行距7-15m ,以后栽植面積逐漸擴大。此外滎陽、博愛的農柿間作,偃師、鞏縣的箭桿楊與農間作,蘭陽、儀封、考城、柘城的農桐、杞柳間作,開封的農柳、檉柳、杞柳間作,都具有較長的歷史。從造林的目的看,在豫東、豫北沙區,人們主要營造農田防護林。農民用以抗御風沙對農田的危害。清末宣統年間(1910年)把可供墾種的沙荒地劃分為輕沙、平沙、重沙3等,各州縣墾種面積多的2600多hm2,少的也有130-200hm2。農民在耕地周圍栽植柳、小葉楊、白臘、杞柳等各種樹木,既可防沙護田, 又能取得用材。但由于這種護田林植樹多為單行,網格面積不足1-2hm2,規模較小,防護效益和經濟效益較低。[17]
在保護樹林方面,河南官方、民間均制訂了一些措施。雍正年間,巡撫田文鏡為保護林木,在基層擇立保約一名,專司巡察。“如有仍恃強剪伐及乘間竊取者,即行報官,按法重處。”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省布政使布告規定“樵采者不得損傷樹身,踐踏者即予罰令賠補。”這里將保護林木的職能納入基層行政管理系統,運用官方力量來保護林木。晚清時期,河南民間還以刻碑立約的方式來自發護林。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陽武縣趙、劉等5個杏蘭村自發集資造林,立碑載有罰規“扳校罰錢一千,鐮殺斧砍罰錢三千。”咸豐元年,溫縣高亢村民相約刻石立碑,提出沁河堤上“所長樹木草薪,根深可保無虞,公議禁斷,不許損樹剎草,不服,稟官究治”。[18]咸豐五年(1855年),鞏縣核桃園鄉五指嶺公議斷坡碑,刻有“草木之植皆緣人為盛衰,養其根則實遂,傷其本則枝亡,公議立一罰規,以勒貞石,使后之人,不敢私意妄取”[19]的文字。同治年間,位于黃河故道的延津縣石婆堌一帶,經常遭受風沙危害,群眾曾組織斷沙會、柳會,造林后封禁起來,以利林草生長固定流沙,又能培育用材。
清代,豫北沙區盛行植柳用以防風固沙。但因營造防風固沙林多為民間自發組織, 或一家一戶小規模經營,防護能力很薄弱,加以政府不重視,常常時造時毀,流沙始終沒有得到控制。延津縣小衛村保存一塊“森林會碑”記述了這種深刻教訓。同治九年(1870年),該村民曾自發組織“森林會”造林護林,農林均有收益。后來人心渙散,會散林毀,風沙較前更甚,全村糊口無資者十有八九。所以不得不于清宣統三年(1911年)復訂會章,重新開始造林。
總的看來,清代河南在林木的保護方面雖然官方和民間都曾經做過一定的努力,但是這些努力并不是一貫的,并沒有形成一種長效機制。限于當時的歷史條件和認識,官方始終沒有設立專門的護林機構,而且除少數的官員比較重視之外,大多數官員則是無所作為。民間則多系自發行為,力量微弱。故護林效果并不明顯,毀林行為難以真正得到遏制。造林方面自然也存在這方面的問題,這也是清代成為河南森林面積歷史上減少比較快的時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修治河渠
(一)清代前期的河渠修治
清前期河南河渠淤塞嚴重易肇水災,而河渠的通暢與否,于灌溉排澇關系甚大,其對農業生態環境影響十分明顯。河渠壅塞,則旱時水流細微,不能進行灌溉;澇時水流四溢,平地行舟,田園莊稼盡遭淹毀,所以歷代盛世時期封建統治者無不重視河渠治理,大興水利建設。但是由于河南境內河流含沙量大,人工治理開挖的技術落后,修治標準低,河渠旋治旋塞的現象非常普遍。清代前期,河南境內的河渠淤塞相當嚴重,以至于水旱災害頻繁發生。乾隆二年(1737年)乾隆帝曾發布上諭說:“朕聞河南省之葉縣、西平、遂平、襄城、郾城等縣,今年皆遭水患,蓋緣河南地土平衍,河流不能盈尺,雖有去地二三丈者,究竟與地勢相平之處居多,且向來渠道率多淤墊,是以一遇山水驟發,不能宣廬舍田禾,盡遭淹漫。”[20]乾隆四年,再次發布上諭說:“今年六月豫省地方大雨如注,川澤交盈,分洩不及,開封等屬被水之州縣甚多。……豫省地方有淮、潁、汝、蔡諸水經緯其間,凡舊有河道,皆達江湖。第因故道被淹,無支河導引,是以水無容納之區,勢必旁溢。下有壅塞之處,澇即難消”。[21]在兩年的時間里,專門針對河南境內的河流發布兩次上諭,既反映了乾隆皇帝對修治河渠的重視,也反映出當時豫境河渠淤塞嚴重,極大的危害農業生產。乾隆朝河南巡撫陳宏謀在《請開歸德水利疏》中指出,“豫省歸德一府,……舊有之河日漸淺窄,每遇夏秋雨水略多,河不能容,水漫平地,即成水災。歷考從前自乾隆四年至今乾隆十六年,計十三年之中,歸郡九州、縣成災者八年,歉收者三年,中等有收者僅一年,幾于無地不災,無歲不賑”[22]。由此也可以看出當時修治河渠的緊迫性。
為使河渠通暢,減少水旱災害給農業生產造成的損害,清代前期河南歷任巡撫及各州縣官員大都比較重視轄區內的河渠修治。修治河渠主要途徑有官修、民修兩種,根據工程量的大小、投資的多寡和受益范圍的大小而定。一般來說,工程量較大、投資巨大的一般有官府投資,組織民眾疏浚開挖;工程量不大、受益范圍較小的溝渠一般由州縣鄉村基層官員或士紳組織附近民眾自行舉辦。清代前期,國內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政府有比較充裕的財力進行此項工作,因此河南境內的河渠修治處于大力推進的時期。清代前期對河渠的修治主要集中在康熙至乾隆年間。如汝寧府上蔡縣“素多水患”,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以后,在知縣楊廷望的率領下,于農隙之時,“成大小溝澮百一十道”。西平縣因地勢低下,形若釜底,遇雨時山洪暴發,泛濫時不可收拾,以至于農民長久難以安耕,多逃散于他鄉,“故野多不耕之士”。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后,在知縣李植的組織下,經過數年努力,修挖溝渠83條,大大改善了當地農業生產的條件[23]。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楊汝揖任固始縣知縣后,對固始縣境內山川進行勘查,搜集資料。經過三年的實地調查,撰寫了固始縣《水利圖說》四卷,對鏡內的大小河流逐條提出了治理意見,制訂了實施方案和投資政策。在他的努力組織下,在縣境內疏浚溝河,筑壩建閘,大力發展灌溉、防洪事業。除整治恢復清河、堪河兩個灌區外,還在史河下游興建柳河灌區,在灌河下游興建曲河上下壩灌區,在白露河下游建興龍灌區,在羊行河與急流澗河上興建古城壩和千公堰灌區。在淮河右岸三河尖至張墓坎子興筑了防洪大堤,使固始水利灌溉工程得到極大發展。故在《河南通志》中有“固始水利甲冠中州”的記載。康熙四十五年,河南巡撫汪灝請開賈魯河北通黃河,在兩頭堤根建閘壩,可使賈魯舟楫由黃入洛,同時有利于兩岸地區的排澇灌溉。疏浚挖深自滎陽至沈丘間數百里長的河道,歷經三載完工,對提高賈魯河的防洪排澇、通航能力,促使歷史名鎮朱仙鎮的進一步繁榮起到了重要作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商水知縣疏治汾河,由龍勝溝到項城長百余里。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禹州開浚焦寨至三管冢渠道,引穎水灌田。
雍正二年至八年(1724-1730年)河南各府州縣大興水利工程建設。雍正二年(1724年)河南彰德知府李渭為發展當地的灌溉事業,組織百姓疏浚萬金渠,增開支渠,建閘啟閉,定各村分日用水。雍正五年(1727年),豫東太康、淮陽等州縣疏浚河道,太康之舊黃河、燕城河,淮陽蔡河、瀖河、枯河、狼兒溝、黃河故道、里外溝河等,歷經數年疏浚完工。雍正六年,彰德府組織疏浚安陽等縣各泉源。衛輝府輝縣在百泉池南,建設斗門,筑堰建閘,并疏各泉,以資灌溉。獲嘉縣開挖丹河,河內縣于上秦渠進水口門改建石閘,并疏通東西民渠,建小涵洞。南陽縣修建了河唐渠十二里屯渠、三十里屯渠等河渠數十條等。鎮平縣在雍正五年共開挖長1-10里、寬3-8尺、深1-5尺,專門用于灌溉農田的溝渠79條,幾乎村村之間都有小型溝渠相連,形成了全縣范圍內的農田灌溉系統。[24]汝寧全府在雍正五年至七年共修建6尺深、5尺寬的溝渠一百多條。[25]雍正八年,陳州、許州的許多溝洫也紛紛修通,使吠畎澮陂澤各有所歸,既有利于灌田,又能夠排澇。豫西河南府以洛陽為中心的灌溉系統歷史上比較發達,清前期地方政府先后疏通永清渠等古水道,連接伊水、洛水,使數千頃之地得以灌溉。豫北懷慶府濟源、河內、孟縣、溫縣、武陸等縣,都利用黃河、沁水、丹河完成了河渠農田灌溉配套工程。
乾隆時期,河南修治河渠的活動得到了更大規模的開展。
首先,朝廷為推進河南河渠的治理,制訂了對地方官的獎懲措施。對于治水有功人員予以記功褒揚,對于忽視治河而導致水災發生,徇私舞弊侵吞工程款者視情況給予罰俸、降級、革職、治罪的處理。如乾隆二年(1737年),清廷議準:“嗣后豫省應修水利地方,如有工程重大動用帑項修筑者,承修各員果能實力辦理,修筑堅固,錢糧并無費,俟工程完竣,保固三年之后,令該督撫將該咒功績,核實造冊,題請交部分別議敘,專轄監修統轄督修之咒,果能督率有方,各屬內毫無怠忽。照河工秋汛平穩之例,量加議敘,至承修之員,如有膜視悠忽,不先期修筑,一遇水發,即致田畝被淹者,照河工堤岸豫先不行修筑例,降一級調用。專轄監修之員,罰俸一年。統轄督修之員,罰俸六個月。倘有虛冒錢糧侵蝕入,已以致工程不堅者將承修之員,照侵欺河工錢糧例,嚴參革職治罪。該管各官徇隱不報,照徇庇例,降三級調用。”[26]
其次,針對當時治河存在的因各地行政管轄權的分割及各上下游的利害關系而造成的上疏下堵,以致功敗垂成的問題。乾隆四年(1739年),乾隆帝發布上諭說:“聞現在撫臣檄令各屬勘估興修。但愚民無知,上游方事疏浚,而下游填實阻隔,仍致水無去路。于事何益,著細心熟籌,專委管理河道明晰水利之大員,親勘全局,通盤計算,務使一概疏浚深通。毋令各分疆界,稍有阻滯。再豫省之賈魯河,原有江南地方全注入,是廬鳳等處,即豫省之下游也。……從來疏浚河道時,上游十分用力,下游百計阻撓,各處人情如此,不獨豫省為然。是在封疆大吏洞悉其弊,毋為所欺,庶幾原委暢流,水無泛溢之患”。[27]
第三、較大工程由巡撫籌劃,上奏朝廷批準撥款實施;較小工程則有各州縣官制定計劃,勸用組織當地民力自費修治。
第四,為防止已修治的河渠因水過沙停、仍舊於淺,以致前功盡棄,乾隆年間,河南巡撫蔣炳向朝廷上奏提出了四條水利善后事宜,其中兩條是關于如何使河渠保持順暢的。一是要求已開各河,要歲加修浚,以防復淤。各地方官務要及時查勘組織修治。二是河灘地禁栽蘆葦、蒲草,禁止壘筑土埂捕魚,以利水道暢通。當時,低洼積水之處及河灘處,“所不能樹藝五谷者,民間豪強之家多栽蘆葦、蒲草于河身於淺處,間筑土埂以捕魚蝦。雖水濱自然之利,但因此小利,多致阻水不能迅速暢流,反為上游之害”。故要求各地方官應三令五申,嚴禁在新開河身之處栽種蘆葦、蒲草和筑埂捕魚。并且要于每年三至五月專門派人清查兩次,“違者即行懲處,仍勒令開挖凈盡,以期保護河渠不致淤阻”。[28]
從前述情況可知,乾隆一朝對治河極為重視,治河工程舉辦次數和修治河渠的數量非常多,對減少洪澇災害起了重要的作用,極大的改善了河南農業生態環境。但是乾隆末年至鴉片戰爭前夕,隨著清王朝的衰落,貪污腐化現象盛行,財政日見困難,河南境內河渠修治活動也逐漸減少,這一時期見于記載的河渠工程較少。如嘉慶四年(1799年),禹州引柳林南沙河水灌陳崗田百余畝,北岸引涌水曰龍泉渠,灌田430畝。道光七年至十年(1828-1837年),疏浚滎澤縣索須河,疏通湯河入衛故道,南陽府城東南白河,筑碎石磨盤壩三道。淅川丹江東岸,筑碎石磨盤壩十道,又修筑沁河兩岸堤工八十四段。[29]這些治河活動規模小,成效不顯著。
(二)晚清時期的河渠修治
晚清時期,清王朝的統治更加腐朽,外部西方列強的侵略不斷加深,內有持續多年的農民大起義。清政府對外抵抗侵略,對內鎮壓農民起義,都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財力。更嚴重的是每次抵抗侵略失敗后,不僅大片領土主權喪失,還要支付巨額的戰爭賠款。內外交困的形勢使得清政府的財政狀況捉肘見襟,只有拼命地搜刮百姓,竭澤而漁。而這樣做的結果造成人民更加貧困,整個社會陷于國困民窮的境地。國家和地方民間均無精力和能力進行大規模的河渠修治。不過在如此困難的形勢下,河南的河渠修治工作仍然有所建樹。
賈魯河的三次修治。賈魯河因元末治河名臣賈魯曾修治而得名,清代前期曾多次修治。道光二十一年河決祥符、二十三年河決中牟后,賈魯河被淤塞成了平陸,附近地區一遇大雨,洼地積水無法宣泄,形成澇災,而一遇干旱,則形似荒漠。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地方當局征集民工挑浚賈魯河,但因黃水的淤積形成的沙荒地面積很大,挖出河段很快就被飛沙吹積淤墊。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只能將中牟至朱仙鎮一段改道辛莊寨入祥符境,再由毛井走五里堡南大李莊迤東,然后由朱仙鎮之西繞鎮南,勉強挑浚成河,但是不久又淤塞。同治十一年(1872年),河南巡撫錢鼎銘在省城設立水利總局,興辦水利。是年投資官銀5萬余兩,再次挑浚沙淤多年的賈魯河,南自周家口,北至朱仙鎮,西北至鄭州京水寨,疏積沙,補殘堤,取得了比較明顯的效果。不僅“俾上游無水澇,下游通舟楫”,并對灌溉沿岸農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光緒八年(1882年),賈魯河復淤淺,清廷諭準于朱仙鎮西八里之王堂,挑挖新河,第三次進行了修治。
惠濟河的疏治。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河決祥符后,水退沙留,賈魯河和惠濟河於廢,開封城外地勢益高,城內雨水無法排出,積數十載,“塘泊皆滿,水出地上”,壞官私廬舍以千計。于同治七年(1868年),河南巡撫李鶴年籌劃疏浚惠濟河,十月動工,次年三月工竣。計用官銀42 379兩有奇。浚修后的惠濟河凡長55340余丈,深丈有5尺至8尺,廣12丈至8丈。后又經續治,結果城中“水溢暢出”,而且同治九年夏,城西、城南均苦潦,而城中安然,城東五州縣亦幸免水患。
其他修治活動。道光二十九年在武陟縣令主持下,挑浚廣濟渠,但不久復淤。同治五年(1866年)商水知縣疏治汾河由三里橋到馬家橋55公里。同治六年(1867年)疏浚夏邑境內響河,與永城毗連之朱家橋,入巴溝河,又由巴溝河南岸東大橋之下,開濉河口門,至杜家營,另開挖新渠入白洋溝以資宣洩。同治十一年(1872年)至同治十二年七月,在河南巡撫錢鼎銘的主持籌劃下,除疏治賈魯河之外,還挑浚了淇縣勺金河、固始清河、中牟丈八溝、孟縣余洛河,其余各縣在官府的督導下,亦頗積極,卓有成效。[30]此外,為擴大水稻種植面積,光緒年間河南巡撫裕長飭令各州縣勸興水利。豫西魯山、洛陽、宜陽、新安、永寧(今洛寧縣)、澠池等縣均已新開水渠,有一縣增至20余道者。豫北修武、新鄉等縣,使擇地掘井,每縣至20余口之多。武陟縣,“鑿井灌田,縣西幾遍,縣東亦以滋多”,還在沁河上設置開啟閘門四五個以資灌溉。豫東鹿邑縣知縣在境內組織民力,督浚溝渠10道。其中,新安縣自光緒五年后,用以工代賑之法,修挖溝渠17條,超過此前四五十年修渠總數的數倍。[31]另據《清史稿·列傳》記載:光緒四年(1878年)丁戊奇荒時,全福曾攜籌集到的四十余萬金“至河南分賑洛陽等十二州縣,在重災區新安、澠池,開渠澗,制龍骨車,興水利。又浚洛陽、宜陽廢渠,貫通伊、洛,灌田兩萬頃。”
和清代前期類似,晚清時期清政府對河南省內的河渠治理及保護的辦法也曾做出了一些規定。如光緒八年,清廷諭準:河南省河渠,按照村莊設立渠長,如有淤墊殘缺責令隨時報官集夫督修。河南地畝向無田間水道,應就地形較洼之處,開橫直溝渠。州縣官于農閑時,督令開挖橋閘涵洞,責令渠長經管,報官修筑。河邊種葦及設籪捕魚有妨水路者,率渠長查禁。盜挖堤缺洩水者,嚴拿重究。又奏準:歸德府屬巴溝、洪溝二河,每歲十月農閑,由江南、河南二省,各派道府大員會勘,如有淤墊,即督率本地民夫照界挑修,倘犬牙相錯,有須工作并舉者,立即詳咨會辦。[32]這些措施的實施,對河南的河渠修治、維護工作起到了良好的促進作用。
(三)晚清時期的河政腐敗與水利的失修
晚清時期河南的河渠修治雖然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在一定范圍內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但是總體上看來,成效有限,成績乏善可陳。水旱災害比清代前期更加頻繁,由此引起的嚴重饑荒不斷發生,尤其是光緒初年的丁戊奇荒,其嚴重程度為有清一代二百六七十年間所僅見。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晚清時期的河政十分腐敗、水利失修所造成的農業生產條件日益惡化無疑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孫中山在《中國的現在和未來》一文中說:“中國所有的一切災難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統的貪污,這種貪污是產生饑荒、水災、疫病的主要原因。”[33]晚清時期的河政十分腐敗,以黃河的治理費用為例,河官貪污成風,冒領虛報、中飽私囊。據《清史紀事本末》揭露:“南河歲費五六百萬金,然實用之工程者什不及一,余悉以供官吏之揮霍。河帥宴客,一席所需,有斃三四駝,五十余豚,鵝掌猴腦無數。食一豆腐亦需費數百金,他可直已。驕奢淫佚,一至于此,而于工程方略,無講求之者。”[34]南河總督潘錫恩“致仕回籍”后,竟“擁資數百萬”,成為皖南首富。除貪污腐敗之外,治河官員的昏庸無能,諱言災情,視河工為兒戲,也是河政敗壞的一個重要表現。光緒十三年黃河在鄭州十堡決口前,十堡黃河堤岸已經十分危險,但身為河督的成孚卻漠然置之。“遲至十日之久,危在頃刻之間,萬夫失色,呼號震天,各衛身家,咸思效命,無如何于之上,曾無一束之秸、一撮之土,棘手待潰,徒呼奈何!”成孚仍奏報虛飾,諱決為漫,諱四五百丈為三四十丈,且稱居民未傷一人”。[35]有清一代,首重治河,黃河的治理尚存在如此的嚴重腐敗問題,其它河流的修治也可以想見。如緒十年(1884年),有人指出,河南省內農田水利敗壞日久,特別是經過戰爭后,“地方各官直不知水利為何事,惟日持三尺法以催比征徭而已”。[36]
河政敗壞所造成的水利失修現象十分嚴重。官府只顧苛斂而不顧水利,許多州縣舊有溝渠堙塞日甚,水患頻發。項城各鄉,“民風凋敝,道路平毀,溝渠淤塞”;[37]鹿邑縣境,原有溝渠百數十條大都堙塞,有的且墾為農田,農民“播種即畢,旱澇皆聽之于天”。[38]像扶溝境內的蔡河、雙溝河、惠民河等“衡決潰溢相仍,民不堪命”。[39]陜州境內的譙水、橐水,“稍有雷雨,即被暴水沖沒……旱則水泉干涸,河底熯然”。光緒四年閏五月中旬,丁戊奇荒剛接近尾聲,許多州縣雨水較多,又成大災。如葉縣沖壞20余村民房5000余間,淹死數百人;南召亦許多農舍被毀,死數十人;寶豐水沖44村,壞民房近萬間,淹死86人;魯山沙河漫溢,大片農田被水。[40]雖然有鑒于此,河南巡撫鹿傳霖于年初農閑時派員赴各州縣,與地方籌商疏浚於淺河道,挑挖堙塞溝渠。在官府的督促下,有些州縣也興辦了一些水利設施,但大都敷衍塞責。如安陽原有的天平渠,當地官紳于光緒五年(1879年)即籌劃重浚,三年后修成,可惜“官紳莫肯實心任事”,工程草率,效益不著。[41]
晚清時期農業生產持續衰退、土質變劣、荒蕪土地日漸增多,雖然與官府的橫征暴斂,農民負擔奇重,生活絕對貧困化等原因有關,但是水利不興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光緒三十一年,社會人士稱“豫省……沿河二十余州縣,沙壓荒地,一望無際……腹地平原雖皆土脈肥沃,然水利未興,施肥化工之術不講,以致歲率歉收,一畝之田,未獲得半之效”。[42]如新安、澠池一帶,旱地每畝收麥90多斤,如果有水灌溉,再加糞肥,可提高到200多斤。[43]據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官方出版物敘述,全省“一遇雨澤,即有漫溢之害;一經不雨,即有亢旱之害……荒地之多,甲于他省”。不僅沙地斥鹵一望無垠,就是平原低濕地帶,在南方均可以成為膏腴水田者,亦“任其荒蕪”,村旁隴畝可耕之地,也聽其荒蕪不耕。[44]據1910年省內36個州縣冊報,共有荒地330多萬畝。即使在耕之田地,也“大都鹵莽滅裂,田多之戶,即不免草率竣功,田少者又以無力養牛,暫假于鄉鄰,谷種入土即已”。[45]如武陟縣道光前有耕地7 209頃,至清末只有6425頃。
與生態環境發生最直接、最重要關系的是人類的農業活動。曾雄生認為,傳統農業反映出“人”、“天”、“地”、“稼”的關系,所謂“夫稼,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為之者人也”。其中“天”、“地”是自然環境,“人”、“天”、“地”的關系是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稼”兼具自然因素和人的因素,人按照人之所需與自然之可能,選擇和種植農作物。[46]所以人類的農業生產活動,對生態環境具有明顯的影響作用。清代,中原人為擴大耕地面積,進行了持續200余年的農業開發,從本質上說是與林草爭地、與河道爭地、與山林植被毀壞相始終。水、旱、風、沙等自然災害雖然是氣候的異常變化引起的,但持續人為的不合理的土地開發又成為導致水土流失、旱澇加劇、沙堿肆虐、自然環境惡化的重要原因。
在自然生態系統中,物質流動遵循物質不滅定律,在周而復始的循環過程中不會減少,只要沒有外界大的干擾破壞,就可以永續利用,保證生態系統的穩定發展。但是在半人工的農業生態系統中,因為人們每年需從農業生態系統中收獲農產品,使部分物質流出了該系統,故每年都需要施肥增加新物質。農業生態系統越是高產,從中索取的物質越多,則每年要補充、輸入該系統中的物質也越多。一味的索取,使系統內的物質越來越少,會導致土壤退化,農業生態系統質量下降,生產潛力衰退,久而久之,整個農業生態系統就會崩潰。由于河南多數地區缺乏森林植被,農村燃料嚴重短缺,因而“土地里生長的一切都被農民收去,他們把殘梗、葉片和草都一齊收去作燃料,地里連一葉、一草、一根都不留下,也不可能以草灰作肥料……很多的土地太貧痔了,或者是碳酸鈉過多,……如果不充分施肥,種植就很難得到好處。 這種土地在一個貧苦人手里,幾乎毫無用處。”[47]這樣大量的秸稈不能還田,再加上大量的耕地得不到施肥,使土壤有機質含量不斷減少,土壤肥力不斷下降。
清代河南土地肥力下降集中表現為豫東與豫北平原大面積耕地地力耗竭、土地沙堿化,土地生產能力極為低下,甚至完全不能耕種。這種現象在康熙、乾隆年間已比較明顯。如延津縣“新開不堪耕種之地,稍可者三畝方可有一畝之獲,次者四畝方有一畝之獲,稍下者五畝方有一畝之獲,最下者總無收成。即略有收成之田,耕種四五年,其地漸疏,其土漸浮,沙復飛揚,堿復浮泛,不可耕種”。[48]中牟縣墾荒,“初開之時,借草根腐朽之力,或可種收一兩年,及力盡風竭,仍棄為荒耳”。[49]此種情形,在河南其它地方也很常見,尤其山墾進行比較徹底的地方,本來就不高的土壤肥力很快降低,數年后即廢耕。如嵩縣“山農尤苦者,地皆陡瘠,不任行犁,專恃人力,初墾荒田,得粟頗多,三年后,土薄不堪藝植,則移墾他處,名為倒荒”。[50]由于地不養人,一些山村居民不得不另擇他處而居。移墾之后形成的嚴重的水土流失,不僅造成農作物賴以生長的基本物質基礎喪失,就連自然植被也難以恢復生長,形成不可逆轉的生態環境退化。
參考文獻:
[1]呂坤:《實政錄·民務》卷之四《清均土地》,嘉慶十四年重刻本.第l0-11頁。
[2]轉引自陳嶸:《中國森林史料》,中華農學會叢書,1951年版,第49頁。
[3]【道光】王德瑛:《舞陽縣志》卷二《縣南北河防水惠論》,道光十五年刻本,第19頁。
[4]《公議斷坡碑》,《中州今古》,1986年第1期,第20頁。
[5]王鳳生等修:《武陟縣志》,卷23《俞森種樹說》,道光九年修。
[6]田文鏡:《撫豫宣化錄》卷三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頁。
[7]賀昌齡輯:《皇清經世文編》卷四一《備荒管見》,《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74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461頁。
[8]【乾隆】康基淵:《嵩縣志》卷六《風土》,乾隆三十二年刻本,第9頁。
[9]轉引自楊海蛟:《明清河南林業研究》,北京林業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6月。
[10]轉引自楊海蛟:《明清河南林業研究》,北京林業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6月。
[11]轉引自陳嶸:《中國森林史料》,中華農學會叢書,1951年版,第48頁。
[12]【雍正】田文鏡、孫灝等:《河南通志》卷七七《藝文》,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594頁。
[13]《清高宗實錄》,卷八三,乾隆三年十二月丙子,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13頁。
[14]河南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纂:《河南通鑒》,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34-435頁。
[15]轉引自楊海蛟:《明清河南林業研究》,北京林業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6月。
[16]轉引自楊海蛟:《明清河南林業研究》,北京林業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6月。
[17]楊海蛟:《明清河南林業研究》,北京林業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6月。
[18]溫縣亢村禁斷碑(咸豐元年十一月初十日立)
[19]公議斷坡碑,《中州今古》,1986年第1期,第20頁。
[20]《清會典事例》,轉引自河南省水利廳宣傳中心編《河南水利大事記》,方志出版2005年1月,第118頁。
[21]《清會典事例》)轉引自河南省水利廳宣傳中心編《河南水利大事記》,方志出版2005年1月,第120頁。
[22]【清】乾隆十九年《歸德府志》卷十五《水利略二》,河南省商丘地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整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464頁。
[23]【康熙】《西平縣志》卷1《溝渠》。
[24]任崇岳主編:《河南通史》第3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2頁。
[25]【嘉慶】《汝寧府志》卷5《水利》。
[26]《清會典事例》)轉引自河南省水利廳宣傳中心編《河南水利大事記》,方志出版2005年1月,第118頁。
[27]《清會典事例》)轉引自河南省水利廳宣傳中心編《河南水利大事記》,方志出版2005年1月,第120頁。
[28]【清】乾隆十九年《歸德府志》卷十五《水利略二》,河南省商丘地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466-467頁。
[29]引自河南省水利廳宣傳中心編《河南水利大事記》,方志出版2005年1月,第141頁。
[30]河南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纂:《河南通鑒》,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89頁。
[31]【民國】《續武陟縣志》卷六。轉引自河南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纂:《河南通鑒》,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98頁。
[32]《清會典事例》)轉引自河南省水利廳宣傳中心編《河南水利大事記》,方志出版2005年1月,第151頁。
[33]《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08頁。
[34]《咸豐時政》,《清史紀事本末》卷45。
[35]轉引自河南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纂:《河南通鑒》,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501頁。
[36]《中國近代史料叢刊》,《戊戌變法》(二),第301頁。
[37]【宣統】張鎮芳:《項城縣志》(卷三),臺北:文海出版社,第47頁。
[38]【光緒】《鹿邑縣志》卷九,光緒二十二年刊本,第3頁。
[39]【光緒】《扶溝縣志》序,轉引自河南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纂:《河南通鑒》,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97頁。
[40]張諧之:《詳陳陜州水利情形稟》,《敬齋存稿》,卷三。轉引自河南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纂:《河南通鑒》,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98頁。
[41]【民國】《續安陽縣志》卷三,民國二十二年刊本,第4、5頁。
[42]《東方雜志》第二卷第5期《實業》第74頁。
[43]河南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纂:《河南通鑒》,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97頁。
[44]《河南官報》第23期。轉引自河南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纂:《河南通鑒》,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521頁。
[45]《河南官報》第15期。轉引自河南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纂:《河南通鑒》,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522頁。
[46]轉引自張研:《清代自然環境研究》,《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
[47]轉引自 徐潔:《農民經濟的歷史變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222頁。
[48]【康熙】余心孺:《延津縣志》卷九《條陳》,康熙四十年刻本,第45頁。
[49]郭盡光:《縣南八堡墾荒批詳始末》,【乾隆】《中牟縣志》卷九,乾隆十九年刻本,第12頁。
[50]【乾隆】康基淵:《嵩縣志》卷九《風俗》,乾隆三十二年刻本,第11—12頁。
作者簡介:周楠(1980-)女,中共河南省委黨校黨史教研部講師,博士,主要從事中共黨史、中國近現代史方向的研究。
(作者單位:中共河南省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