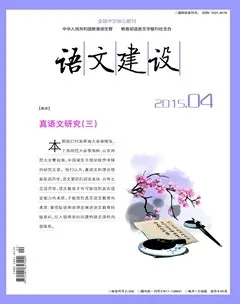解讀文本應立足文本
莫懷戚的《散步》人選初中語文教材多年,其平實的敘事、真純的情感、含蓄的說理和曉暢優美的語言表達,成為學生學習運用言語的范例和精神生命成長的養料。對這篇散文的解讀,大致可分為四種角度:文本角度、作家角度、讀者角度和三者交互角度。
第一種解讀角度從文本敘事說理切人,所占比例較多,無論是由敘事推導出表現了美好的家庭人倫親情,還是歸結到中年人的擔當和應盡的責任,都是基于文本文字敘事本身的閱讀立場。
第二種解讀角度從作家寫作緣由、寫作意圖切人,立足點在于凸顯中國文化敬老愛幼的可貴。莫懷戚曾寫過兩篇交代寫作緣由、寫作意圖的文章,一篇是《(散步)的寫作契機》,一篇是《二十年后說(散步)》。前一篇里作者寫自己與美國漢學家柯爾特常就中西文化的異同進行淺層次的交流,讓他意外和感慨的是對方對中國孝文化大加贊賞,稱其為文化的精髓:“我們自己丟掉的,發達國度的人卻拾起來,如獲至寶,這使我感慨不已,開始重新正視這份看起來很陳舊已無什么油水的民族遺產。寫作的念頭就產生了。”第二篇明確地交代是要寫責任,寫生命,寫人類生命規則。人類生命的規則是什么呢?人類“沒有資格獨享強壯,它(生命)必須對它的兩端的弱勢負責,即強壯當對幼小和衰老負起責任來”。對老人負責,是人類與動物的不同。“對幼子負責,屬于遺傳本能,而對老人負責,就是文化了,與本能顯然不可同日而語。”敬老是中國人的生命規則,也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特點,敢于把老人這個包袱背在背上,是中國人的底氣,也是中國人心靈最健全之處。與中國文化對比鮮明的是西方文化的仿動物秩序,社會是“孩子的天堂,青壯的戰場,老人的墳場”。這種秩序適于競爭,但文化含量很稀薄。由敬老的責任到生命的規則再到中國文化相較于西方文化的底氣,這種逐層連接深化的解讀方式是基于作者的立場。
第三種解讀角度基于讀者(學生)的立場,學生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將視線聚集到文本的哪個角色,都能獲得愛與幸福的感受體驗,都能體悟到親人之間愛的付出和成全。作為年幼的孫子,享有父母的疼愛、祖母的遷就,這很普通,不普通的是父母對他的重視。面對選路分歧,父親雖然決定走大路,但對兒子是有愧意的,覺得是“委屈”了兒子,這充分表明在父親的眼里兒子的意愿和大人的意愿同等重要。當他說“前面也是媽媽和兒子,后面也是媽媽和兒子”,一家人“都笑了”,那笑聲中包含的是對說話者言語水平的驚訝和贊許。作為年邁的祖母,身體不好得到的照顧關懷卻更多了,為了遵從她的意愿兒子甚至都忍心委屈孩子。作為兒子,母親依賴自己,孩子聽話,妻子順從。作為妻子,只是在外面總聽丈夫的,但在家里呢,大概和外面有很大不同吧。
第四種解讀角度是文本、作者、讀者的交互融合,讀者通過文本認識反省自己,作者通過文本表達自己并被讀者理解,文本因讀者和作者的反復觀照而具有了鮮活豐富的持久力。每個生命都會經歷幼小、壯年、衰老,此時“我”對兒子的呵護正如當年母親對“我”的呵護,此時母親對“我”的依賴正如當年“我”對她的依賴。“我”老去的時候,兒子正如今天的“我”,照顧“我”,呵護他的孩子,生命就是這樣一代一代盡責傳遞。世界其實就是生命的世界,一端是年老的生命,另一端是年幼的生命,中間是背起兩端的壯年生命。生命的世界之所以充滿生機,是因為每個生命都曾得到過照看,也都會盡照看他人的責任。
以上四種角度的解讀都獲得了不同程度的認可,現在出現了第五種角度的解讀——社會政治大敘事角度,文章為《從小敘事到大敘事——重讀(散步)》,與以往解讀最大的不同在于,作者找出的文本關鍵詞是“秩序和權威”,理由是整個散步事件都在突出“我”和“母親”新舊兩代權威。事件的開始是要不要去散步,由“我”來決定。身體不好的母親本不愿出來,“我”說正因如此才應該多走走,母親很聽“我”的話,便去拿外套。當散步發生分歧時,走哪條路也取決于“我”,母親老了,早已習慣聽從她強壯的兒子;兒子還小,習慣聽從他高大的父親;妻子,在外面,總是聽“我”的。后來選擇走小路,是母親改主意決定下來的。由秩序和權威,作者又引出了大路與小路的象征意義,大路是老年心態,小路是青春心態。根據結尾部分的一段話,“好像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來,就是整個世界”。作者得出這樣的結論:《散步》寫的是一個時代社會、政治、文化的面貌轉換,“當時的中國,新的生命在滋生,需要以新的體驗感受這一世界,這時舊的意識沒有退去,還在影響這個世界,中間力量背負起這兩種因素,自然就是背負起了整個世界”。文章最后指出,解讀的視角有大敘事和小敘事兩種,從國家命運、民族前途、政治博弈、社會變遷的角度出發是大敘事,從人倫、親情、離愁、性格、人性角度出發是小敘事,《散步》的解瀆應該從以往的小敘事角度轉化為大敘事角度,大敘事角度的解讀為語文課堂教學日標指向提供了新的思路。
先不說作者對于大敘事小敘事這類文學評論專業術語的闡釋是否得當,單說作者認定以大敘事角度來解讀是《散步》文中的應有之意的理南,就不那么讓人信服。作者認為《散步》寫于激烈變革的20世紀80年代,是處于大敘事盛行的年代,而小敘事則是從90年代才開始在我國流行,所以《散步》的寫作敘事方式以及解讀角度必然是大敘事。以時代文學潮流來圈定作家作品同然有合理性,但單憑一個依據就要做出斷語未免有點草率。文學創作向來既受社會時代影響,同時又是個人的選擇,絕非時代影響就可以強制的。另外,任何一個時代文學思潮都是主流與非主流并存,80年代的文學敘事不盡然是大敘事的天下,從來就沒有一種敘事可以純凈地統治一個時代。更何況莫懷戚自己就申明過當時的創作是“情節化”的(也稱細節化),“近年的散文寫作傾向之一,是情節化,總之寓理于事之風長,單純說理之風消”,“情節化”或稱“細節化”是小敘事最明顯的特征之一。
從大敘事角度解讀,雖說是增多了一種解讀的維度,但這種維度的解讀前提是作品必須具有鮮明的大敘事特征。有論者這樣歸結大敘事的特征:“在題材主題上,往往是反映包括政治、經濟、民族、文化、宗教、信仰、階級革命、啟蒙解放、社會責任、集體主義、國家命運、歷史進程等人類和社會重大問題,在強調寫實的基礎上‘再現’歷史,追求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一。在內在邏輯上,追求作品的現實批判性、歷史性與人性深度,注重普遍價值觀與文化精神的內在統一,但往往是時間與因果邏輯成為敘事的基本規則。在敘事結構上,追求白始至終的全景敘述,具有敘事線索的清晰性、敘事結構的完整性以及敘述情節的連貫性。”如果作品此類特征并不顯著,非要拿來標新立異,那么它對語文教學的價值貢獻可能會有限得多。
多元解讀是語文新課程改革以來最富有活力也最容易被扭曲的一個課程術語,它既是對作家作品“一元化”的超越,同時又是對讀者中心主義的反撥。多元是作者、作品、讀者三者融合交互產生的多維與多義,是三方的互相補白、印證與更新。作品給予讀者更多的人生體驗,讀者使作品的意蘊更強大,讀者和作品使作者更深入地反觀自身,作品和作家使讀者的境界更開闊,正如一些美學論斷所言,人在對象物中看到了更真切的自己,對象物因人具備了超越自身的屬性。多元解讀在語文教學中出現的變形異化,和我們總在闡釋學的理論泥淖中尋求依據有關。闡釋學內部本身矛盾重重,各派宗旨不很統一。毫不夸張地說,多元解讀是闡釋學的“浪子”,多元的家該歸向何方?闡釋學幾乎無法做出正面同答,因為當闡釋學給了讀者在面對文本及文本所代表的世界極度自由權利之后,當一切歷史都成為自我人生的注解,當自我完全等同于世界的時候,失去了外物參照感的人的自身存在感也將歸于荒蕪。如果我們能在更大的哲學視野里認識理解闡釋學,也許就少些偏差。參照物越多,越能準確定位,這不僅僅是物理學適用的原則。西方哲學在經歷了以人為中心漫長的主客對立之后,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人把自身凌駕于萬物之上,最終必然導致人的困境。當人把萬物甚至同類當作可供驅使的對象時,自身必將陷入孤立的絕望之中。人對物的侵占利用,人對人的統治欺壓,只能導致自身離人的本質屬性越來越遠。近年來流行于影視劇里的怪物、怪獸絕不單純是奇特的想象,而是對自身存在感到恐懼的產物,害怕自身將來變成非人的形態。于是,以倡導平等主體性,試圖以“理解”解決存在的危機感的存在主義逐漸成為主流。存在主義信奉客體是和主體一樣平等的存在,萬物的關系是主體間性,人類在與他者的交互中才能有效地阻止自身的異化。在這樣的哲學觀下再來看文學闡釋,就能深入地理解多元解讀的實質是讀者、作者、作品的平等作用,是三者力最的交響,作品如樂章,作者如作曲者,讀者如演奏者。作曲者通過樂章展示自己,演奏者在樂章中體驗作者并且表達自己的理解,樂章作曲者通過演奏者得到完善和升華。簡單點說,多元解讀是以文本原意為基礎的讀者閱讀闡釋,是讀者對文本原意的開掘和發展。
具體到散文多元解讀,文本原意基礎該從哪一方面抓取呢?首先是了解創作背景和創作動機,然后是分析文體特征。拿《散步》來說,第一條前邊已經詳論,第二條分析文體特征。散文是一種重在抒寫作者主觀感受和情思,結構自由靈活,題材廣泛多樣的文體。《美國語文》第六部分“繁榮與保護”第四課散文作品專題,給散文下的定義是“非虛構的簡短寫作,作者借散文來表達個人看法或主張”,并把散文分為分析散文、諷刺散文、說理散文和思考散文:分析散文是分析解釋一個主題的各部分;諷刺散文是用嘲笑反語對一個主題進行評論;說明散文是提供一個主題并對它進行解釋;思考散文描述個人經歷或關鍵性事件,表達作者對于事件的感情和思考,通過思考達到對事件經歷的深刻理解。
用《美國語文》關于散文的定義分類來說,《散步》屬于思考性散文。分析文體特征,不是說把一個定義、分類準則拿來套用,分析是比較、甄別、取舍,結合共性規律特征和個性差異做出綜合判斷。正如袁愛國老師在《散步》設計思想里提到的“散文教學內容的確定,不僅要關注散文的文體特征,還要體現具體作者的‘個性’特征”,我們是把共性與特性放在一起合稱為文體特征,因為只有二合一的文體特征分析才能幫助學生既借助文體圖式進入文本,又能以文本的特性十富圖式。
以文本原意為基礎的多元解讀,并不是在文本原意解讀之后,才開始讀者闡釋,而是多向開展,可以先開展讀者解讀,然后以文本原意印證,之后再進行讀者解讀,如此循環,直至讀者真正深入地理解作品。當然也可以先開展作者原意解讀,但不是一下子將作者原意和盤托出,而是以此為線索引導學生發現原意,創造作品的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