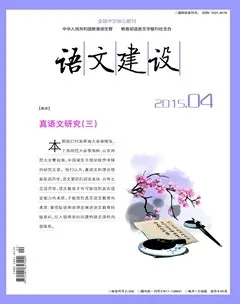古典詩歌欣賞的基礎范疇(一):比喻
一般說,中國古典詩歌是講究比興的,其實,這種說法并不全面,許多敘事性的經典長者如《木蘭辭》就只在結尾處有一個比喻,短者如杜甫的《石壕吏》整首無比喻。當然,就抒情詩歌而言,用比喻的很多,但是,論者往往引用朱熹的“以彼物喻此物也”為滿足。就比喻來說,只是一種修辭,是詩歌、戲劇、小說都少不得要運用的,并不包含詩的特性。我們的任務是把詩的比喻的特性揭示出來。從概念到概念的演繹不能解決問題,請允許我從一個最簡單的例子開始。《世說新語·語言》載:
這個問題,光憑印象就可以簡單解答,謝道韞的比喻比較好,但是,光有個感覺式的答案還不夠。第一,感覺到的可能有錯;第二,即使沒有錯,感覺也是比較膚淺的。感覺到的,不一定能夠理解;理解了的,才能更好地感覺。我們的責任就是要把其中的道理講清楚,這就涉及對比喻內部特殊矛盾的分析。
通常的比喻有三種:第一種,抓住兩個不同事物或概念之間的共同點,這比較常見,如“燕山雪花大如席”,“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第二種,抓住事物之間的相異點,如“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第三種,把相同與相異點統一起來,如“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第二和第三種,是比喻中的特殊類型,比較少見。最基本、最常用的是第一種,從不同事物或概念之間的共同點出發。謝安家族詠雪故事屬于這一種。
構成比喻,有兩個基本的要素:首先,從客體上說,二者必須在根本上、整體上有質的不同;其次,二者在局部上有共同之處。黃侃在《文心雕龍札記》中說:“但有一端之相似,即可取以為興。”這里說的是興,實際上也包含了比的規律。《詩經》:“出其東門,有女如云。”首先是女人和云,在根本性質上不可混同,然后才是在數量的眾多給人的印象上,有某種一致之處。撇開濕而易見的不同,突出隱蔽的暫時的聯系,比喻的力量正是在這里。二者之間的相異性是我們熟知的,因為熟知就會感覺麻木;但二者之間的共同點是被淹沒的,一旦呈現,就變成新的感知,就可能對感覺有沖擊力。比喻的功能,就是在感覺麻木的地方,開拓出新鮮的感覺。我們說“有女如云”,明知云和女性區別是根本的,仍然能體悟到某種紛紜的感覺。如果你覺得這不夠準確,要追求高度的精確,使二者融洽無間,像兩個相等半徑的同心網一樣重合,只能說“有女如女”,而這在邏輯上就犯了同語反復的錯誤,比喻的感覺沖擊功能也就落空了。因此,紀昀(曉嵐)說比喻“亦有太切,轉成滯相者”。
比喻不能絕對地追求精確,比喻的生命就是在不精確中求精確。朱熹給比喻下的定義是:“以彼物譬喻此物。”(《四庫全書·晦庵集:至林熙之》)這只接觸到了矛盾的一個側面。王逸在《楚辭章句·離騷序》中說:“《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海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云霓,以為小人。”《楚辭》在比喻上較之《詩經》更加大膽,它更加勇敢地突破了以物比物、托物比事的模式,在有形的自然事物與無形的精神之間發現相通之點,在自然與心靈之間架設了獨異的想象橋梁。
關鍵在于,不拘泥于事物本身,超脫事物本身,放心大膽地到事物以外去,才能激發出新異的感覺,而執著于事物本身只能停留在感覺的麻木上。
閱讀古典詩歌,目的不在認識比喻,而在于判別什么是好比喻,什么是不好的比喻。從質量上說,比較有兩種:一種是一般的比較,一種是好的比喻。好的比喻不但要符合一般比喻的規律,而且要精致;不但詞語表層顯性意義相通,而且深層的、隱性的、暗示的、聯想的意義也要相切。這就是《文心雕龍》所說的“以切至為貴”。
有了這樣的理論基礎,就可以正面回答謝安侄兒謝朗的“撒鹽空中”和侄女謝道韞的“柳絮因風”哪一個比較好的問題了。
以空中撒鹽比降雪,符合本質不同、一點相通的規律,鹽的形狀、顏色與雪一點相通,可以構成比喻,但以鹽下落此喻雪花,引起的聯想卻不及柳絮因風那么“切至”。因為鹽粒是有硬度的,雪花則沒有,鹽粒的質量大,決定了下落有兩個特點——一是直線的,二是速度比較快;而柳絮質量很小,下落不是直線的,而是方向不定的,速度也是比較慢的。另外,柳絮飄飛是自然常見的現象,容易引起經驗的回憶,而撒鹽空中并不是自然現象,撒的動作和手聯系在一起,撒鹽的空間有限,和滿天雪花紛紛揚揚之間聯想不夠“切至”。柳絮紛飛在當時的詩文中早已和春日意象聯系在一起,引起的聯想也是詩意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謝道韞的比喻,不但恰當切至,而且富于詩意的聯想;而謝朗的比喻,則是比較粗糙的。
比喻的“切至”與否,不能僅僅從比喻本身看,還要從作家主體來看,和作者追求的風格有關。謝道韞的比喻之所以好,還因為和她的女性身份相“切至”,如果換成一個關西大漢,這樣的比喻就可能不夠“切至”。有古代詠雪詩日:“戰罷玉龍三百萬,殘麟敗甲滿天飛”,就含著男性雄渾氣質的聯想,讀者從這個比喻中可能感受到叱咤風云的將軍氣度。
比喻的暗示和聯想的精致性,還與形式和風格不可分割。“未若柳絮因風起”,是七言的古詩(不講平仄),由于詩的比喻,充滿了雅致高貴的風格。這并不是唯一的寫法。同樣是寫雪,李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北風行》)就是另一種豪邁風格了。李白的豪邁與他對雪花的夸張修辭有關。如此大幅度的夸張,似乎有點離譜,故魯迅為之辯護曰:
魯迅的這個解釋,僅僅從客觀對象的特點來看問題,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卻把問題簡單化了。其實,全面看問題,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本體與喻體的客體特征有相似性,魯迅說的正是這個意思,因為是在北國燕山,雪花特別大;但是,特征的相似性又很豐富,有時,北方的雪花并不僅僅是雪片之大,如岑參的“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就以雪片之多,鋪天蓋地之美取勝。為什么有不同的選擇呢?
第二,就是主體特征,也就是情感的、風格的選擇和同化。當然,也有人為“撒鹽空中”辯解說,謝朗比喻的是“米雪”,更像某種粒狀的小雪。然而,詩的意象是物象特征與情感特征的統一,在詩中情感是絕對自由的,物象可隨情感特征而發生無窮的變異。詩中的意象并不單純以逼真的物象取勝,拘泥于物象,忽略了情感對于物象的主導作用,就人不了詩之門。王國維總結中國古典詩話詞話各種說法得出一個著名的論斷:“一切景語皆情語”。說的是一切比喻皆由情感的特征同化,不符合事物的形態,甚至其性質和功能發生“變異”,卻可能更富于詩意。在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中,“千里冰封,萬里雪飄”達到“欲與天公試比高”的程度,若拘泥于物象吹求,就不可能感受到其氣魄了。
第三,情感還受另一個維度的約束,那就是文學形式。“燕山雪花大如席”之所以精彩,還因為它是詩。詩的虛擬性,決定了它的想象要自由得多。如果是寫游記性質的散文,說站在軒轅臺上看到雪花一片一片像席子一樣落下來,那就可能成為魯迅所擔憂的“笑話”了。
第四,詩意的情趣并不是文學唯一的旨歸,除情趣以外,笑話也是有趣味的。這時的比喻,就不是以“切至為貴”,相反,越是不“切至”,越是不倫不類,越有效果,這種效果,叫作幽默。同樣是詠雪,有打油詩把雪比作“天公大吐痰”,這固然沒有詩意,但有某種不倫不類的怪異感、不和諧感,在一定的上下文中,也可能成為某種帶著喜劇性的趣味。如果說,詩意的比喻表現的是情趣的話,而幽默的比喻傳達的就是另外一種趣味——諧趣。舉一個更為明顯的例子,如“這孩子的臉紅得像蘋果,不過比蘋果多了兩個酒窩”,這是帶著詩意的比喻。如果不追求情趣,而是諧趣,就可以說“這孩子的臉紅得像紅燒牛肉”,這缺乏詩的情趣,但可能在一定的語境中顯得很幽默風趣。這在詩歌中也是一格。相傳蘇東坡的臉很長而且多須,其妹蘇小妹額頭相當突出,眼窩深陷,蘇東坡以詩非常夸張地強調了妹妹的深眼窩:“數次拭臉深難到,留卻汪汪兩道泉。”妹妹反過來譏諷哥哥的絡腮胡子:“口角幾回無覓處,忽聞須內有聲傳。”哥哥又回過來嘲笑妹妹的額頭:“邁出房門將半步,額頭已然至庭前。”妹妹又戲謔性地嘲笑哥哥的長臉:“去年一滴相思淚,今朝方流到腮邊。”雖然是極度夸張雙方長相的某一特點,甚至達到怪誕化的程度,卻沒有丑化,至多是讓人感到可笑,這樣的諧趣就是幽默感。
第五,詩歌的比喻還有既不是情趣,也不是諧趣的,叫作“智趣”。最有名的例子是朱熹的《觀書有感》:
整首詩都是一個暗喻,把自己的心靈比作水田,為什么永遠清凈如鏡地照出天光云影呢?因為有源頭活水,聯系到詩的題目“觀書”,說明讀書就是活水。這樣的詩在說明一個道理,其趣味既不是抒情的情趣,也不是幽默的諧趣,而是智慧的“智趣”。
什么問題都不能簡單化,簡單化就是思考線性化,線性化就是把系統的、多層次的環節,完全掩蓋起來,只以一個原因直接闡釋一個結果。比喻的內在結構也一樣有相當系統豐富的層次,細究下去還有近取譬、遠取譬,還有抽象的喻體和具體的喻體等講究。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就是魯迅也未能免俗,把客體的特征作為唯一的解釋。
我想,魯迅的失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提出問題是從一般修辭學的角度,而不是從詩的角度。如果從詩的角度,柳絮因風,撒鹽空中,就不僅僅是修辭的問題。修辭本身不能決定自己的價值,要看傳達情志起了什么作用,而什么樣的作用又要看運用了什么樣的文學形式。同樣的比喻,在不同的文學形式效果是不同的。
在語文教學和研究中,常滿足于把豐富多彩詩歌比喻的精妙,僅僅歸結為比喻,最多是區分為明喻、暗喻等。這樣的歸類充其量不過是把各不相同的情感和語言表現,納入幾個有限的、干巴的模式中,遮蔽了其獨特的、不可重復的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