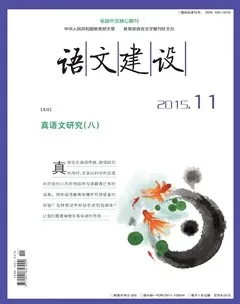語言品味四例
對于語文教學,我有這樣一個比方:語文就如同一枚水果,語言是它的皮(或者殼),文化是它的肉,而精神(或者說價值觀)是它的內核;語文教學,就是要帶領學生去剝開那層語言的殼,吃到文化的肉,完了再種下一粒精神的種子在學生的心田,直到它有一天生根發芽。語文教學,無論是閱讀還是寫作,無外乎三個層面:語言、文化、價值觀。語文課堂首先要解決的,無疑是這“水果”的皮(殼)——語言;而語文教學最能成趣的地方,也是語言品味。
以歐·亨利的《最后的常春藤葉》為例,蘇教版教材編寫在“珍愛生命”單元,并賦予“精神支柱”小欄。如果我們在文本解讀中把焦點放在老畫家貝爾曼身上,一味地圍繞“杰作”做文章,把貝爾曼的犧牲精神和人與人之間相濡以沫的情感作為解讀重點,顯然忽略了“編者想要我們教什么”和“學生真正應當學到什么”。
我們不妨到課文中去,抓關鍵段落的關鍵詞語:
“我真是個壞姑娘,蘇艾,”瓊珊說,“冥冥中似乎有什么使那片葉子不掉下來,啟示了我過去是多么邪惡。不想活下去是個罪惡。現在請你拿些湯來,再弄一點摻葡萄酒的牛奶,再——等一下,先拿一面小鏡子給我,用枕頭替我墊墊高,我要坐起來看你煮東西。”
這里面,“啟示”一詞非常重要。最后的一片常春藤葉(貝爾曼的“杰作”)給了瓊珊“啟示”,這是一種自我生命意識的喚醒。每個人都有自己最后一片葉子,無論它的大小或形狀。只要它在我們心靈的窗口閃動,我們就有凝望它的理由。不管我們有沒有勇氣走近,看一看那是真實的葉子還是顏料的魔術,只要有一片葉子,我們就會感知自我的存在,心中就還有希望。如果某個時刻,我們心中沒有希望了,那這片葉子也就不復存在了。
這就應了梁漱溟的那句話:“一輩子首先要解決人和物之間的關系,再解決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最后解決人和自己內心的關系。”是的,到底是什么力量讓瓊珊起死回生?一是“人和物之間的關系”問題的解決,這里有西藥,有醫生;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問題的解決,這里有日夜陪伴著她的蘇艾,有為了她付出生命的貝爾曼,有人與人之間的相濡以沫;但實際上,最重要的還是“人和自己內心的關系”問題的解決。
再以日本作家栗良平的《一碗陽春面》為例,文中母親四次要面的語言描寫就值得師生品味:
……唔……陽春面……一碗……可以嗎?
……唔……一碗陽春面……可以嗎?
……唔……兩碗陽春面……可以嗎?
唔……三碗陽春面,可以嗎?
這里有小說人物形象的真實性:“……唔……可以嗎”的話語,很符合日本人的說話方式,語言符合人物民族的特征,也符合母親當時的心理。這里有小說人物形象的復雜性和發展性:母親由非常害羞地開口要一碗陽春面,到少了一些害羞,再到非常平靜地說出要三碗陽春面,有一個變化發展,其中的原因是他們母子三人戰勝了困難,經濟狀況得到了一定的改善。這樣一品味,小說的人物、情節、環境,也就自然而然地貫通起來了。
又以電影文學劇本《泰坦尼克號(節選)》為例,杰克在冰冷的海水中對露絲有這樣一段告白:
聽我說,露絲。你一定能脫險的。你要活下去,你會生許多孩子,看他們長大。你會安享晚年,安息在溫暖的床上,而不是今晚在這里,不是像這樣地死去。你明白了嗎?
這里,教師可以設置一個語言活動:這段告白中,絕大多數“你”都可以改成“我們”,比如:“聽我說,露絲。我們一定能脫險的。我們要活下去,我們會生許多孩子,看他們長大。我們會安享晚年,安息在溫暖的床上,而不是今晚在這里,不是像這樣地死去。你明白了嗎?”但是,作者為什么不用“我們”而用“你”呢?對于這樣一個語言問題的討論,可以深入到文化層面:西方文化做事說話都比較直接,很少“美麗的謊言”,從下文杰克斷斷續續的話語“一定要答應我活下去……無論發生什么……無論多么令人絕望……露絲,永不放棄。答應我”中可以看出,在刺骨冰冷的海水中浸泡多時的杰克已經意識到自己快要不行了;如果換成東方文化,就是明知自己已經不久于人世,要和愛人永別,說出的話也會是“你要活下去,照顧好我們的老人”之類,而不是嫁給別人,“生許多孩子”。除此之外,還可以深入到精神層面來探討:當杰克對露絲說出這些安慰、鼓勵乃至祝福的話,他的眼里,露絲已經不再僅僅是她的愛人,更是一個作為弱者需要保護的女性。杰克對露絲的情感,在這里超越愛情,到了人性的層面。這和后文羅爾和希勤思的對照,以及老露絲回憶往事時說的“后來,在救生艇上的七百人只有等待……等待死亡,等待獲救,等待永遠無法赦免的心靈愧疚”的人性叩問遙相呼應。
再以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一詩為例:
想起故園飛黃葉/想起野塘剩殘荷/想起雁南飛/想起田間一堆堆的草垛/想起媽媽喚我們回去加衣裳/想起歲月偷偷流去許多許多
針對這樣一小節詩,可以在語言層面設計這樣一些問題:“想起故園飛黃葉/想起野塘剩殘荷”,把它改成“想起故園鋪綠葉/想起野塘滿碧荷”好不好?不好,因為意境不對,一個是哀景,一個是樂景。換成“想起故園的黃葉/想起野塘的殘荷”好不好?也不好,因為“飛”字和“剩”字,把靜景寫活了。
甚至,在學完《就是那一只蟋蟀》一詩,學生對鄉愁的意蘊和相應的意象有所感知后,再拓展引入余光中的《鄉愁四韻》(只給學生出示前兩韻):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酒一樣的長江水/醉酒的滋味是鄉愁的滋味/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給我一張海棠紅啊海棠紅/血一樣的海棠紅/沸血的燒痛是鄉愁的燒痛/給我一張海棠紅啊海棠紅
給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信一樣的雪花白/家信的等待是鄉愁的等待/給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給我一朵臘梅香啊臘梅香/母親一樣的臘梅香/母親的芬芳是鄉土的芬芳/給我一朵臘梅香啊臘梅香
之后,讓學生結合文本意蘊,尋找其他意象,以仿寫的形式,來續寫后兩韻。這樣的語言活動,往往有“無法預約的精彩”,例如:
給我一地月光白啊月光白/霜一樣的月光白/霜冷的滋味是鄉愁的滋味/給我一地月光白啊月光白//給我一口思鄉井啊思鄉井/酒曲一樣的思鄉井/酒曲的醞釀是鄉愁的醞釀/給我一口思鄉井啊思鄉井
總之,不管是把語文稱作“語言文學”,還是稱作“語言文化”,它都不能離開語言文字。語言文字的品味,能使語文課堂更有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