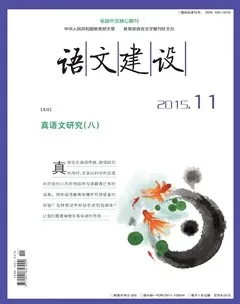《左忠毅公逸事》:桐城派“雅潔”之珍品
方苞是桐城派古文的主要代表,他主張“義法”,核心觀念是“言有物”“言有序”。這從字面上看好像平淡無奇,結合歷史語境分析,卻頗具深義。“言有物”相對于言無物,道理很簡單,就是不講空話;但是,“物”的內涵是“闡道翼教”“助流政教”,屬于文以載道的正統。他的成就以治經學為主,古文作品相對較少,其中也有些封建倫理的腐朽說教,如對某婦“割肱療姑”野蠻孝道的表彰。幸而他的文章最高成就不在“言”這種非人道的“道”,而在一些至今讀來仍然醒人耳目的杰作,《左忠毅公逸事》則是古典散文無可爭議的經典,可以作為他“言有物”的最積極意義上的注解。
一
“言有物”作為一個散文流派的綱領,“物”不是泛指,蘊含著歷史的針對性。方苞對中國散文歷史有過系統考慮。《四庫全書總目》對他的《〈望溪集〉提要》評論說:“其古文則以法度為主。嘗謂周秦以前,文之義法無一不備,唐宋以后,步趨繩尺,而猶不能無過差。是以所作上規《史》《漢》,下仿韓歐,不肯少軼于規矩之外。”其文取法六經,以《論語》《孟子》為最高典范,其次是《左傳》《史記》。唐宋八大家文章固然有成就,但在方苞看來“明道”不足,明朝只取歸有光。這就意味著他對影響甚大的獨抒性靈的公安派、竟陵派袁氏、鐘惺等不屑一顧。公安派、竟陵派之文章并非言之無物,只是在他看來,獨抒個人性靈,不能“闡道翼教”,等于是空言無物。
《左忠毅公逸事》其義不在個人性靈,而在為他人、為國(朝廷),置個人性命于不顧。這就是方苞的“言有物”之“物”。
本文所記之事為“逸事”,小事,不見于經典。文章最后聲言,據先輩方涂山所言(方為左光斗外甥,而且“與先君子善”),左光斗獄中對史可法的那一番話是他親自聽史可法說的。這里強調的是,所寫人物皆歷史人物,文中故事雖未見于正史,但具實錄性質,并非耳食之言。
至于方苞的“言有序”,從字面上看也是常識性的,無非是說,文章要講結構條理,似乎沒有什么深刻的內涵,但聯系到具體論述,“有序”就是文章要“雅潔”“澄清無滓”,所針對的是清初文壇上(通“黹”,刺繡,引申為雕琢)章繪句以取寵的文風。這里的關鍵是“滓”,什么是“滓”呢?第一,不可入語錄中語,應該是指朱熹式的口語,在他看來是不“雅”的;第二,不可入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第三,不可入漢賦中板重字法;第四,不可入詩歌中雋語;第五,不可入南、北史佻巧語。所謂“六朝藻麗俳語”,漢賦板重字法,因其堆砌,不夠簡“潔”。至于“不可入詩歌中雋語”,就不僅排斥華麗辭藻,而且也排斥抒情。“南、北史佻巧語”應該包括抒情贊嘆。避免了這一切,文章就能達到方苞所追求的不俗之“雅”,不繁之“潔”。這大概就是桐城派“古文義法”精神。理清了方苞的這種主張,才有可能深入分析《左忠毅公逸事》的優越和局限。
二
從文體而言,這是一篇記敘文。所記二人三事,題目點明是“左忠毅公”,當然以左光斗為主角,然皆以史可法眼光出之。全文當然有感情,但史可法視聽之效果為限。
就第一事而言,寫左氏識才、愛才。為官出巡,見陌生窮困書生之文,賞識到為之解衣掩戶,日后于科場見之,當場評為第一。召入府中,對夫人坦言:自己的兒子都平庸,日后能夠繼承大志者,只有此人。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明顯具有相當的傳奇色彩。如果當作傳奇文章來寫,則應該有相應的形容和渲染,則駢麗、排比、抒情是免不了的。然而,本文卻本先秦六經之道,重敘述,棄描寫與抒情,更不著筆于正面心理活動。
這一段寫作很有特點。第一,在用詞方面,幾乎都是當時書面常用的名詞和動詞,沒有任何生僻的上古語,形容詞也平常,只有一個(“嚴寒”之“嚴”),副詞只有兩個(“微行”的“微”,“瞿然而視”的“瞿然”)。全部過程直敘到底,沒有唐宋散文的刻畫和一唱三嘆,沒有公安竟陵文章的心靈剖白,當然也沒有朱熹語錄式的口語。第二,在句法上都是簡單句,句與句之間幾乎沒有連接詞,時間、空間的連貫性以及因果,盡在句間空白之中。這就是方苞所追求的簡潔而高雅的風格。第三,文章雖然簡潔,但是節奏不單調。句讀以短句為主,間有長句,最短者只有一字“曰”,最長者“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十字,其他句讀停頓,多為二字(一日、微行、及試、呈卷、召入),三字(入古寺、公閱畢、為掩戶、吏呼名、至史公),四字(風雪嚴寒、從數騎出、文方成草、叩之寺僧、使拜夫人、惟此生耳),其間雜以五字句(先君子嘗言、即解貂覆生、公瞿然注視、即面署第一)。語言節制,節奏起伏。第四,敘奇事,大抵為陳述語氣,只在結語處用語氣詞(則史公可法也,惟此生耳),情感只在關鍵處略現。所有這一切,顯然與公安派的強烈抒情、竟陵派的濫情形成對照。
文章最核心部分是史可法獄中見左光斗的場面。文章寫左公受刑之慘烈,寫史公冒險犯難拜見,左公報以怒斥。大義凜然,其精神,其氣概,可謂驚心動魄。然而,全程并無心理直接描寫,而僅寫外部效果,以可見動作和可聞之語表現。
若讓公安派來寫同樣的場景,史可法聞恩師被炮烙之慘,少不了內心悲痛之渲染,其視覺、聽覺當有令人戰栗之文。然文章只寫左公“旦夕且死”,不寫史可法內心不可見之痛,只于外在之可見效果上用名詞、動詞表現:一曰“涕泣謀于禁卒”,士人公然泣于獄卒,可想其內心之痛;二曰“卒感焉”,連獄卒都被感動了,可見其精誠,然而不見任何形容詞。至見左公,只寫“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只用了兩個可視的細節雄辯地突出其受刑戮之烈,一個“矣”字流露情感。接著寫史可法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左光斗“目不可開”,只從聲音中聽出是史可法。接下來文章寫道:
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如炬。
這里,感人的不僅僅是左光斗用了很大力氣才把眼皮撥開,更令人震撼的是居然“目光如炬”。這樣的形容顯然夸張,一個“面額焦爛不可辨”到眼睛都睜不開的人,居然會“目光如炬”。這是情感的夸張,不可能如他所說是聽來的原話,而是他詩意的想象,這就有點近于他反對的“詩歌中雋語”了。這在方苞的文章中是很少見的,但這還只是表現左光斗精神的序曲。接下來,其大義凜然更是驚心動魄:左光斗對史可法來探看,不但沒有感到歡欣和安慰,反而是憤怒:
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奸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
這種“怒”不是一般的怒,而是怒不可遏。這好像完全不近人情,居然罵冒險來探望的門生是“庸奴”,但是,這恰恰突顯其完全忘記了自己“旦夕且死”,有一種原則比之自己的生命、比之學生高貴的情誼更高,這就是左光斗所說的“大義”。按“大義”原則,他有權利如此無禮,因為:國家糜爛,危急存亡;我(老夫)已經完了,準備犧牲了(已矣),都無所謂;但是,你可是“天下事”的“支拄”;如今你竟“輕身”來此,就是“昧大義”;昧大義者,就是奸人不來構陷你,我也可以打死你(撲殺汝)。
左光斗不僅在語言上發出了威脅,而且更為動人的是,不顧目不能視,“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左光斗越是粗暴,越是顯示出他為史可法輕身入探的嚴峻后果和形勢而焦灼。這是因為,在他心目中,史可法太重要了,對于國家是唯一能支撐局面的,對于大義是唯一能力挽狂瀾的,一旦喪身則等于絕望。故方苞強調左氏粗暴,不但在行為,而且在語言。用語似乎有點接近他所反對的“語錄語”,有點不夠“雅”了。從這里,也約略可見方氏之所謂“雅潔”,所謂不用“語錄語”,是太絕對了,有時,他自己也不能完全遵守。就文章而言,這不僅不是缺點,反而表現了左氏深感危急,對史可法越是責之重、語之暴,越是顯示出他對史可法期待之殷。在寫法上,本文雖為逸事,非史家言,但是,所寫皆歷史人物,故皆遵史家記事記言之準則,左光斗精神之崇高皆在言語和行為之中。就是直接贊頌,也不是出自作者,而是史可法出來以后,對人言“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從被感者之言顯示感人者精神之烈。
三
方苞的“雅潔”實際上是對先秦六經和《論語》《孟子》的總結。應該說明的是,在先秦六經,乃至《論語》《孟子》中,只有對話和動作,幾乎沒有環境和心理描寫,故能寓贊頌于簡潔敘事對話之中。“雅潔”在他的許多成功的文章中得到相當的體現。如《逆旅小子》敘其路經石槽時,于客棧見襤褸的小兒,備受店主凌虐,訊問得知,店主乃其叔父,懼此孩成長分其家產。方苞書告京兆尹捕詰。四年后,復經此處,聞該兒已凍餒而死,其叔也暴卒。此本相當曲折情節,方苞以百余字出之。方苞聞“逆旅小子”已死,接了一句:“叩以:‘吏曾呵詰乎?’則未也。”最后只三個字,余味無窮,堪稱精致。
契訶夫云,簡潔乃天才姊妹。然而,簡潔過分,也可能變成簡陋。方苞言:“嘗謂周秦以前,文之義法無一不備。”其實,周秦以前之文,長于記言、記事,不長于描寫與抒情。方苞無視于此,故其文往往簡潔到極端,未免有簡陋之失。就是《左忠毅公逸事》這樣的杰作,也由于敘事過簡,引起后世論者質疑。如“呈卷,即面署第一”。明代的考試有相當嚴密的程序,哪里可能一看史可法的文章就定為第一。其他考生的文章看了沒有呢?其他考官參與了沒有呢?這些都省略了。
這是桐城派最經典的文章,其強調簡潔,廢棄描寫、抒情,現出了簡陋的端倪。至于其他文章,則更是顯然。如《獄中雜記》雖暴露黑暗難能可貴,但是,拘于敘述難免缺乏感染力。例如:“茍入獄,不問罪之有無,必械手足,置老監,俾困苦不可忍,然后導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為劑,而官與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資取保;其次,求脫械居監外板屋,費亦數十金。惟極貧無依,則械系不稍寬,為標準以警其余。”文章內容極其慘烈,而用語極其樸質。缺乏形象的感染力,簡則簡矣,陋則難免。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提到方苞的《望溪集》時說:“雖大體雅潔,而變化太少,終不能絕去町畦,自辟門戶。”“變化太少”,可能是說他拘于敘述對話,缺乏抒情、描寫之調節。
五四新文學運動對方苞為代表的桐城派,因其思想上以“闡道翼教”為務,故目為“桐城謬種”,成為文學革命的對象。現代散文理論之奠基者周作人,寧取法公安派的獨抒性靈,提倡“敘事與抒情”,于桐城之“義法”和“雅潔”,周作人一如方苞之于視公安派一樣,視桐城派之“義法”和“雅潔”為無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