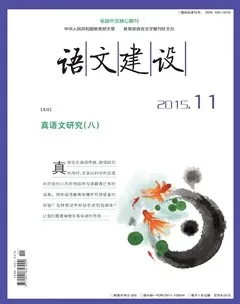品讀《山市》文筆之奇
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一向被學(xué)界視為文言短篇小說的集大成之作,代表著中國古代文言短篇小說的最高成就。其實,從嚴(yán)格意義上來說,《聊齋志異》里的作品并不全是小說。如《噴水》《尸變》《耳中人》《宅妖》《外國人》等,這類作品屬于紀(jì)實性的志異筆記,在體裁上屬于散文體,多篇幅短小,重在如實記錄見聞傳說以及現(xiàn)實生活中的奇事異行,不重視虛構(gòu)想象、人物形象的塑造等。與小說類相比,這類作品多因缺乏深刻的思想內(nèi)涵和精巧的藝術(shù)構(gòu)思而不太被人看重,但其中也有一些作品,文境虛幻相生、瑰麗奇崛,可謂風(fēng)致?lián)u曳、美輪美奐,堪稱散文中的經(jīng)典。
《山市》就是這樣一篇優(yōu)秀的志異筆記作品。它描寫的是發(fā)生在淄川縣西奐山的一次海市蜃樓的奇幻景象,文筆峭拔、意境奇特,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紀(jì)實性山水游記。全文如下:
奐山山市,邑八景之一也,然數(shù)年恒不一見。孫公子禹年與同人飲樓上,忽見山頭有孤塔聳起,高插青冥,相顧驚疑,念近中無此禪院。無何,見宮殿數(shù)十所,碧瓦飛甍,始悟為山市。未幾,高垣睥睨,連亙六七里,居然城郭矣。中有樓若者,堂若者,坊若者,歷歷在目,以億萬計。忽大風(fēng)起,塵氣莽莽然,城市依稀而已。既而風(fēng)定天清,一切烏有;惟危樓一座,直接霄漢。樓五架,窗扉皆洞開;一行有五點明處,樓外天也。層層指數(shù),樓愈高,則明漸少。數(shù)至八層,裁如星點。又其上,則黯然縹緲,不可計其層次矣。而樓上人往來屑屑,或憑或立,不一狀。逾時,樓漸低,可見其頂;又漸如常樓;又漸如高舍;倏忽如拳如豆,遂不可見。又聞有早行者,見山上人煙市肆,與世無別,故又名“鬼市”云。
全文由目擊者孫公子與同人的視點切入,記敘了山市從發(fā)生、發(fā)展到結(jié)束的全過程。清代評點家但明倫贊嘆曰:“文境之妙,此為天下奇觀。”[1]馮鎮(zhèn)巒也稱賞不已:“是古文法,短篇峭勁。”[2]
作為一篇以真人實景為描寫對象的作品,《山市》怎樣宕開寫實的局限,在文境上被激賞為“天下奇觀”的呢?
“筆翻空則奇,局逆振則險。”文章開篇點題,指出奐山山市為淄川著名的八景之一,但是多年不遇,“恒不一見”,起筆峻峭突兀,也為下文的奇幻展現(xiàn)埋下伏筆。“忽見”一詞如閃電霹靂劈空而來,形象地指明了目擊者在沒有任何心理準(zhǔn)備的情況下相顧驚詫的神態(tài)。文章按時間順序,像電影鏡頭一樣依次展示了十二個變幻莫測的奇幻場景:山頭孤塔聳立;數(shù)十所宮殿碧瓦飛甍;高垣連亙六七里;億萬樓若、堂若、坊若歷歷在目;大風(fēng)起,城市依稀;風(fēng)定天清,一切烏有,惟危樓一座,直接霄漢;樓五架;樓外天;層層指數(shù),數(shù)至八層,裁如星點;其上黯然縹緲;樓上人往來屑屑;遂不可見。這些場景的轉(zhuǎn)換通過“忽見”“無何”“未幾”“忽”“既而”“逾時”“倏忽”等一系列時間副詞綰結(jié)起來,流轉(zhuǎn)自然,毫無生澀之感,而且還將目擊者驚疑嘆奇的心理變化糅合其中,既突顯了幻景隨著時間流動而發(fā)生的動態(tài)變化,又將目擊者的心理變化暗寓其中,動靜結(jié)合、虛實相間,生動傳神地刻畫了一幅千載難逢、瑰麗超拔的藝術(shù)奇觀。
真正的文學(xué)高手慣于弄險,從而將作品提升到一種“奇”“險”的絕佳境界。被譽(yù)為“七言圣手”的王昌齡藝高膽大、善于弄險,他的詩歌起調(diào)時就比較高,高度逐漸攀升到“轉(zhuǎn)”的時候已經(jīng)險極,作者卻能借著生花妙筆就勢一振,在造成雷公砰訇一般的震撼效果之后又能巧妙地回到原點,從而使作品產(chǎn)生一種大起大落、蕩氣回腸的震撼效果。
《山市》在謀篇布局上與王昌齡的詩歌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但明倫為它云詭波譎的文境所嘆服,稱它為“奇文”:“忽然碧瓦飛甍,忽然城郭連亙,劈空而來,超拔可喜。中間樓若者,堂若者,坊若者,以億萬計,填實飽滿,矞麗堂皇。忽而大風(fēng)吹去,城市依稀,則填實中仍是空中落想,不著跡相。繼而掃除一切,危樓一座,天外飛來,縹緲虛無,是空是色。然后返虛入渾,化實為虛,色相皆空,筆墨皆化為煙云飛去。”[3]馮鎮(zhèn)欒也有同樣的感受:“一變……略頓……又一變……又一變收場……另換一局作余波收”[4],對文章的屈伸、波瀾和突轉(zhuǎn)等藝術(shù)技巧給予了很好的解讀和評賞。
山市,是一種罕見奇幻的自然景觀,多發(fā)生在海邊或沙漠地區(qū)。科學(xué)界認(rèn)為它是因光線經(jīng)不同密度的空氣層發(fā)生折射時,把遠(yuǎn)處的景物神奇地顯示在空中或地面產(chǎn)生的景象。孤峰疊翠、景色奇特的淄川奐山就是這樣一個多次被歷史記載有山市發(fā)生的地方。明嘉靖版《淄川縣志·山川》載:“煥山:在縣治西四十里,古有煙火臺,爛然有光,故名。今廢址尚存,時或有山市發(fā)見。”清代乾隆版和民國版的《淄川縣志·山川》對奐山的山市也有相關(guān)的記載。康熙四十一年(1702),淄邑人趙金昆在河中洗澡,見到了奐山山市并寫文記之;康熙二十六年(1687),奐山山市在農(nóng)歷六月初五和初七兩天神奇地相繼出現(xiàn),目擊者有不少當(dāng)時淄川的文化名流,如張嵋、唐夢賚、畢際友、袁藩、張紱等人。
蒲松齡為淄川本地人,老家距離奐山不遠(yuǎn),應(yīng)該說他對此地非常熟悉和熱愛。除《山市》外,他還有不少描寫奐山的作品,如《奐山道上書所見》《奐山道中》《奐山小憩》等。作為一名作家,奐山山市的神秘莫測、虛無縹緲給了他創(chuàng)作的文學(xué)動力,而作家豐厚扎實的文學(xué)功底更讓這篇紀(jì)實性的作品在虛實正奇的藝術(shù)構(gòu)思上達(dá)到了一種從心所欲的境界,從而使這篇作品超越了《聊齋志異》其他紀(jì)實類志異筆記的文學(xué)局限,整篇都折射出浪漫主義的奇光異彩。這也是在眾多描寫奐山山市的作品中,《山市》能夠勝出、成為群英翹楚的原因所在。
奇幻與現(xiàn)實的緊密結(jié)合,虛實相間的藝術(shù)手法以及絢麗旖旎的浪漫主義風(fēng)格構(gòu)成了《山市》文境之妙的多重藝術(shù)魅力,讓歷代讀者久久回味、神以遠(yuǎn)行。今天在我們的寫作教學(xué)中,有不少教師在一些具體的問題面前,如作文如何創(chuàng)新、如何處理虛與實的關(guān)系等,感到非常棘手和困惑。無疑,《山市》在這些方面給我們帶來很多藝術(shù)技巧上的啟發(fā),值得我們借鑒和深思。
參考文獻(xiàn)
[1][2][3][4]蒲松齡.聊齋志異:全校會注集評本[M].任篤行輯校.濟(jì)南:齊魯書社,2000:1276,1276,1276,1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