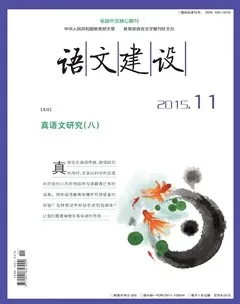民國時期中學國文教育的文學意味
1927年6月汪懋祖奉江蘇教育廳令,接收江蘇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改組舊有教育資源以組建蘇州中學,同年7月5日汪懋祖被任命為蘇州中學校長。因而本文討論的時間范圍亦從汪懋祖1927年出任蘇中校長到1931年辭職為止。
汪懋祖對蘇州中學的定位和期待很高,“蘇中規模大,人才多,實可作為一個實驗中學”[1],這可從兩方面來看。第一,汪懋祖早年留學美國,入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獲碩士學位;學成回國后,汪懋祖先后在國內多所大學任教。這樣的履歷使他有能力在蘇州中學進行試驗。第二,汪懋祖于國文教育尤為重視,因此蘇州中學國文教師的師資力量十分雄厚。錢偉長于1928~1931年就讀蘇州中學,對當時蘇州中學的師資有這樣的回憶:“蘇高中成立后,校長、教師都是新聘的,理科教師幾乎清一色都是東南大學的講師,文科教師都是在地方上聘的,像我的四叔國學大師錢穆就被聘為國文首席教師,沈同洽是英語首席教師,楊人楩是歷史首席教師,還有呂叔湘等,后來這些人都成了國內各大學的名教授。”[2]
一、文言教學與“學術化蘇高”
汪懋祖任職蘇州中學,結合教育實際,貫徹其“新儒家的教育思想”。創辦之初,汪懋祖要求不僅高中生、初中生讀文言文,小學高年級的學生也應該學習淺近的文言文,且重視文言寫作。汪懋祖在《蘇中校刊》的發刊詞中提及他的辦學思想,“不佞思欲上紹范文正,胡安定之學風,旁求歐美各中校之精華”[3],即希望辦一所汲取中西文化之長的中學。汪懋祖在為蘇州中學擬英文名時特意選定“Soochow Academy”,意在彰顯和實現其“學術化蘇高”的辦學理念。他在《蘇中事業之回顧與展望》一文中提到:“一個優良學校成績的表現,不僅在畢業生多數能考取大學,或中學會考能得到錦標,而在入學后能獨立研究學術,崇高人格,出大學復能發展其能力,以各得其用,此亦清醒的教育者所當注意的。”[4]
由于這種推崇文言文教學和“學術化蘇高”的教學理念,國文教師的國文功底頗高。汪懋祖選聘的國文教師或為前清秀才、貢生、遺老的及門弟子,如李希文曾是前清的貢生;或為地方中學和師范學校的老師,如無錫三師的錢穆;還有三位大學教授,吳梅、陳去病(歷任全國多所大學教授)、李崇元(曾為金陵大學教授)。[5]
二、國文教學述論
蘇州中學對國文學科的界定為“國文學科:凡國語、國文、國學等均屬此科”[6]。蘇州中學在國文學科設立后,依據教育部頒發的課程標準,結合當時實際情況,“明確目標、選擇教材、規定進度、研究方法、布置作業與交流經驗”[7]。在此基礎上,國文一科進一步制訂《江蘇省立蘇州中學學程綱要》(以下簡稱《學程綱要》)、《江蘇省立蘇州中學教學概況》及《江蘇省立蘇州中學各科教學進度表》,以達到各年級之教材、目標、進度、要求的統一;并注重各年級之間的相互銜接,使得初、高中國文教學有一個整體的掌控和梯度的認識。1930年編訂的《學程綱要》對初高中必修“國文”科具體的教學目標,有明確的記錄。
初中之部:
1.使學生通解普通語言文字的意義及應用。2.使學生有自由發表思想、情感,及記述見聞的技能。3.培養文學的欣賞。4.指導課外閱讀,使略具關于中國文字學術之普通知識;養成其自動研究的能力。
高中之部:
1.使學生明了中國文學源流及各種文學體裁的大概。2.繼續增進其自由發表及記述的技能。3.培養欣賞中國文學名著的能力。4.繼續指導課外閱讀,使學生明了中國學術思想變遷的大概,并養成其自動研究國學的基礎。[8]
在具體實踐過程中,初高中的國文教學主要分課內教學和課外教學,課內教學以單篇文章教學為主,課外教學主要是名著閱讀。總體來說,初高中國文教學主要為精讀、略讀和習作三大塊,輔之以臨時測試,但教學重點在精讀方面。
精讀方面,初高中教材的選文標準要求是:
關于內容方面:一、能啟發或補助知識及思想者。二、足以激起青年向上精神,及鼓動其人格上的感應者。三、對于研究中國文學學術大體上有關系者。四、足以發揚民族精神不背時代潮流者。
關于形式方面:一、記事文能切實描寫,不落虛泛者。二、說理文能透辟發揮,不落陳腐者。三、音節諧和能耐誦賞者。四、辭意不背邏輯者。[9]
為了論述方便,本文只討論高中國文教學情況。
高中部選文(精讀文)篇目在內容與形式方面各有側重。選文方法為“凡近人文章傳記以及批評群經諸子關于學術思想者,不論語體文言,一概得以選授”[10]。選文的文體兼顧記事、說理、抒情三類,且三學年中記事文、抒情文的比重逐年下降,說理文的比重逐年上升。高中三年總體上分為集部、史部、經子三大類,每學年以其中一類為中心,同時兼顧其他兩類,以明思想變遷與文章流別。
第一學年,選歷代名著,以集部為主,而子史間亦附之。記事文,說理文,抒情文,其量的比例為4與3,3與3。第二學年,選左傳國策史漢通鑒以下文字,以史部為主,而集部關于典志碑傳等巨著,子部關于古史者附之。記事文,說理文,抒情文,其量的比例為4與4,4與2。第三學年,選六經諸子,及宋明理學,清儒考證各家文字,以經子為主,而史部集部與之有關系者附之。記事文,說理文,抒情文,其量的比例為3與5,5與2。[11]
高中部第三學年教學范文篇目具體如下:
經子文,詩谷風,采薇,伐檀,蓼莪,黃鳥,七月,東山,蒸民,常武,采芑,車攻,斯干,尚書堯典,甘誓,湯誓,牧誓,無逸,秦誓,易下系庖犠氏一節,禮記大學,禮記中庸節,左傳隱公不書即位,公羊傳隱公不書即位,谷梁傳隱公不書即位,儀禮士相見禮,周禮大司寇,考工記梓人,莊子秋水篇,齊物論,天下篇,荀子天論篇,性惡篇,正論篇選,議兵篇,老子選,韓非解老,喻老,難一,難二,和氏篇,墨子兼愛上,非攻上,孟子神農之言章,好辯章,孔子在陳章,論語選,呂氏春秋察傳,又別類,孫子形篇,公孫龍白馬論,跡府。
史與集附,史記孔子世家節,老莊申韓列傳,商君列傳,呂不韋列傳,孟子荀卿列傳,屈原賈生列傳,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屈原九歌,荀子賦篇,柳宗元論語辨二首,王安石論老子,朱熹開阡陌辨,蘇軾秦穆公墓,王守仁大學問,答顧東橋書(拔本塞源之論節),夏曾佑嚴評老子序,章炳麟齊物論釋序,孫詒讓墨子傳略,俞樾讀經偶得,汪中荀卿子通論,汪中呂氏春秋序,姚鼐讀孫子,吳汝綸寫定今文尚書二十八篇敘。[12]
高中部教材每學年在內容和形式上各有變動,依文學史的體例,結合集部、史部、經子部及近人傳記、評論學術思想等文章來講授,使學生具備欣賞古典文學的能力。這種設計理念貫徹了蘇州中學國文教育的理念——重視文言文,注重情感熏陶,且以說明文為主,培養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給學生打下了良好的國文根基。
上述教材范文篇目的選擇,是針對國文必修學程而言的。選修學程中,高中部的文字學、學術文、國學概論、美術文等學程,依照各學程的教學目標依次設定。內容或為授課教師自行編訂,分節講授,或為框定篇目,自行擇取。例如,文字學教材內容分六節:文字之本源、文體之組合、文字之運用、文字之淘汰及增添、文字之改革及因襲、文字之比較,由教師自編講義。學術文教材框定在以下篇目的文章中: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梁啟超《治國學的兩條大路》、朱熹《大學章句序》、司馬遷《論六家要旨》、莊周《莊子·馬蹄篇》等,授課教師自行取舍。國學概論分十節講授:孔子與六經、諸子學之源流、秦人焚書坑儒、兩漢經生今古文學、晚漢之新思潮、魏晉清談、隋唐之佛典翻譯及經學注疏、宋明理學、清代考證學、最近期之學術思想。美術文分體選材,分詩、詞、曲、駢文四類,詩選漢魏晉宋、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宋元明清朝有代表性的詩歌或名家名篇;詞北宋取晏殊父子、柳永及李易安,南宋取姜夔、辛棄疾;曲取元人小令、元明套數雜劇;駢文選六朝的徐陵、庾信,清朝的胡天游、邵齊壽等。應用文教材綱要為公牘、函簡、契約等。文學史自編講義分八節講授,上古先秦至明清近代各時期的文學流派、學術思潮及代表作品。古書示要自編講義,分經子古史依次教授。國學問題選取近代討論國學問題的文字和著作,要目為古史討論、諸子、宋學與漢學等。兒童文學的教材內容主要是《兒童文學是什么》《兒童文學教育的實施》《兒童文學研究法》等,圍繞兒童教育來設定。[13]選修學程的教材內容依然是圍繞必修學程的教材內容來設定,充實教材內容,拓展延伸必修學程的不足。選修與必修學程相結合,共同為完成國文一科的教學目標服務。
三、《蘇中校刊》中的國文實踐
汪懋祖另一項重要措施是創辦《蘇中校刊》,為師生的研究成果尋求一個發表的平臺,目的是將本校的辦學情況通過校刊公諸社會。1927年至1931年上學期結束,《蘇中校刊》共編輯出版54期,主編幾次變更,第1~9期胡哲敷編,第10~16期烏翰芳編,第17~22期汪懋祖編,第23~54期沈佩弦編。雖然幾易主編,但編輯的宗旨一脈相承,校刊的欄目亦大體保持一致。校刊每期固定的欄目有《講演》《論著》《校聞》《文藝》,其他隨即變動的欄目有《布告》《筆記》《公牘》《專件》《雜俎》等項。這些欄目與國文教育有關的主要是講演、論著和文藝三大項。《講演》一欄主要登載本校教師和社會名人在蘇州中學做的演講講稿;《論著》一欄主要刊登本校教師和學生的研究成果;《文藝》一欄為師生發表文藝作品的陣地,最能反映蘇州中學濃厚的國文教學風氣。以內容而言,校刊中有關國文教育的文章大致分散在文哲類、教育類、社會科學類和文藝類中。據《蘇中校刊》第84、85兩期合刊載“《蘇中校刊》總目錄分類統計”[14],以上四類文章細分情況大體如下:文哲類涉及哲學及人生問題(11篇)、經學及小學(8篇)、史地學通論(2篇)、諸子(7篇)、文學通論(13篇);教育類文章主要關于中學國文教育(3篇);社會科學類有歷史及現代問題(3篇)、社會問題(1篇);文藝類較繁多,有序跋(19題)、散文(35題)、新體詩(15題)、韻文(107題)。為方便分析,筆者將前54期中有關國文教育的文章做了簡要歸納。
1.文哲類
這一類文章有關哲學及人生問題,共11篇,講演4篇,論著7篇,有社會名人的講演、本校教師的著作、校內學生的論著。講演有胡適的《我們的生活》(第1期)、《科學的人生觀》(第8期)等。本校教師著作有沈佩弦的《美和善怎樣是神秘底統一的》(第26期)等,學生著作有徐貴基的《希臘的哲學科學和文學底研究》(第13期)等。
經學及小學一類的文章共8篇,全部為論著,刊登本校教師和學生對經學小學問題的研究。本校教師作品有錢穆的《易經研究》(第17期)、沈昌直的《詩經言字解駁胡適之》(第1期),學生作品有張渭璜的《一點兒國學常識》(第43期)、成彭的《詩經研究——左傳五鳩考》(第43期)。
史地學通論有顧頡剛的講演《對于蘇州男女中學史學同志的幾點希望》(第21期)、戴增元的《班史傳儒林不傳文苑》(第10期)。諸子類7篇論著,師生作品皆有,錢穆的《墨辯碎詁》(第11期)、《惠施歷物》(第43期),學生錢小云的《申韓之學本于黃老》(第16期)。
文學通論一類共13篇文章,講演2篇,論著11篇。這類文章涉及對中國文學史上個人、流派、思潮等的研究,既有教師著作也有學生的研究。教師有吳瞿安的《清代辭章家略說》(第20期),諸祖耿的《李長吉研究》(第26、29期)等,學生有霍森源的《中國文學之特點》(第43期)等。
2.教育類
教育類主要談的是中學的國文教育,1篇講演,2篇論著,內容上主要是對中學國文教育的具體看法和教學上的經驗之談。吳瞿安的《對于中學國文的我見》(第9期)主要談對當前國文教育的看法,指出不足之處,認為今不如昔;張圣瑜的《一個中等學校國文教學法綱要》(第8期)介紹了作者在國文教學法上的幾點經驗,對讀文、讀書、考試在選文、授課、課內外指導及考查方法上的具體操作,做了綱要性的簡介;戴增元的《本校三周年國文學科教學概況》(第48期),對蘇州中學創校以來的國文教學情況,從教學目標、教材選擇、教學方法上做了清晰的描述。
3.社會科學類
關于歷史和現實問題的有3篇論著,錢穆的《述清初諸儒之學風》(第2期),學生從書一的《晉與漢末學風迥殊之原因》(第43期)、陸長康的《滿清衰亡之原因》(第13期);關于社會研究的有學生王鴻基的《文學化的吳江俗諺》(第43期)。這類論著就傳統學問和現實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并對地域鄉土的語言文化的演變進行調查和探索。
4.文藝類
文藝類分為序跋、散文、新體詩、韻文四種。序跋共19題,相對散文韻文而言,文學價值稍弱。如汪懋祖等人為校刊開專號、為同人著作等做序言,簡言事務緣起及意義,簡介書的內容及價值,有《蘇中校刊發刊詞》(第1期)、《周年紀念特刊弁言》(第14期)、《高中英文選序》(第24期)、《張著兒童文學序》(第5期)等。
篇目統計散文35篇,教師文章僅5篇;新體詩15篇皆為學生習作;韻文107篇,教師53篇,學生54篇。就文體而言,偏重舊體詩詞,現代文也有涉及,但數量少。散文、新體詩、韻文以文章主題分大致可劃為五個方面:游記、詠嘆、唱和、贈別、偶感,且五種主題時有交叉。附錄各類主題的詩歌各一首。
游記類:《游杭雜詠——過岳墳》(學生:張渭璜)(第46、47期合刊)
傷心胡馬半神州,不抵黃龍誓不休。偏有奸臣陰矯詔,滿腔熱血付東流。
詠嘆類:《漁家樂》(學生:劉樸齋)(第9期)
全家穩住一扁舟,水面生涯亦自由。荻港蕭蕭移棹去,沙鷗點點逐波流。幾番沉醉斜陽里,一曲高歌古渡頭。解纜歸來天色晚,滿江新月正如鉤。
唱和類:《和楊又時先生戊辰歲朝例詠》(學生:許自誠)(第6期)
詩情真摯自能工,著意雕鏤總是空。佳句每從無意得,太平僅與夢中同。文章經國方稱富,書畫怡情不算窮。滄海橫流何所懼,阿儂收去實詩筒。
贈別類:《秋夜贈雪聰寒云》(學生:曹樹勛)(第43、44兩期合刊)
離人情緒亂如絲,寥落秋心枉自馳。客地月明孤館夜,鄉關夢斷五更時。幾多往事隨流逝,添得新詩寄與誰?底事凄涼愁不寐,一天星斗共愚癡。
偶感類:《讀書雜感》(教師:沈穎若)(第5期)
傳家產業不祥物,多少青年誤此中。能聚不如能散好,伏波畢竟是英雄。
從《蘇中校刊》登載的大量舊體詩詞而言,師生試做舊體詩詞篇數之多、題材之廣,可說是同類各種中學校刊所少見。雖然從技法與質量而言,并不見得上乘,但這種創作熱情反映該校熏習傳統熱情之高漲,亦見出提倡者的有意引導。
四、余論
由以上梳理與分析可見,蘇州中學(1927~1931)國文教育偏于傳統文化的熏染,這種局面的出現與汪懋祖的提倡有莫大關系。早在1918年第5卷第1號上汪懋祖發表《致〈新青年〉的通信》,對《新青年》倡導新文學而又不許反對者“討論是非”表示不滿。1919年汪懋祖又在《留美學生季報》第6卷第1號上刊登《送梅君光迪歸圜橋序》(該文又刊于1922年4月《學衡》第4期)就明確表示和梅光迪意見一致,反對新文化—新文學運動,汪懋祖對吾國學者“洎于既狹且卑之實利主義。論文學則宗白話,講道德則校報施”表示不滿,因為新文化運動導致數千年先民之遺澤摧鋤以盡,中國人的靈魂也喪失了。[15]后來汪懋祖參與“學衡派”,在理念與思想上認同傳統。待其掌校蘇州中學,汪懋祖更是不遺余力推行傳統文化教育。從制度到課程設計,傳統文化色彩極為濃厚,師生合力,不但講授經史子集,而且試做舊體詩詞。雖然蘇州中學的課程設計有白話文的內容,也會根據學生學力情況,在初中階段涉及現代小說、傳記、散文等類別,高中階段略讀文部分涉及梁啟超、魯迅、胡適等現代作家的內容,但這些改變不了蘇州中學重視傳統文化教育的性質。筆者曾翻閱大約處于同一時期出版的中學校刊,如《溫州中學校刊》《江蘇省立徐州女子師范學校校刊》《香港華南中學校刊》《振華季刊》《南開高中學生》《松江女中校刊》《廣東省立一中校刊》《上海女中校刊》《安慶女中校刊》《協和湖》等,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像《蘇中校刊》如此大規模刊登師生傳統文化(經史子集)研究論文、舊體詩詞習作的可謂較少。
早在1918年4月10日胡適答盛兆熊信坦言白話的實際影響不大,“我們現在沒有那么大的權力可以把大學入學的國文試驗都定為白話”,并舉例說現在政府通電、文告都用文言。[16]胡適所言不虛,不但將大學國文定為白話困難,就是中學國文教育也難得盡變為白話,蘇州中學的國文教學實際情況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按照何兆武的說法:“白話文到今天真正流行也不過五十年的時間,解放前,正式的文章還都是用文言,比如官方的文件,研究生的畢業論文大都也是用文言寫的。除了胡適,很多學者的文章都用文言,好像那時候還是認為文言才是高雅的文字,白話都是俗文。”[17]何兆武雖是事后回憶,但大致情況確實存在。揆諸實際,民國大學新文學之所以難進課堂,除師資一方面原因外,我們從蘇州中學的國文教育實際情況可看出,學生素質其實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素。若果學生在中學階段完整熏習經史子集,進一步深造后,由于之前接觸新文學、白話訓練較少,缺少情感與思維的訓練,加之新文學自身的不足(學問因素較稀薄等),想親近恐怕也是難事。
參考文獻
[1]汪懋祖.蘇中事業之回顧與展望[J].蘇中校刊,1933(86).
[2]錢偉長.難忘蘇中:《百年蘇中》序言[M]∥胡鐵軍主編.百年蘇中·三元春秋.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5.
[3]汪懋祖.《蘇中校刊》發刊詞[J].蘇中校刊,1928(1).
[4]汪懋祖.蘇中事業之回顧與展望[J].蘇中校刊,1933(86).
[5][6][7]參看金德門主編.蘇州中學校史(1035~1949)[M].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121,84,121.
[8][9]江蘇省立蘇州中學學程綱要[S].蘇州三元坊蘇州中學總部,1930:1~2,2~3.
[10]江蘇省立蘇州中學教務處編.江蘇省立蘇州中學教學概況[Z].江蘇省立蘇州中學,1932:8.
[11][12]戴增元.三年來國文學科教學概況[J].蘇中校刊,1930(48/49/50合刊).蘇州中學高中三學年都極為重視文言文教學,筆者此處只節錄高中第三學年學習范文。這些范文教師必須在課堂上講授。
[13]筆者根據1930年出版的《江蘇省立蘇州中學學程綱要》綜合歸納而來。
[14]本文統計數據來自第1至54期《蘇中校刊》,并不包括之后所出期刊。
[15]詳細論述可參考沈衛威.“學衡派”編年文事[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
[16]胡適.胡適全集:第23卷[M].鄭大華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197.
[17]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寫.上學記:修訂版[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