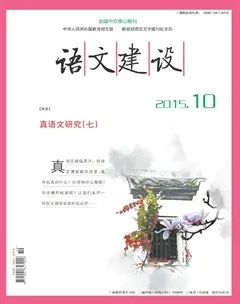找準語文教學的切入點
語文教學的切入點,是課堂教學展開的發起點,是閱讀教學思路的起始點,是教師在深入的文本解讀中找尋到的文本關節點,也是教師帶領學生走進文本世界的最佳入口。因此,有人說:“它不是隨意的靜態孤立的點,而是有條件的動態聯系的點,從這一點出發,能向教學各部分發散、輻射,教學各部分也可以向這一點聚攏、集中,它有著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顯著特征。”[1]復旦大學附中黃玉峰老師說得好:“課堂教學的成功,必須有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對所教文本的熟悉,二是找到破譯文本的突破口。”找準突破口即找準切入點,是課堂教學成功的一個重要條件。
教學切入點的選擇,是教師文本解讀的結果。教師只有在深入解讀文本的基礎上,才會找到合適的、科學、巧妙的切入點。高明的教師在備課時,總是先對全文的字詞進行梳理,對全文的關鍵語句寫出鑒賞評價,對全文的結構、手法進行全面的分析之后,再來思考教學的切入點。
教學切入點的選擇,體現了教師的教學技巧。面對文選型教材,一篇文章教什么,從哪里開始教,決定著課堂效益的高下。如果找到一個合適的切入點,就可四兩撥千斤,帶動全文的閱讀,能夠激發學生的閱讀興趣,從而更好地引導學生走進文本中去。
一、教學切入點選擇的原則
1.基于言語特質
“語文課程的人文性蘊含在工具性中,要緊扣字、詞、句、段、篇教語文。語文教學要致力于培養學生的語言文字應用能力,提升學生的綜合素養。”[2]語文與歷史、政治等學科不同,歷史、政治等學科通過語言文字這個憑借了解內容后,即可徑直進入學科知識的討論和生發。語文則不行,語文學習是在“言語形式—言語內容—言語形式”的循環往復中涵養語感,豐富情感。確切地講,語言文字在這里絕不單單是一種了解內容的“工具”,語文教學中的“語言”既是“形式”又是“內容”。[3]最近幾年的課堂教學中的確出現了淡化語文知識、輕視語言訓練等傾向,這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語文學科主體的迷失。因此厘清語文教學中言語形式與言語內容的關系,不僅是教學切入的思考起點,也是整個教學的邏輯起點。
2.依據體式特點
王榮生認為,閱讀教學就是教閱讀方法,閱讀方法源于體式特征。這里的體式特征,一是指文本作為特定體裁類別的特征,二是指文本作為“這一篇”所獨有的特征。古人作文尤其講究體制,認為“文章以體制為先”,寫作之前“宜正體制”,寫作之后要“不失體裁”“。茍舍制度法式,而率意為之,其不見笑于識者鮮矣,況文章乎?”[4]古人作文重體式,作為讀者要理解文本,也應以體式為切入口。閱讀教學應從文體的角度入手,重視學生內隱言語的建構圖式。現代心理學的認知圖式理論認為,人之所以能識別事物發現規律,是由于長期貯存于大腦中的事物演變的圖式。圖式就是對事物和事件的一般特征的概括。圖式能將知識系統化、結構化,形成有意義的內隱言語知覺模式。這種內隱言語圖式的建構,離不開必要的文體感知和認同。小說可從環境、情節、人物切入,新聞可從標題、導語、主體、背景、結語切入,散文可從借景抒情、借物寓人、象征等表現手法切入,戲劇可從矛盾沖突切入。當然,借鑒學術界最新的研究成果進行語文知識的更新,已經成為語文學科建設的當務之急:詩歌可以引入隱喻、復義、跳躍、錯位等,散文可以引入情思、理趣、格調、氣勢等,小說可以引入敘述視角、形象變形、復調小說、文本互涉等,這些正是語文教育研究與實踐需要努力的方向。
如一位教師在執教《合歡樹》時,從散文的“有我”散文重在表達作者對世界感悟的情思)這一體式特征來引導學生體悟作者是如何表現情感的,讓學生學會讀散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3.根據學情
新課程倡導以學定教,這既是文本解讀的原則,也是教學切入點選擇的原則。作為教學的解讀,與一般讀者解讀的最大區別,就是要根據學情來對文本內容進行篩選、過濾,從中選出適合教學、適合學生的教學內容,而教學切入點的選擇,更是離不開學情。因此教學要弄清學生的知識基礎、能力現狀和情感認知發展需要,找準學生學習的最近發展區,以最優化的教育策略恰當切入,架起學生、文本、教師互動建構的立交橋。具體地說,從學生出發選擇切入點,首先要以學生的需要為目標,以教材為依托,系統把握,面向所有學生。其次要尋找學生求知的興奮點、教材與學生生活的連接點,引導學生運用所學的知識、方法,解決生活中的問題,探究文本對話的摩擦處、矛盾處、困惑處。
如王君老師在執教《老王》時,依據“當下的這一代孩子難以進入‘老王’的世界”這一學情,及時改變切入點,從老王“靠著活命的只是一輛破舊的三輪車”——這種“活命”展開生命的對話,讓學生理解老王被社會遺棄的痛苦、沒有家人的孤苦,從而激活了學生的認知和情感需求,激活了課堂。
二、明確教學切入的落點
教學切入點的選擇從哪些方面著手?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
從文眼切入。文眼是文章的核心和關鍵所在,比如魯迅《社戲》中的最后一段文字:“真的,一直到現在,我實在再沒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戲了。”可以由此切入,提出問題:那夜似的好戲真的好看嗎?進而觀照全篇。
從關鍵的詞句段切入。關鍵詞或關鍵句指的是能夠集中揭示中心、表達感情、塑造人物形象、展現文章風格的詞語或句子,是一篇文章的神經中樞或信息節點,具有發散和貫通文章的作用。常見的切入課文的關鍵句有起始句、主旨句、過渡句、矛盾句、總結句、蘊藉句等。關鍵段指表達文章中心、揭示作者情感、彰顯文章藝術特點的精要語段,連接文章的過渡段以及文章的首尾段。教學切入時抓住重點語段,可以化繁為簡,重點突破。如《孔乙己》末尾一句:“我到現在終于沒有見——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李鎮西老師在執教此文時即以此切入,引導學生思考孔乙己到底死了沒有,進而追述決定人物命運的因素是自身和周圍的環境,孔乙己自身的性格如何,周圍的人又如何,沿波溯源,從而帶動全文的理解。
從線索切入。無論何種文體的文章,都有一定的行文思路及線索。線索可以是時間、空間、情感、事物等。線索提示行文方向,標示作者思路,串聯組成課文的豐富材料。從線索切入,可使散珠成串,綱舉目張。如教學朱自清的《春》時,可以從盼春—繪春—贊春的線索切入,讓學生感受作者對春天的情感。
從主旨切入。文學文本總是有一定的主題傾向,有的主題顯豁,有些主題模糊、多元。教師可以直接提出對文本的多元理解,引導學生進行思辨,從而理解文本內容。如王鼎鈞的《那樹》,就有環保意識、生命意識、親情意識、文化意識等多元的主旨,教師可以在上課伊始直接呈現給學生,讓學生讀文談觀點,并從文中尋找證據來支撐,形成爭鳴,達到投石湖心的效果。
從結構切入。任何文章都有其獨特的結構形式,從文章的結構切入,有利于引導學生了解作者的思路,了解段與段之間、段與篇之間的關系,理清敘述順序,把握重點內容。如余映潮老師在教學《記承天寺夜游》時,就讓學生將課文變形,即將原本只有一段的課文重新編排段落,經過討論,學生按敘事、抒情分為兩段,按記敘、描寫、抒情分為三段,按起、承、轉、合分為四段,通過這樣的切入,學生快速把握了全篇。
三、探尋教學切入的方法
1.質疑切入
學貴有疑,質疑是有效閱讀的手段。進入閱讀狀態的學生,總會發現文章的疑點,這些疑點有的被學生消化了,有的卻遺留在學生腦中,這些問題最適合作為教學的切入點。一位教師在執教《范進中舉》時這樣切入:結合課文內容,你能推測范進中舉時的年齡段嗎?一石激起千層浪,學生個個埋首于課文,試圖找出答案,當細尋卻無功而返時,更激發了他們的求知欲。學生競相回答,結論也頗有些道理。在一片爭議之后,當教師把原著中范進中舉的實際年齡“54歲”寫在黑板上,學生看后有驚喜、有失望、有不解,但最終都歸于一種表情——不可思議的驚訝。“那他考了多少年啊?”“他幾歲開始考的啊?”“他為什么考那么多年還不放棄啊?”……諸如此類的疑問層出不窮。
2.比較切入
比較能夠引發學生的深層思維,教師通過呈現與文本主題、技巧相關聯的材料,讓學生對文本進行比較閱讀,能引發學生對內容的探究、對語言的品析,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如一位教師執教《羅布泊,消逝的仙湖》時,首先就呈現了《辭海》關于羅布泊的介紹:
蒙古語稱羅布諾爾,意為“匯入多水之湖”。古稱蒲海、鹽澤、洛普池、澤。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塔里木盆地東部、若羌縣東北部。孔雀河從北面注入,呈葫蘆形,面積3006平方公里,湖面海拔768米。由于河流改道及上游灌溉引水,湖水逐漸枯淺和干涸,沿岸鹽澤廣布。
之后再讓學生結合課文閱讀思考:羅布泊湖水的介紹、河流改道及干涸的介紹,又是怎樣的?寫法有什么不同?從而激活了課堂。
3.情境切入
情境切入是指在學生不易理解文本內容、缺乏有關背景生活表象、難與文本形成有效對話的情況下,教師通過多媒體圖像、語言、活動等方式,營造一個形象的場景,使學生能夠快速進入文本的方式。比如學習《安塞腰鼓》,學生對黃土高原的這種民族風情不太了解,就需要通過視頻來豐富學生的表象認知,從而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文字。
4.目標切入
佐藤學在《靜悄悄的革命》一書中把課程分為階梯型課程和登山型課程,其中階梯型課程的教學環節體現為:目標—達標—評價。上課伊始即展示目標,給課堂學習定向,讓學生心中有數,知道學什么,能夠大大提高學習的效率,這也是很好的切入方法。如余映潮老師執教《云南的歌會》即采用此種方法切入:
我們今天學習的這篇課文,有人說了這樣三句話來評價它。第一句話,這篇課文的特色是多么鮮明啊!第二句話,這篇課文的片段描寫是多么生動啊!第三句話,這篇課文表現的生活是多么有趣啊!我們今天的學習就圍繞這三句話來進行。
之后課堂就圍繞這三條目標,逐條分析。整堂課顯得簡明清晰,不枝不蔓。
教學切入點的選擇與實施,表面看是教師的一種教法,實際卻是學生的一種閱讀方法、閱讀路徑。教學切入點選好了,學習就變得輕松高效了。
參考文獻
[1]付煜.語文閱讀教學切入點研究理論探索與實證[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04.
[2]聚龍宣言[J].語文建設,2013(1).
[3]李衛東,榮維東.課堂導入語與教學切入點的設計策略[J].語文建設,2007(4).
[4]劉九洲,張聲怡編.中國古代寫作理論[M].華中師范學院: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