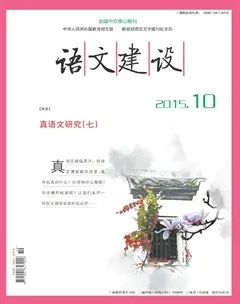“文何以載道”才是語文教學的大道
語文課應當教什么?
這是問題嗎?可這似乎不是問題的問題卻偏偏出了大問題。一位教師教鄒韜奮《我的母親》,不厭其煩地進行母愛教育,就是不引導學生學習作者是如何表達母愛和自己對母親的愛。一位教師教《本命年的回想》,課堂上討論的是過年的風俗,就是不研究課文如何寫過年的風俗。一位教師教《中國石拱橋》,作業竟然是為家鄉設計一座拱橋。有質疑者說:“這是語文課,還是橋梁專業的設計課?”
他們為什么這樣教語文?因為他們誤將課文的內容當成語文教學的內容。殊不知,課文的內容與語文教學的內容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語文教學的主要內容應當是用什么樣的語言形式來表達思想情感。也就是說,“文何以載道”才是語文教學的主要內容,才是語文教學的根本大道。這是一個頗有哲學意味的話題。
語文教學的材料是一篇篇課文。任何文章都是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形式與內容的關系是語文教學的根本問題,或者說,形式與內容的矛盾是語文教學的基本矛盾。
然而,語文教學中形式與內容的關系,與社會上一般人讀文章時形式與內容的關系不一樣。一般人讀文章,更關注文章的內容。例如,地方日報一則停水的通知,人們關心的是什么時候停水、什么時候恢復供水,而不太關心通知的語言形式。讀一部小說,人們更關心人物的性格及其命運,而不太在意小說的藝術形式。語文教學更應當關注的恰恰是文本的語言形式,因為語文課程的基本目標或者說語文設科的基本出發點在于培養、提高學生理解和運用祖國語言文字的能力。因此,課文的語言形式應當成為語文教學的主要內容。這就是語文教學中形式與內容的辯證關系。正如書法:一首唐詩,可以用柳體寫,可以用歐體寫,唐詩是內容,柳體或歐體是形式。然而當我們研究或欣賞書法藝術的時候,情況發生了變化,書法藝術成了我們欣賞的內容,柳體書法藝術既可以通過一首唐詩來表現,也可以通過一首宋詞來表現,唐詩或者宋詞成了柳體書法藝術賴以存在的形式。
當前語文教學實踐的主要弊端就是游離課文的語言形式,沒完沒了地討論課文的文化內涵,把語文課上成了思想品德課、科技常識課,或者是泛文化課。那樣的語文教學必然是低效的。
一位小學老師教《真理誕生于一百個問號之后》,講完了課文中的三個例子,教師又補充了兩個例子,其目的就是要強化課文的主題思想。可是她偏偏不引導學生學習課文中很有價值的語言表達。作者在寫第一個例子前說“就拿洗澡來說吧”,在第二個例子前說“無獨有偶”,在第三個例子前說“最有趣的還是”,正是這三句話將三個例子連貫起來,并與課文的其他表達聯系起來,使課文成為一個有機整體。學會了這些,就掌握了組織文章結構的一種方法。一個小學生學會了這樣的表達,即使到了初中,其作文也是上乘。本文開頭提到的《我的母親》,教學的主要內容應當是作者如何表達母愛和自己對母親的愛。例如,作者說:“母親去世的時候,才二十九歲。”這個“才”就應當好好學,因為它表達了作者對母親英年早逝的惋惜之情。沒有這個狀語,文章就顯得冷冰冰的。狀語重要,你還得用得恰當,否則還不如不用,不然你把“才”換成“已經”試試。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所以成為千古名句,并不因其思想價值高,而是因其所表現的作者的言語智慧高。贛江上空的這一景象不知有多少人見過,不就是有些云霞,有野鴨子在飛嗎?是作者的言語智慧創造了一種意境。“楊柳依依”“桃花灼灼”的價值,主要不在于楊柳和桃花的可愛,而在于作者以最恰當的、最美妙的語言表現了楊柳和桃花的可愛。用“依依”來表現楊柳的婀娜,以“灼灼”來表現桃花的明艷,簡潔之至,貼切之至,美妙之至,幾千年來無出其右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世界母語日提出的主題是“母語是一個民族文化的靈魂”。中華民族文化的靈魂既不是孔孟之道,也不是老莊哲學,而是孕育了孔孟之道和老莊哲學,培養了詩經楚辭和唐詩宋詞的漢語——我們的母語。
閱讀教學就是要引導學生從字里行間汲取作者的言語智慧。我給“國培”班的骨干教師講這個道理,老師們說:“現在明白學生為什么寫不好作文了,閱讀教學不引導學生汲取作者的言語智慧,學生怎么能學會寫作文?”語文課程標準明確提出,語文課程是學生學習運用祖國語言文字的課程。這一表述具有撥亂反正的意義,是近十年來中國語文教育最了不起的進步。
當然,語文課程有人文性,但語文的本質屬性是工具性,語文是一種表情達意的人文工具。語文教學具有多重功能,語文素養中還應當有情感態度價值觀,而且積極的情感態度價值觀能夠促進語文能力的提高,但情感態度價值觀的培養應當滲透到聽、說、讀、寫的語文活動過程中去,而不是“外加香油一勺”,更不能喧賓奪主。
(作者單位:江南大學文學院)
網友熱議
貢如云
吳教授的觀點,我是認同的。最近接觸到美國的一些課程文件,發現在這個問題上,中美主流觀念是多么的一致。高中母語教師湯普森在教環境題材的散文單元時說:“散文解讀,當然需要關注文本的內容信息,但更需要領會文本的言外之意,尤其要用心體悟作者傳達這些意思的語言構造,包括文學技巧與文風選擇。”這正如讀吳格明教授的文章,領悟其意只是一方面,琢磨為何要這樣表達,才是關鍵。能有這樣一種讀解意識,讀才是聰明的讀,學方為聰明的學。
(作者單位:南京曉莊學院)
錢曉國
語文究竟該“教什么”?當前不少教師迷失在“人文”的叢林里,以為語文課就是挖掘文本的人文意蘊,而將意蘊賴以存在的語言形式棄置不顧,凌空蹈虛,致使語文教學被異化成“空中樓閣”。這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吳格明教授做此文可以說意在撥亂反正。通過挖掘文本的人文意蘊,對學生進行情感、態度、價值觀的培養固然很重要,但這并不是語文學科獨有的任務,語文的主要任務還是在于通過聽、說、讀、寫等言語實踐活動,培養學生正確使用漢語言文字,養成較強的語文應用能力,否則,“種了別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正如吳教授所言,“文何以載道”才是語文教學的大道。
(作者單位:湖北省安陸市第二高級中學)
王科
文道統一歷來是中國傳統,學習語文不可能剝離“道”而空談語言,也不可能丟棄語言而侈談“道”,二者水乳交融、和諧共生。失去了對文章內容(道)的理解和體悟,所附著的語言也就毫無價值和意義了。形式必須是“有意味的形式”,而不是冷冰冰的“物質外殼”。朱光潛在《咬文嚼字》里說,“咬文嚼字,在表面像只是斟酌文字的分量,在實際上就是調整思想和情感”,“在文字是推敲,骨子里實在是思想情感上‘推敲’”,語言的精妙之處只能在內容(主題思想)中體現。“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美在意境,美在情景交融,美在內容和形式的高度統一。本質上說,思想和語言須臾不可分離,“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歸根結底,閱讀教學就是要憑借語文教材這個“例子”,在培養學生聽說讀寫能力的同時,引導學生認真讀書,充實頭腦,開闊眼界,豐富和拓展知識儲備,涵養深廣的人文素養。
(作者單位:甘肅省酒泉市特殊教育學校)
張毅
關于這個話題,民國時期早已有人談過,夏丏尊等先生就曾再三強調過要學習語言的形式,近年來吳忠豪教授也提出了“語文本體性內容”的理論。那么,幾十年來有眾多大師的指導和呼吁,為什么教學中還會偏離語文教學的軌道呢?我認為,語文課“教什么”存在的問題,首先是語文科核心知識和能力訓練體系不明確造成的,責任首先在語文課程的頂層設計者身上,我們不能把責任都歸罪于一般教師。換句話說,教師教學的隨意性是我國語文科課程建設成熟度低造成的,要想改變現狀,語文教育界首先要聚焦課程建設。我今年一直呼吁語文科內部分科教學,如果內部不分科,很難說清楚到底是應該重內容還是重形式的問題。例如,教學說明文《鯨》,教學重心當然是說明文的說明方法和語言特色方面;教學孔孟的文章,則重在經典教化,內容的教學當然是重點;而《背影》一文作為“定篇”,散文的細節描寫以及中國傳統父子關系的內容方面都是教學的重點,不可偏廢。
(作者單位:山西大同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