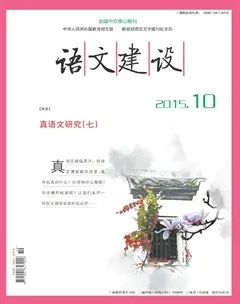新思路 新突破
由于每年參加廣東省高考語文評卷工作,我對中學語文教學的現狀有一定的了解,與中學語文教師的接觸亦逐漸增多。胡興橋就是我接觸過的一位優秀的中學語文教師。
從地域文化的視角,重新審視中學語文教材和教學狀況,確實是解決目前中學語文閱讀和作文教學存在問題的一條新思路。那么,地域文化以何種方式關涉中學語文教學,確實是我們首要探討的問題。我認為,《地域文化與中學語文教學》有三個方面值得關注:
第一,帶領中學生回歸地域生活之源去閱讀理解。人生活在一定的地域生態環境之中并獲得真切的體驗和內心的感悟,生活是文學閱讀與寫作的源泉,但是,目前在高考指揮棒下的應試教學,恰恰是遠離生活,閱讀與寫作不重真切的體驗和內心的感悟。興橋兄認為:“在這個時代迅速變遷的當下,當讀圖與讀頻正在走進學生常規生活的當下,我們的閱讀與寫作將何去何從?我們如何能激發起學生的內心,就像當初的我一樣,能將寫作作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甚或迷戀乃至癡迷文字帶來的愉悅和感動呢?”為了讓學生獲得閱讀和寫作所帶來的愉悅和感動,興橋兄在教材中充分挖掘地域原生態生活的課程資源的價值。
如他講朱自清的《背影》時,有意引導學生思考為何作者單單選取浦口車站“買橘”送別這一場景。原來,“買橘”是揚州一地特定的文化習俗。每年大年初一清晨,揚州主婦須將事先準備好的橘子分發給全家老幼,這是新年第一件莊重又愉快的事。揚州話把碰上好運叫“走局”,好的運氣叫“橘氣”。“橘”和“局”諧音。橘子的清新鮮爽的氣味,俗稱“橘氣”,故而贈人以橘便意味著把好運氣贈予對方,希望吃了橘子的人,處處走運,事事遂心。《背影》中的父親失業,在“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的境況下,臨別前為兒子翻越月臺去買橘,不僅寄托了一個迂執的父親對兒子的良好祝愿,而且蘊含了深沉的父愛。因而這一“背影”打動了“我”,深深烙在“我”的心田。正是通過“買橘”這一揚州特有文化風俗的揭示和分析,使學生能更好地領悟文中人物的內心情感,更好地感受到“背影”所包含的濃濃的父子的深情。
《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就明確指出:“各地區都蘊藏著自然、社會、人文等多種語文課程資源。要有強烈的資源意識,去努力開發,積極利用。”興橋兄認為:“以語文教學的視角,關照地域文化,是每個具有前瞻意識的語文教師的教育使命和文化責任。地域文化以何種方式關涉我們的語文教學,是我們首要探討的問題。”這種認真貫徹落實語文課程標準的教改精神是值得肯定和推廣的。
第二,引領中學生回歸文化之根去探究閱讀。我認為,目前中學語文教學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語文教師歷史文化知識薄弱,知識結構不完善,教學多照本宣科,缺乏學術探究精神。《孟子·萬章下》:“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章學誠《文史通義·文德》“: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之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遽論其文也。”因而,讀一篇文學作品,即讀其人,即讀其世,即讀其文化。興橋兄講蘇軾《江城子·密州出獵》時,能結合密州的民風及文化傳統說明這些與蘇軾詞風轉變的關系。“首先,密州儒學相當興盛。其次,密州一帶的民風樸魯純真‘不知嬉游’,而且在北宋這一帶的人們以強悍勇武聞名。深沉厚重的儒學傳統,會促使作者在詞中更多更深地寄托自己的政治抱負;純樸而‘不知嬉游’的民風,也會促使作者進一步減少詞這種體裁中固有的脂粉氣;而以習武知兵為目的的圍獵活動,慷慨悲歌的文學傳統無疑更有助于作品豪壯風格的發揚。可見,密州特定的文化環境直接影響了蘇軾詞風的改變,并由此而開創了宋代豪放詞風的先河。”讀書的目的是明理,在于明心見性。這種結合地域文化資源對作家作品的學術解讀,是作者經過認真查閱文獻資料并進行探究后得出來的,與那些照本宣科或者無“根”臆測的語文閱讀教學,不可同日而語。
第三,從最熟悉、最喜歡的地域人物事件入手,調動中學生閱讀和寫作的內驅力。興橋兄覺得高考指揮棒之下的作文教學,有著驚人的一致性,老師們大都忽略了作文最本質的引領,而常常在技巧與方法上層出不窮地落實,以至于高考作文常常似流水線生產的產品,而鮮有上品。學生害怕作文甚至討厭作文,這對于我們的母語教學和習得,真是一個莫大的諷刺。“一個好的語文教師,應該讓自己的孩子在最能體現自身情感世界的作文方面有所建樹,而不是憑著某一種或幾種模式,進行空洞麻木的‘仿套抄’和‘假大空’式的寫作。”因而,《地域文化與中學語文教學》嘗試從孩子最喜歡的東西入手,去調動他們寫作的內驅力,將寫作作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變害怕作文、討厭作文為喜歡作文。我認為這種通過閱讀和寫作教學引領中學生回歸地域生活之源的語文教改,讓中學生的閱讀和寫作有了源頭活水,能夠“展示語文學科的生命能量”。閱讀和寫作的關系非常密切,隨著文本閱讀理解水平的提高,必然會促進寫作水平的提高。
我認為,一個合格的語文教師應該具備以下四個基本條件:第一,他應該是一位嚴謹的學者,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勇于探索,自我完善;第二,他應該有尊崇教書育人的教育理念,注重人的素質教育,而不是圍繞高考指揮棒照本宣科地進行教學;第三,他應該是民族文化的傳承人,具有高度的歷史責任感;第四,他應該具備牢固的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目前,我們更多的是強調教師的責任感,這種“責任感”的內涵就值得懷疑。教育理念不正確,對教學的內容沒有獨立的思考和批判精神,人云亦云,照本宣科,這種“責任感”越強危害反而越大。這一點,我想興橋兄是有深切體會的。他早年曾擔任某中學文學社的輔導工作,一干就是七年。他覺得自己并不快樂,“因為文學社的文學作品直指心靈,性靈而自由無礙;而另一方面,作為一名要出教學業績的語文老師,我不得不結合當時湖北的高考優秀例文,不厭其煩地教導學生怎樣寫好高考作文,當我2004年將學生的高考成績教得出類拔萃時,我已然失去了一個語文教師應有的文學心態,我于是去尋找一個關于語文教師夢想、關于語文教師尊嚴的未來”。我高興地發現,《地域文化與中學語文教學》正是興橋兄試圖尋找語文教師夢想和尊嚴的有效突破。
作為《地域文化與中學語文教學》的第一個讀者,我讀后獲益良多。然而我同時覺得,作者較為注重單篇作品的教學實錄,多停留在語文教學經驗總結的層面,還需一些教育理念和教學理論層面的探索,在尋找語文教師夢想和尊嚴的征途中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唐人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云:“愚以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詩。”我想,興橋兄應當經常邀請酒朋詩侶宴集,“辨”各種富有地域特色的名酒的“味”,如果將各種富有地域特色的名酒的“味”都“辨”明了,那么,對“地域文化與中學語文教學”內在關系的體悟也會更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