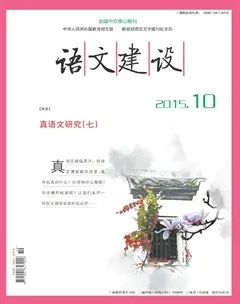民國小學語文教科書兒童本位探析
民國時期是我國從傳統教育向現代教育過渡的轉折時期。不同歷史時期其教育價值取向、教育訴求有所區別,探索、研究民國時期小學語文教科書教育價值取向、教育訴求,對當今小學語文教材的編寫具有現實意義。葉圣陶認為,教師在進行教育時應當找到“適當的教材”:“所謂適當的教材,無非是兒童所曾接觸的事物,然則將兒童所曾接觸的事物,盡行記錄或說明,就可算最好的教材么?那又未必。因為兒童的生活,差不多浸漬于感情之中;冷靜的理解,旁觀的述說,在兒童殊覺無味。要使兒童感覺無味,就不是最好的材料。所以國文教材普遍的標準,當為兒童所曾接觸的事物,而表出的方法,又能引起兒童的感情的。換一句話說,就是具有文學趣味的。……文學趣味本是兒童的夙好呢,教師當然要教他們以富有文學趣味的教材。”[1]“兒童本位”是民國時期小學語文教科書的一大亮點,所謂“兒童本位”即兒童中心論”,是美國著名教育家杜威提出的。“兒童是起點,是中心,而且是目的。兒童的發展、兒童的生長,就是理想所在。”[2]其目的在于追求真正發現兒童,解放兒童的心靈。
一、辛亥革命時期的小學語文教科書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統治,結束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封建統治,建立以孫中山為首的臨時共和國,成立臨時共和國教育部,對教育進行一系列的改革。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頒發《普通教育暫行辦法》規定:“凡各種教科書務合于共和國宗旨,清學部頒行之教科書,一律禁用。”提出新的教育方針,突出資產階級的公民道德教育和知識技能訓練,體現了“共和精神”;尊重兒童特點,以兒童能力為本位編寫小學語文教科書。
1912年11月,教育部在《普通教育暫行辦法通令》《普通教育暫行課程標準》的基礎上,頒布《小學校令》和《小學校教則及課程表文》,提出:“小學校教育以留意兒童身心之發育,培養國民道德之基礎,并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識技能為宗旨。”[3]1912年《編輯共和國小學教科書緣起》明確提出編輯教科書的要求:“注重國民生活上之知識與技能,以養成獨立自營之能力。”這一時期教科書的教學內容多從兒童生活開始,與兒童的日常生活密切聯系,以培養兒童的生活能力為本位。如商務印書館1913年4月出版的《共和國教科書新國文》第二冊第2課:“一小舟,河邊行,前有槳,后有舵,上有布帆。”教學內容來自學生的周圍生活,有利于激勵學生的學習興趣,有利于學生掌握知識、形成技能。
依據兒童的身心特點,注重兒童的興趣愛好,以兒童的能力為主體,培養兒童未來生活所必需的知識技能。1916年10月,教育部修正公布的《國民學校令》《國民學校令施行細則》明確提出:“國民學校施行國家根本教育,以注意兒童身心之發育,施以適當之陶冶,并授以國民道德之基礎及國民生活所必需之普通知識技能為本旨。”1916年《國民學校令施行細則》規定:“讀本文章宜取平易切用,可為模范者,其材料就各科內擇其富有趣味及為生活所必需者用之。”[4]如商務印書館1912年出版的《共和國教科書新國文(初小用)》第二冊第7課:“臥室內,有火爐,爐中燒炭,火漸盛,炭漸紅,一室溫暖。”其內容不但來自學生的生活,而且富有文學趣味,同時有利于培養兒童了解社會、熱愛社會的精神,為未來的生活打下堅實的基礎。
從教育部頒布的有關文件精神、提出的教育方針到小學語文教科書的編輯要求以及選文可知,辛亥革命時期的小學語文教科書教學內容多與兒童的日常生活密切聯系,側重培養兒童的生活能力,真正體現“兒童本位”的教學理念。
二、北洋軍閥時期的小學語文教科書
五四運動以降,“科學”“民主”“自由”等觀念深入民心,廢除民初教育部提出的教育宗旨倍受推崇。1919年北京教育調查會通過調查研究,提出以教育本義代替民初教育部提出的教育宗旨,“養成健全人格發展共和精神為教育宗旨”[5]。所謂健全人格是指具備下列條件:私德為立身之本,公德為服務社會國家之本;人生所必需之知識技能;強健活潑之體格;優美和樂之感情。美國著名的教育家杜威到我國講學、宣傳并發表“兒童本位”和“興趣主義”理論,認為教科書的編寫從形式到內容都應由兒童的興趣出發,借以引起兒童的學習興趣,提高學習效果。我國教育界不少權威人物是杜威的學生,經過他們的鼓吹,教育界掀起一股實用主義的教育思潮。1923年6月,全國教育聯合會新學制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復訂刊布的新學制課程綱要規定語文教材總的編輯原則:“從兒童生活上著想,根據兒童之生活需要,編訂教材,形式則注重兒童化,內容則適合兒童經驗。”當時的小學語文教科書便是在這種指導思想下編印出來的。
這一時期出版的小學語文教科書較多: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分別出版的有1922年的《新法國語教科書》,1923年的《新學制國語教科書》等,1924~1925年的《新小學教科書國語讀本》(初小用)等,這些教科書所涉及的內容廣泛,但多數教材的編輯遵循“以兒童生活為本位”的原則,其內容多數與兒童的家庭、學校等日常生活相關,以兒童熟悉樂見的兒歌、童話寓言等形式編寫。如商務印書館1923年出版的《新學制國語教科書》(初小用)第二冊第20課:“我左手拿著水杯,我右手拿著牙刷。我彎著身體,我把牙刷放在嘴里。我動手刷牙齒,我把牙刷拿出來。我喝一口水,我把水漱口。我把頭低下去,我把水吐出來。”
總之,這一時期的小學語文教科書從選文內容到編寫形式充分體現當時教育部的教育精神,體現當時教科書編輯者的編寫原則,即以兒童生活為本位。
三、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學語文教科書
1923年,孫中山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改組國民黨,對“三民主義”進行重新解釋,提出“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的主張,“新三民主義”成為國民黨的指導思想和原則。為宣揚和落實“新三民主義”,1928年2月28日,國民黨政府大學院(相當于教育部)頒布的《小學暫行條例》明確規定:“小學教育應根據三民主義,按照兒童身心發展的程序,培養國民之基本知識技能,以適應社會生活。”為了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培養學生的基本知識技能,以適應社會生活的需要,根據“新三民主義”教育宗旨,1929年4月國民政府公布教育宗旨的實施方針第二條明確提出:“普通教育,須根據總理遺教,以陶冶兒童及青年‘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國民道德,并養成國民之生活技能,增進國民生產能力為主要目的。”[6]如1931年8月蒙文書社出版的《漢蒙合璧國語教科書》第一冊第 9頁的課文:“阿爸拿著剪子剪羊毛,羊呀羊,不要跑,剪罷羊毛去吃草,拿著剪子剪羊毛,羊毛長,羊毛好,織成絨絨做衣料。”該篇課文的內容貼近學生的日常生活,便于學生理解、掌握;同時,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學習剪羊毛、織絨絨、做衣料。
1932年,國民政府教育部根據《三民主義教育實施原則》制訂并頒布《小學課程標準》,規定小學教育的總目標為:“小學應根據三民主義,遵照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發展兒童身心,培養國民道德基礎及生活所必需的基本知識和技能,以養成知禮、知義、愛國、愛群的國民。具體分析如下:(一)培育兒童健康的體格;(二)陶冶兒童良好的品性;(三)發展兒童審美的興趣;(四)促進兒童生活的知能;五)訓練兒童勞動的習慣;(六)啟發兒童科學的思想。”[7]該課程標準還對教材的編寫、教學提出一系列的具體要求,包括須令兒童反復練習的、須令兒童精密思考的、須令兒童欣賞的、須令兒童發表的等。[8]這一時期出版的教材多以兒童或兒童熟悉的人物為主角,促進兒童的生活知能,表現兒童良好的品性、技能、習慣等。
1933年8月12日國民政府教育部頒發的《小學組織法草案》規定小學教育目的為:“應遵照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以發展兒童之身心,培養國民之道德基礎,及生活所必需之基本知識技能。”1932年《小學課程標準總綱》提出:“各科教材的選擇,應根據各科目標,以適合社會——本地的現時的——需要及兒童經驗為最重要的原則。”[9]把教材的選擇標準歸結為適合社會需要和兒童經驗兩大方面。商務印書館1934~1935年出版的《復興國語課本》(初小用)選擇教材內容的原則為:提倡犧牲和互助精神,以民族復興為中心;切合兒童生活,易于兒童閱讀;服務生活,學以致用。這套教材的編寫在當時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有利于培養學生的互助精神,培養學生熱愛勞動的觀念,培養學生學以致用的能力。如第二冊第26課:“來來來!不要走!大家伸出兩只手。哥哥幫助爸爸,種菜種豆。姐姐幫助媽媽,打油打酒。妹妹幫助我,趕雞趕狗。大家伸出兩只手,幫助做事不要走。”
根據形勢的變化,國民政府教育部于1936年重新頒布《小學課程標準》,總綱第一條規定小學教育總目標:小學應遵照小學規程第二條之規定,以發展兒童身心,培養兒童民族意識、國民道德基礎及生活所必需的基本知識技能為宗旨。具體如下:培育健康的體格與健全的精神;養成愛護國家復興民族的意志與信念;培養愛護人群利益大眾的情緒;培育公德及私德;啟發民權思想;發展審美及善用休閑的興趣和能力;增進運用書數及科學的基本知能;訓練勞動生產及有關職業的基本知能。這一時期出版的教材內容豐富,多數以學生生活為中心,涉及學校、家庭、自然等。如上海世界書局1937年4月出版的《高小國語讀本》第二冊第8課《假使》:
假使
假使我是一朵花兒,我希望早些開放;我要盡量表現我的美麗,還要盡量發揮我的芬芳。
假使我是一只鳥兒,我希望歌聲響亮;我要贊美自然界的風景,還要在天空里任意翱翔。
假使我是一條小河,我希望源遠流長;我要保持著蕩漾的清波,還要灌溉那可愛的田莊。
假使我是一顆明星,我希望大放光芒;我要使天文家增加思想,還要使航海家認識方向。
該詩歌富有兒童情趣,有利于培養兒童的想象力,充分體現“兒童本位”的教育思想。
簡言之,國民黨統治時期以“兒童本位”為教育思想主要在于培養兒童適應特定時期的社會生活所需,為當時的政治服務,即培養國民之基本知識技能,提倡犧牲和互助精神,以民族復興為中心,適應社會生活需要。
四、中央蘇區和抗日根據地時期的小學語文教科書
1934年2月16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頒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小學校制度暫行條例》,明確規定:“在工農民主專政下的小學教育,是要訓練參加蘇維埃革命斗爭的新后代,并在蘇維埃革命斗爭中訓練將來共產主義的建設者。共產主義的文化教育是革命的階級斗爭的工具之一,必須運用實際斗爭的教育和經驗來進行教育,使教育與斗爭聯系起來。要消滅離開生產勞動的寄生階級的教育,同時要用教育來提高生產勞動的知識和技術,使教育與勞動統一起來。”1934年4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員部頒布《小學課程教則大綱》,總的要求是:“小學的一切課目都應當使學習與生產勞動及政治斗爭密切聯系。”根據上述有關文件的精神,中央蘇區教育廳制定小學語文教科書的編寫規則:充分體現“社會化、政治化、勞動化、實際化”的指導原則。中央蘇區的小學語文教科書就是根據這個精神來編寫的。如1933年7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員部出版的《共產主義兒童讀本》第一冊第7課“分田,分了田,自己才有田”;第8課“作田,作了田,自己才有谷”。
1938年3月6日,陜甘寧邊區教育廳發出《陜甘寧邊區抗戰時期小學應該注意的幾個工作通知》,其中第二條規定:“課程重心的轉移:首先應該注意到統一戰線和抗戰政治教育,使學生對抗戰的形勢和抗戰的工作有簡單的了解。”1941年發布《陜甘寧邊區國防教育的實施原則》,第四條規定:“國防教育應與抗戰的行動密切聯系,學習與行動應打成一片……”1944年4月、5月,《解放日報》發表社論,社論明確指出根據地的教育必須為抗日戰爭服務,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上述文件精神決定陜甘寧邊區小學語文教科書的內容要注重兩個方面。一是抗日的,如1938年編寫的《國語課本》第一冊第26課《士兵保國衛民》:“工農做工種地,士兵保國衛民。工人也當兵,農民也當兵,人人要當兵。當兵打日本,打敗日本,我們民族才能生存。”一是與生產勞動相聯系的,如1946年編寫的《初級小學國語課本》第二冊的《小英雄》:“李有娃,年紀小,摘棉花,不彎腰。眼兒明,手兒快,過來過去真輕巧。少說話,多做事,半天摘了一大包。和大人,比一比,有娃不比大人少。你叫他,小英雄,有娃聽了低頭笑。”
誠然,中央蘇區和抗日根據地時期的小學語文教科書從特定歷史時期的兒童生活實際出發,密切聯系當時兒童日常生活,體現特定歷史時期的教育精神,體現“兒童本位”的教育理念,具有一定的時代性、合理性。
小學語文教材的編寫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兒童本位”的教育理念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們也應當認識到小學語文教材承擔著“啟蒙”“養正”的神圣職責,因此,希望小學語文教材為兒童提供一種純粹的“兒童本位”只能是理想主義。正如萬福仁在《呼喚兒童文學》中所說:“教育永遠是一個完整的過程,而作為一個完整教育過程的學校教育,它永遠不是也不可能是以兒童為目的的。它首先考慮的是現實社會的存在和發展,是一代代的兒童成長為什么樣的成人的標準,而不是也不應該是兒童的標準。”[10]
參考文獻
[1]葉圣陶.小學國文教授的諸問題[A].葉圣陶集:第十三卷[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2:11
[2]杜威.兒童與課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5.
[3][4][5][6][7][8][9]轉引自范遠波.民國小學語文教材研究[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07:30,32,36,54,55,56,61.
[10]王富仁,鄭國民主編.語文教學與研究[M].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6:132~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