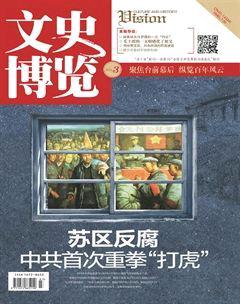民國首屆中研院院士為何缺了他
傅國涌
1948年6月20日,在美國養病的傅斯年給胡適寫信:“話說天下大亂,還要選舉院士,去年我就說,這事問題甚多,弄不好,可把中央研究院弄垮臺。大家不聽,今天只有竭力辦得公正、像樣,以免為禍好了。” 此前3月27日,中央研究院(中華民國最高學術研究機關,1928年在南京成立,民國時期網羅和培養了一大批高級學術研究人才)評議會已在南京先后5次投票選出了81位院士,因政見而為國民黨當局所不悅的郭沫若、馬寅初也在其中。
然而,在這次選出的院士中,史學方面有陳寅恪、陳垣、顧頡剛、傅斯年諸人,卻沒有史學大家錢穆(1895-1990,國學大師,代表作《先秦諸子系年》《國史大綱》)。對此,相隔18年,錢穆仍心有不平。1966年春天,“中研院”舉行第七次院士會議前,有人擬提名錢穆為院士候選人,托其弟子嚴耕望(1916-1996,著名歷史學家)征詢他的意見,但他拒絕提名,且憤慨地說:“民國三十七年(1948)第一次選舉院士,當選者多到八十余人,我難道不該預其數!”
嚴耕望認為錢穆之所以被擯于81人之外,是因學派門戶之見:抗戰之前,中國史學界以新考證學派聲勢最盛,為史學主流。錢穆雖以考證文章嶄露頭角,但由小學、中學教員成為大學教授,且錢穆在意境與方法論上,與考證派分道揚鑣,獨樹一幟,成為孤軍奮斗的新學派。另外,錢穆性格剛烈,從不考慮周遭環境,因此與考證派的主要人物的關系并不和諧。
1947年5月22日,胡適提名的史學方面的候選人是陳寅恪、陳垣、傅斯年、張元濟,傅斯年私下擬的名單上有二陳、顧頡剛、蔣廷黻、傅斯年等,確實都無錢穆在內。為何他們可以容得下政見不同的郭沫若,卻排斥學術見地不同的錢穆?嚴耕望提供了一種解釋視角。但從夏鼐(1910-1985,考古學家)發表在1948年《觀察》周刊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的分析》來看,很可能還有另外的因素使當時主辦院士選舉的學界中人排斥錢穆,那就是他的學歷背景。
在當選的81人中留學美國的有49人,占60.5%,其他留學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等國的有28人,無留學經歷的僅6人,4人有進士、舉人等科舉功名,兩人是國立大學本科或研究所畢業。雖然主事者極盡所能,試圖保持公正、像樣,乃至為郭沫若的入選而發生爭論,但就他們的提名來看還是講究出身來歷的。像錢穆這樣兩頭不靠,既沒有張元濟那樣的舊科舉功名,也未曾到歐美留學,甚至沒有進過本國的大學,與胡適、傅斯年他們素無淵源,這才是他被排除的更深層的原因。
錢穆《師友雜憶》中提及,當《國史大綱》出版之后,張其昀告訴他在重慶遇到傅斯年,問及對此書的意見。傅斯年回答:“向不讀錢某書文一字。”并指出錢穆屢言及西方歐美,“其知識盡從讀《東方雜志》得來”。 張其昀說:“君既不讀彼書文一字,又從何知此之詳?”傅斯年無語。由此可見傅斯年對錢穆的看法,尤輕看他沒有歐美留學背景。
夏鼐當時的文章開篇就說:“尤其因為提名的辦法不佳,有些可以當選的學者,根本沒有被提名,以致無從選出,令人頗有遺珠之感。”錢穆無疑就屬于這樣的“遺珠”,當然,他的學術貢獻并不因此而減少一毫的光芒。時間是最好的證明,他的著作今天仍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