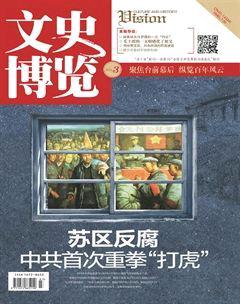扁鵲到底是誰
裘偉廷
《史記·扁鵲傳》說,秦越人聞名天下,周游列國,“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據考證,“扁鵲”是翩翩飛舞的喜鵲之意。2000多年前,司馬遷曾敘述了一個“扁鵲”的故事。他說這個人姓秦,名齊之,越人。后來有人覺得齊之與越人意思似乎不通,就自作主張將“齊之”兩個字給刪去了,直接叫做“秦越人”。
據傳,秦越人以扁鵲名義出現之前,年輕時的他曾是驛舍的舍長(驛館主事),至少在齊國某通衢大道上的驛舍待過十年以上的時間。直到有一天,一位隱姓埋名,只曉得是從長桑來的老人長桑君到了這座驛舍。從那時開始,兩人的交往持續了十年時間,終于在某一個夜里,長桑君把秦越人叫到房間里,將私藏的醫學秘籍和一種奇藥傳給了他,剛交待好,長桑君遂隱身不知去向。次日,秦越人按照老人囑咐,和著天上的露水,服下那包藥,30天后,果然出現了想不到的奇事,他竟然可以隔著厚厚一堵墻,看到墻那邊的人。從此以后,秦越人就給人診病了,他的眼光能洞徹人的五臟六腑,那里面有什么癥結一清二楚。
就這樣,秦越人成了天下診脈使針石治病第一人,開始在齊、趙兩地行醫。他曾為五日不醒人事的晉國大夫趙簡子診病。后路過虢國,救活了虢太子。去齊國時,秦越人望診齊桓侯,告訴他皮表孔隙有疾,不治恐會加重,而招致對方不悅。等到桓侯病入骨髓,已無可救藥,秦越人趕緊逃離了齊國。后來,他來到秦國,秦太醫令李醯(xī)嫉妒其醫技,派人刺殺了他。
關于秦越人,司馬遷將之描述成身形飄忽的行者,一會兒在齊國,一會兒在趙國,一會兒沒準又在北虢、西秦什么地方出現。司馬遷的追蹤,唯一的結果就是從趙國老百姓口傳中知道,有一個叫扁鵲的神醫來過。于是,司馬遷放棄了秦越人的故事,他敘述的故事就變成了扁鵲的故事:當整個趙國普遍重視女性時,扁鵲就以婦科醫師的身份出現在邯鄲;而東周各國,民間以尊崇老人為俗時,扁鵲在洛陽就及時成為專治耳瞽目眇的五官科醫師;到了秦都咸陽,由于那里老百姓特別愛護孩子,扁鵲便又是兒科醫師了。司馬遷最后用他的如椽史筆鄭重寫道:扁鵲在民間的身份“隨俗為變”。
但當后世的學者文人們,滿懷興趣要考證出一個確實的扁鵲時,事情就變得復雜了。早在晉代,文學家傅玄就質問說,虢國早在給趙簡子治病前120多年就滅亡了,這時怎么會有一個虢國呢?清代學者梁玉繩則發現,從趙簡子死到齊桓侯(桓公武)繼位,其間有93年,感嘆“何鵲之壽也”。學者們還將《扁鵲傳》與其他扁鵲資料相互印證,結果發現了更嚴重的年代上的沖突。《韓非子·喻老》篇中扁鵲見蔡桓公的古文段子廣為大家所熟知,而史載桓公于公元前7世紀初葉去世。《戰國策·秦策》又記載,扁鵲建議用石具為秦武王臉部除疾,而武王是公元前4世紀末葉的人物。扁鵲生活的時代前后相差近400年,這無論如何都是不可能的。
就是說,經過地點、人物、時間之間關系的多次推算,學者們認為,那個為五日不省人事的趙簡子診療的扁鵲,與治好了虢太子假死病的扁鵲;那個跑到齊國(韓非說蔡國)見齊桓公(韓非說蔡桓公),被齊桓公(蔡桓公)拒絕治病的扁鵲,與慷慨激昂大罵秦武王的扁鵲,以及對魏文侯侃侃而談的扁鵲,并不是同一個人。因此,如果司馬遷沒有虛構,那么肯定他所持的資料有誤。于是,他們猜測,也許司馬遷手里關于扁鵲生平的材料,是走遍七國故地,訪問故事史跡,從口頭得來,訛誤是免不了的事。
一些研究者認為,扁鵲是古代傳說中的一位名醫,并非指具體的“秦越人”或其他個體。換句話說,扁鵲只是傳說中的人物。韓非在《安危》篇中,拿扁鵲“以刀刺骨”治療重病患者,來類比大臣的強諫。關于扁鵲的這則事跡,韓非明確說,是源自“聞古扁鵲”。這里,作者在利用材料撰寫文章這一層面上,交待了所述內容源自傳說。在古代,有關扁鵲的傳說曾在廣泛的地域流行,在《冠子·世賢》篇中,就說到扁鵲“名聞諸侯”。既然如此,扁鵲在傳說中超越時空地成為許多醫療事件中的當事人,也就不難理解了。
但是,也有一些學者認為,扁鵲的一些資料源自歷史記錄,他是一位真實的歷史人物。比如《史記·扁鵲傳》記載,扁鵲曾為五日不醒人事的晉國大夫趙簡子診病的事,有學者就認為,《扁鵲傳》明確記載此事系“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這就表明扁鵲診趙簡子一事,乃趙之史臣董安于在事件發生后的當時記錄下來的歷史事件。但問題在于,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這一情節,是整個故事中的一環。它們作為情節雖合情合理,卻未必是真正發生過的。
還有一些學者,將目光關注于對材料真實可靠性的認定上。如盧南喬認為,《扁鵲傳》中的材料是可信的,因為司馬遷是掌握了史料和忠于歷史的。不過接著就有人指出,司馬遷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歷史學家。他雖有求真的意識,但世界觀是古代的,其求真標準也與我們不同。例如,《史記·老子傳》中記述老子活了160多歲或200多歲,并認為這是修道養壽的結果。可見,那個時代的神仙思想已經是司馬遷思想框架中的一部分。《扁鵲傳》中,扁鵲生活的時代長達一個多世紀,正是因為司馬遷對史料可靠性的判定中,夾雜了神仙思想。
有人認為,扁鵲實際上是司馬遷根據民間記憶而塑造出的一個理想人物。司馬遷未必不知道這些前前后后出現的扁鵲,時間上有200多年的差距,甚至他完全知道扁鵲在更遠的黃帝時代便聲名卓著。既然扁鵲是一個實際超越了一定時空的人,那么司馬遷有什么必要執著于此扁鵲與彼扁鵲的分別呢?而更有可能的是,司馬遷站在民間立場上,歷史性地發現并表達了扁鵲作為民間形象的意義。司馬遷故意放棄了對秦越人,放棄了對扁鵲的詳細考定,實際上是為了追求另一種更深刻和更豐厚的敘事效果和歷史寓意——“扁鵲”是按照人民日常生活需要和情感意愿出現的醫人,他是一個按照世俗理想塑造出來的醫學形象,他在民間的行走,充分顯示了民間生存空間的廣闊性和永恒性。
20世紀70年代,在山東出土的東漢畫像石刻“扁鵲針砭畫像”上,扁鵲是一個手執針石為人治病、半鳥半人的神人。這似乎意味著,扁鵲在民間的形象是一只永遠自由的飛鳥。在這個意義上,也許永遠沒有人能告訴我們:“扁鵲”到底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