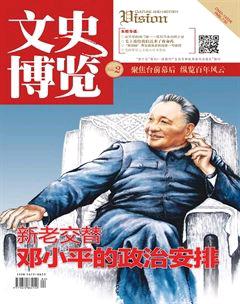民國考試:評卷很靈活
唐寶民
近來從學者李新宇的書中讀到:清朝末年,嚴復在安徽高等學堂做監督時,該學堂有一次舉行大考,考試的題目是《張巡論》,試卷上附有張巡的事跡介紹——
“……張巡是山西永濟人,于唐朝開元末年考中進士,曾任真源(今河南鹿邑)令。唐玄宗重用楊國忠執政,以外戚得勢,權傾朝野。有人勸張巡晉謁楊國忠以表崇敬,求取高官,但張巡堅決拒絕。當安祿山起兵叛唐,會合史思明作亂,張巡以地方官忠于職守,與部下共同堅守睢陽(今河南商丘睢陽區),抵抗安史的圍攻。他的英勇行為受到唐朝廷的表彰,提升為御史中丞。守城苦戰,歷數月之久,后彈盡糧絕,他殺妻妾以餐軍士,最后城被攻破,壯烈殉職……”
張巡誓死不降的事跡得到朝廷的充分肯定,朝廷隆重表彰他的忠于國家的氣節,為他樹碑立傳、修墳建廟;許多文人墨客也紛紛寫文章贊揚他,韓愈就曾在文章中這樣寫道:“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阻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
這道題其實很好答,只要順著出題者的意思表彰張巡寧死不屈、忠君愛國的情操即可。可是,有一個叫王愷鑾的學生,卻對張巡的所作所為產生了不同的想法,認為張巡“殺妻妾以餐軍士”的做法是一種野蠻行徑,是嚴重違反人類道德的行為,于是,他便在答卷中寫道:“張巡殺妻妾,屬野蠻行徑,忍心害理,而無益于兵,也違男女并重之道……”
這份與標準答案相背離的答卷,在當時被視為離經叛道,因為它挑戰了幾千年的君臣大義,棄傳統綱常倫理于不顧,其結果可想而知,作文滿分是100分,閱卷老師給這份卷子批了40分。
考試結束后,嚴復在檢查卷子時,注意到了這篇40分的作文。嚴復從頭到尾仔細看了一遍,興奮得連聲贊嘆,因為他覺得王愷鑾有自己的思想,這一點十分難能可貴。于是,他在考卷上親筆改動了幾個字,并把王愷鑾叫來,仔細詢問了一番,給予熱情的鼓勵,并自掏腰包當場獎勵了王愷鑾10塊銀元。那位評卷老師見此情形,連忙把考卷上的40分改成了90分。
錢穆是國學大師,晚年的時候,他曾寫了一部《師友雜憶》,在這本書中,有一部分章節是記述自己的教育經歷的,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錢穆讀中學時的一次考試。那是一次地理考試,只有四道題,滿分100分,每道題25分。錢穆拿到試卷后,從第一道題開始審題,審到第三道題的時候,他興奮了。原來,這道題的內容是關于長白山地勢軍情的,錢穆對這個問題一直很感興趣,此前曾讀過很多這方面的資料,所以看到這道題之后,便情不自禁地開始答題,而且不是“為了答題而答題”,完全是興之所至,洋洋灑灑地盡情揮毫,早已經忘了自己當時是在考場上。
也不知過了多久,錢穆總算是把這個題目答完了。可就在此時,鈴聲響起,原來交卷的時間到了,可錢穆只顧著全神貫注地答第三道題了,余下三道題,他一個字也沒寫,但已經來不及了,只好悻悻地把卷子交了上去。
按照常理推算,錢穆的這次考試,是不能及格了,因為他只答了四分之一的題,即使那道題給他滿分的話,他也只能得25分。可是,卷子發下來后,錢穆竟然驚訝地發現自己得了75分!
原來,負責這次判卷的是史學大師呂思勉,呂思勉看到錢穆的卷子后,發現他雖然只答了一道題,但這道題答得卻特別出色,論證合理、論據充分,作為一個中學生來講,能做到這一點,實在是難能可貴。
呂思勉素有愛才之心,便就錢穆的這道題寫了長長的批語,對錢穆的答案給予了高度肯定,同時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處,最后,給出了75分的成績,使錢穆僅憑一道題就及格了。
從以上兩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出,嚴復和呂思勉,并沒有按照僵化的規定去評卷,而是用靈活的方式,對學生的創造力進行鼓勵,這種靈活的評判方式,無疑給了學子們自由發揮的空間,更有利于他們自由地成長。
民國時期的考試,雖然也有關于考試成績方面的硬性規定,但在執行過程中,卻具有靈活性的一面,教師在評判學生的試卷時,不是機械地按照僵化思維去做,而是結合學生的具體情況,給予更多的人性化關懷,從而保護了學生的主觀能動性,有力地促進了學生的健康成長。
或許他們認為:考試不是衡量一個學生的絕對標準,人的本身才是目的、是尺度、是根本,其他的一切都是從屬的、次要的。這些,不正是今天應試教育中所缺少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