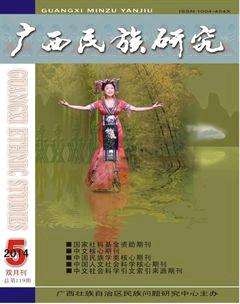國內(nèi)民族文化傳承研究述評
[摘要]國內(nèi)民族文化傳承研究肇始于20世紀(jì)80年代,30余年的學(xué)術(shù)研究經(jīng)歷了一個(gè)從概念到實(shí)踐不斷深化的過程,積累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文章從文化傳承的理論基礎(chǔ)和實(shí)踐邏輯兩大方面對既往研究進(jìn)行梳理,并予以評析,借此提出幾點(diǎn)展望。
[關(guān)鍵詞]文化傳承;研究;述評
[作者]姚磊,梧州學(xué)院副教授,中南民族大學(xué)博士研究生。廣西梧州,543002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4)05-0117-010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各民族先后步入了現(xiàn)代化變革中,伴隨著經(jīng)濟(jì)的快速發(fā)展,民族傳統(tǒng)文化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然而,我們不能拒絕現(xiàn)代化,現(xiàn)代化是民族繁榮發(fā)展的必由之路,喪失現(xiàn)代化將意味著民族貧困;我們更不能摒棄傳統(tǒng),傳統(tǒng)是民族保持自我本色的根基,喪失傳統(tǒng)意味著民族的消亡。可見,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化構(gòu)成了當(dāng)下中國各民族發(fā)展過程中的一組尖銳矛盾,不解決好這對矛盾,將嚴(yán)重影響各民族的健康發(fā)展。近年來,國內(nèi)社會出現(xiàn)的社會誠信普遍下降、人們生活的幸福指數(shù)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嚴(yán)重背離等方面的不良現(xiàn)象,也充分說明了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化失調(diào)所帶來的危害。尤其是文化旅游、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的迅速發(fā)展,彰顯了富有特色的民族傳統(tǒng)文化不僅是民族地區(qū)脫貧致富的重要資本,而且是人們在經(jīng)濟(jì)富足狀態(tài)下追求精神享受的基礎(chǔ);而社會不良現(xiàn)象的糾偏和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在于保持民族傳統(tǒng)文化薪火相傳和持續(xù)發(fā)展。于是,傳承民族傳統(tǒng)文化,既是實(shí)現(xiàn)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有效對接、關(guān)乎中華民族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大問題,又是保持人類文化多樣性的社會普遍要求。誠然,伴隨著現(xiàn)代化變革,學(xué)者們便以敏銳的眼光對民族文化傳承問題進(jìn)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前瞻性的學(xué)術(shù)研究帶動了全社會對傳承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高度關(guān)注和熱情投入。因此,民族文化的傳承從過去到現(xiàn)在一直是熱點(diǎn)命題,這也是民族文化傳承作為一個(gè)動態(tài)、持續(xù)的過程之規(guī)律使然。
一、回顧
20世紀(jì)80年代至今,國內(nèi)學(xué)者從不同學(xué)科、不同視角對民族文化傳承問題進(jìn)行了研究與探討,積累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主要體現(xiàn)為民族文化傳承的理論基礎(chǔ)和實(shí)踐邏輯兩大方面,其中以文化傳承實(shí)踐的邏輯體系為研究重點(diǎn)。
(一)民族文化傳承的理論研究
中國民俗學(xué)引進(jìn)“傳承”概念以前,在張瑜、林惠祥等學(xué)者著作中就有了傳承研究的零星記錄。到了20世紀(jì)80年代,“傳承”一詞進(jìn)入中國民俗學(xué)界。早期有王汝瀾、孔進(jìn)己、簡濤等人的作品問世,主要闡明了民俗傳承的概念,認(rèn)為民俗傳承中最重要的是心意傳承,是其他傳承的軸心和骨干。烏丙安認(rèn)為,傳承性在民俗發(fā)展過程中具有運(yùn)動規(guī)律性的特征,民俗的傳承性與變異性是兩個(gè)矛盾統(tǒng)一的特征,只有傳承基礎(chǔ)上的變異和變異過程中的傳承,沒有只傳承不變異或者只變異無傳承的民俗事象;進(jìn)而提出了傳承論觀點(diǎn),包括民俗的一切傳承的形式或行動方式,應(yīng)當(dāng)將傳承作為一個(gè)獨(dú)立的研究對象,從民俗特征中解放出來。陶立瑤認(rèn)為民俗的傳承性是歷時(shí)的縱向延續(xù)性,表現(xiàn)為在傳承過程中內(nèi)容和形式上的連續(xù)性和穩(wěn)定性。鐘敬文認(rèn)為民俗傳承的語言、行為方式?jīng)Q定了民俗傳承過程需要不斷適應(yīng)周圍環(huán)境而做出相應(yīng)的變化,故而變異性是在民俗傳承和擴(kuò)布過程中引起的自發(fā)和漸進(jìn)的變化。張紫晨將傳承與文化聯(lián)系起來,提出“傳承文化”概念,“不僅代表著傳承著的事象本身,而且代表著一種文化過程,傳承過程就是文化延續(xù)的過程。”王雪認(rèn)為“傳承是民俗文化的延續(xù),也是民俗生活的延續(xù),更是傳承人的生活實(shí)踐。”
通過文獻(xiàn)檢索,文化傳承研究開始于20世紀(jì)80年代中期。“文化傳承實(shí)質(zhì)上是一種文化的再生產(chǎn),是民族群體的自我完善,是社會中權(quán)利和義務(wù)的傳遞,是民族意識的深層次積累,是民族共同體縱向的‘文化基因復(fù)制。”因此,“不僅要充分注意到傳承文化的民間性,還要重視其民族性、群體性以及傳統(tǒng)性與現(xiàn)代性交織在一起的文化變遷性。”可見,文化傳承是一種文化變遷的必然過程,是一種積極的文化再生產(chǎn)。古人云“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即希望文化傳承不僅僅是簡單的文化傳遞和“文化基因”復(fù)制,而是在民族文化深層次累積基礎(chǔ)上,促進(jìn)民族群體自我完善的文化生產(chǎn)和文化創(chuàng)新。目前,學(xué)界廣泛認(rèn)同趙世林教授關(guān)于文化傳承的概念界定,即“文化傳承是文化在民族共同體內(nèi)的社會成員中作接力棒似的縱向交接的過程。這個(gè)過程因受生存環(huán)境和文化背景的制約而具有強(qiáng)制性和模式化要求,最終形成文化的傳承機(jī)制,使民族文化在歷史發(fā)展中具有穩(wěn)定性、完整性、延續(xù)性等特征。”姜又春從歷時(shí)性和共時(shí)性兩個(gè)維度闡釋了文化傳承的內(nèi)涵,即“傳承是人類所創(chuàng)造的一切物質(zhì)和非物質(zhì)的民俗文化發(fā)展變化的運(yùn)動形式……人們傳承的是傳統(tǒng)文化,并以文化傳統(tǒng)的形式影響著人們的行為與心理;文化傳統(tǒng)則反過來作為一種‘文化權(quán)力,支配著人們繼續(xù)保持對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以致持久穩(wěn)定。”從“自我”角度來考察,文化傳承始終向兩個(gè)維度延伸,即前一代人通過文化對后一代人“傳”而達(dá)到永生,后一代人對前一代人文化的“傳”以求生存發(fā)展。因此,文化傳承既是一種必然規(guī)律,存在于物競天擇的規(guī)定性當(dāng)中,又是一種人類的文化理性選擇,離不開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fā)揮。
然而,文化傳承是一個(gè)非常復(fù)雜的問題,人們從不同學(xué)科、不同角度予以關(guān)注,難以形成統(tǒng)一的觀點(diǎn)。又由于民族文化的廣泛性和活態(tài)性,討論文化傳承問題時(shí),始終要清楚兩個(gè)最基本的問題,即“傳承什么”和“如何傳承”,這也是文化傳承體系中最重要的兩個(gè)環(huán)節(jié)。白庚勝認(rèn)為,需要傳承的傳統(tǒng)文化包括民族精神、民族標(biāo)識、制度、民族文化的傳人、學(xué)術(shù)資源、知識系統(tǒng)、情感寶庫七個(gè)方面,可以通過教育傳承、媒體傳承、產(chǎn)業(yè)傳承、學(xué)術(shù)傳承、民間傳承等五種方式來實(shí)現(xiàn)。郭繼承將這兩個(gè)基本問題分別概括為“對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思想價(jià)值的挖掘和闡發(fā),維護(hù)民族文化基本元素”和“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的渠道、方法、載體與方式問題”。羅正副認(rèn)為,少數(shù)民族文化傳承要考慮三個(gè)問題,即全面認(rèn)識少數(shù)民族文化是其文化傳承的基礎(chǔ),采取正確的態(tài)度是文化傳承的關(guān)鍵,實(shí)現(xiàn)民族文化現(xiàn)代化是文化傳承的趨勢。
(二)民族文化傳承實(shí)踐的邏輯體系研究
每一個(gè)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都是該民族成員共同傳承、集體擁有的財(cái)富,之所以流傳數(shù)千年,是文化的擁有者與參與者、特定的文化場域、一定量的文化介質(zhì)長期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任何一方的改變都會引起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弱化、消亡、擴(kuò)大或轉(zhuǎn)移。可見,文化傳承是個(gè)復(fù)雜的系統(tǒng)過程,按照一般系統(tǒng)理論,上述文化擁有者和參與者、文化場域、文化介質(zhì)、文化本體構(gòu)成了這一復(fù)雜系統(tǒng)的四個(gè)主要變量。學(xué)術(shù)研究中分別將前三者稱之為傳承主體、傳承場、傳承方法,筆者按照這三個(gè)傳承要素,結(jié)合傳承體系的整體建構(gòu),分別進(jìn)行文獻(xiàn)梳理,以便厘清民族文化傳承研究的既有成果和學(xué)術(shù)動態(tài)。
1.民族文化傳承的實(shí)踐主體
文化是人創(chuàng)造的,文化傳承也有賴于人的主動性的發(fā)揮,文化主體的自覺和自信是文化傳承的動力源泉。文化傳承主體包括傳者與受者,具體有個(gè)人、群體、政府、學(xué)界、商界、新聞媒體和社區(qū)等。當(dāng)前學(xué)術(shù)界關(guān)于文化傳承的實(shí)踐主體研究主要集中于非遺傳承人領(lǐng)域。劉錫誠、許林田、黃靜華、苑利、陳玉茜、楊娟、黃小娟等學(xué)者對非遺傳承人問題進(jìn)行了專題研究,包括非遺傳承人概念、人生歷程口述史、傳承人的認(rèn)定制度、傳承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傳承人的保護(hù)、傳承人理論建構(gòu)等六個(gè)方面。
黃小娟通過梳理和總結(jié)學(xué)界非遺傳承人的概念界定,認(rèn)為傳承人應(yīng)當(dāng)是能熟練掌握國家或地方政府認(rèn)定的各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項(xiàng)目,并在本領(lǐng)域內(nèi)有較大影響力,為公眾所認(rèn)同,并能積極開展傳承活動的個(gè)體。
對傳承人人生歷程的口述歷史,由最初對某一地域內(nèi)傳承人及其技藝的簡單羅列,到后來成為搜集和保存?zhèn)鹘y(tǒng)技藝原始資料的一種重要手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王文章主編的《中國民間藝術(shù)傳承人口述史》叢書(2010,10冊),記錄了唐卡、剪紙等10種特色鮮明的民間技藝發(fā)展歷程、技藝傳承過程以及傳承人對技藝的思考。《浙江省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傳承人口述檔案集萃:傳人》(2011)一書,從民間音樂、民間舞蹈、傳統(tǒng)戲劇、曲藝、民間藝術(shù)、傳統(tǒng)醫(yī)藥和民俗等方面,全方位展示了浙江省27位國家級非遺傳承人的學(xué)藝經(jīng)歷、藝術(shù)創(chuàng)作及從藝心得等。《我的民間藝術(shù)世界——八十位女性的人生述說》(2007)一書記錄了來自不同地區(qū)和民族的80位民間女藝人的生命歷程、生活百態(tài)、藝術(shù)追求。《揭秘水書——水書先生訪談錄》一書是對貴州荔波、三都、都勻水族地區(qū)的16位水書先生和水書研究員的深度訪談記錄,內(nèi)容涵蓋了水書先生在喪葬、建筑、祭祀等方面的咒辭和儀式等。
為了發(fā)揮傳承人的作用,國家制定了傳承人認(rèn)定制度,并在法律上規(guī)定了傳承人的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綜合劉錫誠、宋兆麟、蕭放、苑利、李華成、周安平、朱兵、李榮啟、游海洋等學(xué)者關(guān)于傳承人認(rèn)定的專題研究,主要有如下觀點(diǎn):(1)細(xì)化傳承人的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建立公正合理的認(rèn)定程序。(2)反思現(xiàn)行傳承人認(rèn)定制度,建議補(bǔ)充申請備案制度和群眾推薦制度,以申請備案制為主,國家認(rèn)定制和群眾推薦制作為有益補(bǔ)充,從而扭轉(zhuǎn)傳承人認(rèn)定的局限性。(3)名錄制度應(yīng)與傳承人認(rèn)定相統(tǒng)一,對列入名錄的重要的、有代表性的非遺項(xiàng)目,政府應(yīng)當(dāng)明確指定代表性傳承人并采取措施支持、幫助其實(shí)現(xiàn)傳承。(4)借鑒日本的“臨時(shí)性指定制度”,避免因申報(bào)周期漫長而遺漏、因傳承人病危或傳承環(huán)境急劇改變而徹底蒸發(fā)掉的珍貴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5)傳承人的認(rèn)定、保護(hù)、監(jiān)管應(yīng)該制度化,建立傳承人考核、檢查、變更、撤銷、退出機(jī)制,以促進(jìn)傳承人承擔(dān)技藝傳承責(zé)任。(6)對于節(jié)日、廟會等集體傳承的非遺項(xiàng)目,設(shè)立集體性傳承人,按照非遺的樣態(tài)進(jìn)行切分,找出主干的文化環(huán)節(jié),將其中具有組織、推動力量的關(guān)鍵人物確定為傳承人。
傳承人基于特殊身份而享有特權(quán)并承擔(dān)相應(yīng)的義務(wù),是對傳承人進(jìn)行保護(hù)和監(jiān)管的理論依據(jù)。《非遺法》第30條、第31條分別規(guī)定了代表性傳承人的資助措施和他們的義務(wù),但欠缺傳承人權(quán)利的相關(guān)規(guī)定。田艷、湯凌燕、劉云升、蘇喆等學(xué)者研究認(rèn)為,傳承人應(yīng)當(dāng)享有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和精神權(quán)利,包括獲得國家補(bǔ)貼、報(bào)酬、知識產(chǎn)權(quán)、獲得幫助權(quán)、禁止假冒、知情權(quán)和利益分享權(quán)等方面體現(xiàn)出來。蕭放、宋兆麟研究認(rèn)為,傳承人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相應(yīng)的義務(wù),主要有(1)自覺、公開展示、傳播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活動,培養(yǎng)新的傳承人,有條件的傳承人要講述自己的口述史或留下書面著作;(2)重視傳統(tǒng)并積極演化,反對與制止盲目改造與濫用;(3)完整保存所掌握的知識、技藝及相關(guān)的原始資料、實(shí)物、建筑物、場所等。
傳承人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活態(tài)載體,保護(hù)傳承人是民族傳統(tǒng)文化保護(hù)工程的核心環(huán)節(jié)。鑒于傳承人的嚴(yán)重?cái)鄬优c缺位,如何保護(hù)傳承人成為全社會關(guān)注的問題,學(xué)術(shù)界對此進(jìn)行了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傳承人的綜合保護(hù)、法律保護(hù)和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三個(gè)方面。苑利、趙世林、安學(xué)斌、王敏、楊雁秋、孫正國等人就傳承人的綜合保護(hù),提出如下可行性建議:(1)官助民辦,避免政府越位;采用客位保護(hù)為指導(dǎo)、主位保護(hù)為根本的形式,讓傳承人成為真正的保護(hù)主體;(2)通過培育民族文化產(chǎn)業(yè),支持文化傳承人進(jìn)行有償傳承活動以解決生計(jì)問題,抓好年輕一代傳承人的培養(yǎng);(3)以帶徒授業(yè)的方式拴住傳承人,避免單純的政府補(bǔ)貼并授予榮譽(yù)稱號;(4)對于無力開展傳習(xí)活動的瀕危非遺項(xiàng)目的代表性傳承人,予以項(xiàng)目資助;(5)發(fā)揮高校尤其藝術(shù)院校培養(yǎng)傳承人的作用,改革高校現(xiàn)行的傳承人人才培養(yǎng)模式;設(shè)立保護(hù)性基地扶持重要非遺項(xiàng)目傳習(xí)人,以培養(yǎng)傳承人;(6)為傳承人提供經(jīng)濟(jì)保障、社會福利保障和精神關(guān)懷,以項(xiàng)目資助方式讓金錢補(bǔ)貼由“輸血”變?yōu)椤霸煅眮斫鉀Q傳承人保護(hù)的關(guān)鍵問題;(7)傳承人保護(hù)類型化,將傳承人保護(hù)分為扶持性保護(hù)、引導(dǎo)性保護(hù)和開發(fā)性保護(hù)三大類,據(jù)此制定個(gè)性化的傳承人保護(hù)方案。關(guān)于傳承人的法律保護(hù)研究,徐輝鴻、聶華林、章建剛、吳安新、趙方等人提出了如下觀點(diǎn):一是以行政法保護(hù)為主,并在法律文本中細(xì)化,政府有區(qū)別地保護(hù)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二是賦予傳承人私法訴求權(quán),保障他們分享商業(yè)收益,允許他們以技藝投資、開辦私人培訓(xùn)機(jī)構(gòu)等;三是給予傳承人特殊保護(hù),即對故意傷害傳承人的刑事違法行為予以刑事處罰。至于傳承人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王培新、齊愛民、李曉秋、甘明、文永輝等人進(jìn)行了專題研究,代表性的觀點(diǎn)主要是設(shè)想通過現(xiàn)行的專利權(quán)、商標(biāo)權(quán)、著作權(quán)、商業(yè)秘密以及調(diào)整現(xiàn)行知識產(chǎn)權(quán)制度中保護(hù)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種種不適應(yīng),建立專門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制度,對此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進(jìn)一步拉大了代表性傳承人與社區(qū)民眾的生活差距,導(dǎo)致更大的不公平。
雖然大多數(shù)學(xué)者認(rèn)同現(xiàn)行的傳承人制度,但林繼富、尹凌、魯春曉、吳效群、王慶等學(xué)者對其提出了反思性意見:(1)現(xiàn)行傳承人認(rèn)定制度功利性強(qiáng),地方政府干預(yù)過度和經(jīng)濟(jì)尋租,行政申報(bào)方式違背文化傳承規(guī)律,造成地方政府壟斷。(2)名錄制度、補(bǔ)助制度、保護(hù)制度帶來了多種負(fù)面影響。(3)基于非遺的集體性和活態(tài)性,應(yīng)當(dāng)注重廣泛的繼承人培養(yǎng)。(4)建立非遺財(cái)產(chǎn)監(jiān)理人制度,以解決非遺傳承人主體問題等。(5)傳承人理論研究反思。現(xiàn)行傳承人理論研究主要著眼于解決傳承人生存的實(shí)際問題,少有建構(gòu)傳承人的研究理論。隨著傳承人學(xué)術(shù)研究的深入,傳承人理論建構(gòu)也有了一定的進(jìn)展。林繼富通過梳理國內(nèi)外民間故事傳承人的研究,認(rèn)為既有研究集中于文本采集,側(cè)重于傳承人的生平描述、講述風(fēng)格和傳承線路的考察,使得傳承人理論較為分散,而田野研究做得不夠制約了傳承人研究的理論深度和理論系統(tǒng)的形成;同時(shí),他建構(gòu)起的民間故事講述的三重結(jié)構(gòu)法則,回答了民間敘事傳統(tǒng)的構(gòu)成層次、鄉(xiāng)土文化意義以及傳承人與民間敘事傳統(tǒng)興衰的密切聯(lián)系等學(xué)理性問題。江帆、王志清、徐媛等人則對民間故事傳承人進(jìn)行了個(gè)案研究,提出了動態(tài)性、原生態(tài)和衍生態(tài)的保護(hù)方案及相互間的矛盾。陳靜梅認(rèn)為,今后的傳承人應(yīng)當(dāng)更多地關(guān)注集體性傳承人的認(rèn)定和保護(hù)、明晰傳承人的權(quán)利內(nèi)容、注重問題研究的田野資料支撐和強(qiáng)化傳承人理論研究等。
2.民族文化傳承的實(shí)踐空間
傳承場是民族文化得以萌生、棲息和發(fā)展的系統(tǒng)空間,也是構(gòu)成民族文化傳承的重要基礎(chǔ)。學(xué)術(shù)界關(guān)于傳承場研究主要集中于綜合性的理論研究、具體傳承場的專題研究和傳承場的變遷研究。
趙世林、張福三、馮天瑜、晏鯉波、和曉蓉、遲燕瓊、井祥貴、姜又春、司馬云杰、劉鐵梁、周星、管彥波、楊國才、魏國彬、和繼全等學(xué)者對傳承場進(jìn)行了研究,主要有如下觀點(diǎn):(1)傳承場的概念界定。傳承場是一種三位一體的“文化精神背景”疊加“特定時(shí)空間”和“特定活動群體”而形成的、保障傳承有序進(jìn)行的中介實(shí)體;一切人與人、人與社會接觸的空間組合都可以是傳承場。(2)傳承場的產(chǎn)生及其特征。人類的群體需要是形成傳承場的基本動力,有多少種需要就會產(chǎn)生多少種傳承場;傳承場是民俗生活文化得以萌生、棲息和發(fā)展的系統(tǒng)空間,具有開放性、動態(tài)性。(3)傳承場的構(gòu)成要素。文化傳承場有“兩要素說”和“三要素說”,前者認(rèn)為文化傳承場包括自然環(huán)境和社會環(huán)境,是民族文化賴以產(chǎn)生、傳遞的硬件;后者認(rèn)為民間文化傳承場由自然場、社會場和思維場組成,其中社會場包括社會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和社會制度環(huán)境,前者是指人類加工、改造自然以創(chuàng)造物質(zhì)財(cái)富所形成的一套生產(chǎn)條件,包括工具、技術(shù)、生產(chǎn)方式等;后者指的是人類創(chuàng)造出來為其文化活動提供協(xié)作、秩序、目標(biāo)的組織條件,包括各種社會組織、機(jī)構(gòu)、制度等結(jié)合而成的體系。(4)傳承場類型。傳承場實(shí)質(zhì)上就是文化傳承環(huán)境,而環(huán)境在文化傳承中的模式、特征決定了文化傳承場的類型和特征。概括地說,傳承場有實(shí)在的物質(zhì)空間和隱喻的空間兩大類,具體包括叢林、火塘、寺廟、儀式、學(xué)校、市場,村寨、家庭、婚禮、傳統(tǒng)節(jié)日、村寨中的文化活動場所等。(5)民族文化典籍及現(xiàn)代聲像資料、大眾媒體及大眾文藝、旅游、網(wǎng)絡(luò)論壇等發(fā)揮了民族文化傳承的媒介作用,是文化變遷進(jìn)程中的新生傳承場。另外,社會的需要和認(rèn)同等構(gòu)成的文化生態(tài)則是一種無形的最廣泛的文化傳承場域。
受社會現(xiàn)代化迅速發(fā)展的強(qiáng)烈影響,農(nóng)村社會的經(jīng)濟(jì)形態(tài)、組織結(jié)構(gòu)都發(fā)生了轉(zhuǎn)型,農(nóng)民由農(nóng)村涌入城市,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社會相對穩(wěn)固的關(guān)系群體不復(fù)存在,民間傳承場正在加速演變。李紅英、翁曉華、孫亞娟、熊斯霞、漆亞莉、李衛(wèi)英等學(xué)者都以某一地域或某一種傳承場為研究對象,重點(diǎn)關(guān)注了民間傳承場的變遷和重構(gòu)。(1)傳承場的變遷及其原因。受經(jīng)濟(jì)、教育等現(xiàn)代化“雙刃劍”的強(qiáng)力作用,民間傳承場迅速地趨向萎縮、消失、轉(zhuǎn)移或擴(kuò)大。(2)家庭、寺廟、傳統(tǒng)歌場等民間傳承場因社會變遷而逐漸瓦解,學(xué)校成了民族文化傳承的重要場域,與學(xué)校小環(huán)境相對應(yīng)的民族地區(qū)社會大環(huán)境也為民族文化的外部傳承提供了強(qiáng)有力的磁場。(3)受文化傳承方式和路徑變化影響,少數(shù)民族文化傳統(tǒng)傳承場逐漸被次生傳承場替代,多元化的傳承場出現(xiàn)了,舊的傳承場被改造完善,新的傳承場也逐步創(chuàng)建起來,這正是文化傳承的必然要求。(4)傳承場的轉(zhuǎn)換引發(fā)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與變遷。許多少數(shù)民族歌謠、舞蹈等傳統(tǒng)文化,因其傳承場發(fā)生了“傳統(tǒng)婚禮場一藝術(shù)舞臺一旅游市場”的漸次轉(zhuǎn)變,從而實(shí)現(xiàn)了從鄉(xiāng)俗禮儀到民間藝術(shù)的傳承與變遷。如邵陽布袋戲等表演類的民俗文化,除了家庭的靜態(tài)傳承場外,因其是鄉(xiāng)村民俗禮儀活動、節(jié)日娛樂活動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故而這些活動成了動態(tài)傳承場,發(fā)揮了更好的文化傳承功能。
3.民族文化傳承的實(shí)踐機(jī)制
民族文化的有效傳承有賴于傳承方式的選擇和運(yùn)用,或者說是傳承機(jī)制的建立和運(yùn)行。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文化發(fā)展到今天,實(shí)質(zhì)上是一個(gè)漫長的傳承過程。在此過程中,傳承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又是不斷變化的。通過梳理烏丙安、羅正副、姜又春、白庚勝、索曉霞、劉錫誠、和曉蓉、趙國宏、彭兆榮、周波等學(xué)者關(guān)于傳承方式的研究,筆者將他們的研究成果歸納為“兩種研究范式,多種傳承提法”。一是“標(biāo)準(zhǔn)”研究范式,即按照不同的標(biāo)準(zhǔn)對傳承方式歸納、總結(jié)、分析。以傳承主體多寡為標(biāo)準(zhǔn),文化傳承有群體傳承、個(gè)體傳承、家庭傳承、社會傳承;以傳承主體是否在場為標(biāo)準(zhǔn),分為在場傳承和不在場傳承;以傳承的組織形態(tài)為標(biāo)準(zhǔn),則可類化為血緣傳承、地緣傳承、業(yè)緣傳承和神授傳承;以傳承途徑為標(biāo)準(zhǔn),則有口頭傳承、行為傳承、心理傳承和書面?zhèn)鞒校灰詡鞒袌鲇驗(yàn)闃?biāo)準(zhǔn),則可細(xì)分為民間傳承、實(shí)踐記憶、實(shí)物意符、教育傳承、媒體傳承、產(chǎn)業(yè)傳承、場館傳承、學(xué)術(shù)傳承、網(wǎng)絡(luò)傳承。二是“載體”研究范式,即按是否以人為載體進(jìn)行總結(jié)。以人為載體,則可以歸納為“一對一”、“一對多”和“多對多”三種傳承方式。“一對一”傳承多體現(xiàn)于日常生活、生產(chǎn)技能和特殊技藝方面,“一對多”的傳承多屬于精神文化范疇的內(nèi)容,“多對多”傳承則是通過民族風(fēng)俗習(xí)慣、生活禁忌、人生禮儀、道德規(guī)范等對社會生活進(jìn)行調(diào)控,客觀上達(dá)到文化傳承的效果,通常以社會輿論給社會成員施加影響來實(shí)現(xiàn)。不以人為載體的傳承主要體現(xiàn)為各民族通過規(guī)章制度和習(xí)慣法來進(jìn)行的。
當(dāng)然,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不是一種方式的重復(fù)運(yùn)用,也不是幾種方式的簡單疊加或交替使用,而是多種方式交叉并行、相互補(bǔ)充的,況且文化自身本就具備著某種傳遞和延續(xù)生命的內(nèi)在機(jī)制。因此,少數(shù)民族文化傳承有其特定的運(yùn)行機(jī)制,是我們發(fā)現(xiàn)文化傳承規(guī)律需要探討的重要命題之一。索曉霞認(rèn)為“制度和法規(guī)形成的社會強(qiáng)制、民族社會生活中的潛移默化、道德和禁忌形成的心理約束”,是隱藏在各種文化傳承現(xiàn)象背后的“看不見的文法”。趙世林將民族文化傳承的社會機(jī)制概括為六個(gè)方面,即以家庭為中心的親親強(qiáng)制、以村寨為單位的社會監(jiān)督、特殊狀態(tài)(戰(zhàn)爭)下的高強(qiáng)傳承、族際交往中強(qiáng)化的自我意識、意味著義務(wù)延續(xù)的祖先崇拜和宗教意識。晏鯉波則認(rèn)為“機(jī)制”不是某種具體方法,而是一種抽象概念,故而認(rèn)為上述兩位學(xué)者的傳承機(jī)制也只是傳承方式,進(jìn)而提出了“選擇機(jī)制、適應(yīng)機(jī)制、采借機(jī)制和參與機(jī)制”四種文化傳承機(jī)制。由于現(xiàn)代化帶來生產(chǎn)生活的重大轉(zhuǎn)型,少數(shù)民族文化傳承發(fā)生了重大變遷,其中最根本的是傳承機(jī)制的轉(zhuǎn)變,即由過去的族內(nèi)傳承擴(kuò)大到族外傳承、對政府力量的依賴日益加強(qiáng)、以現(xiàn)代生產(chǎn)轉(zhuǎn)型的重構(gòu)來實(shí)現(xiàn)文化傳承。鄭國華針對社會轉(zhuǎn)型導(dǎo)致的民族傳統(tǒng)文化傳承失范的危機(jī),提出了“規(guī)范創(chuàng)新”傳承理論,以重塑文化傳承規(guī)則,即“通過意義轉(zhuǎn)接,確立新的價(jià)值認(rèn)同;規(guī)范組織行為,重構(gòu)組織體系;突出民族特色,保存核心形式;選擇合理目標(biāo),防止利用失范。”劉堅(jiān)基于云南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研究,提出了四種普適性的傳統(tǒng)體育傳承路徑,即“現(xiàn)代體育化、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申報(bào)、資料庫與信息庫和生活性保護(hù)(生態(tài)保護(hù)區(qū)與生態(tài)旅游)。”盧德生、井祥貴提出了教育傳承機(jī)制:一是建構(gòu)“研-發(fā)-教”一體化的學(xué)校教育傳統(tǒng)體系;二是建構(gòu)社會教育運(yùn)行機(jī)制,即“以實(shí)現(xiàn)民族成員終極價(jià)值為目的的、特定環(huán)境中的民族獨(dú)享文化傳承機(jī)制”。容中逵則認(rèn)為家庭、學(xué)校、大眾傳媒三個(gè)領(lǐng)域可以分別以行為系統(tǒng)、智識系統(tǒng)、價(jià)值取向系統(tǒng)為側(cè)重來踐行文化傳承的使命。
4.民族文化傳承的實(shí)踐體系建構(gòu)
民族文化傳承是一個(gè)復(fù)雜系統(tǒng),任何一個(gè)變量的單一優(yōu)化都不能解決文化傳承問題。隨著文化傳承的單一要素專題探討和綜合研究的逐步深入,文化傳統(tǒng)體系建構(gòu)研究日益受到關(guān)注。近年來,已有部分學(xué)者就建構(gòu)中華優(yōu)秀傳承文化傳承體系進(jìn)行了專題研究,它既是一種文化傳承理論的學(xué)術(shù)探索,也是一種文化傳承機(jī)制的新嘗試。
段超、郭繼承、王征國、柯可、黃韞宏等學(xué)者都對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體系進(jìn)行研究,歸納他們的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gè)方面:一是中華優(yōu)秀傳承文化傳承體系的內(nèi)涵,即中華優(yōu)秀文化傳承體系是一個(gè)層級分明、和諧互動、傳承久遠(yuǎn)的有機(jī)體系,是由物質(zhì)文化(塔基)、制度文化(塔身)、精神文化(塔頂)、理想文化(塔尖)構(gòu)成的“人類文化金字塔”的層級結(jié)構(gòu)模式的中國化;二是構(gòu)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體系的重要性,即只有它的有效運(yùn)行才能確保文化從個(gè)案到整體的有效傳承;三是如何建構(gòu)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體系,這是近二三年來文化傳承研究的重點(diǎn),提出了四種建構(gòu)方法;(1)運(yùn)用系統(tǒng)論、控制論來統(tǒng)籌建構(gòu)文化傳承體系,具體從傳承主體、傳承方式、文化本體、保障措施等層面來建設(shè);(2)以人為本,以確立中華人格理想為目標(biāo),建構(gòu)以國學(xué)為基礎(chǔ),以國魂為精神,以國法、國藝、國教、國俗、國技為修身、規(guī)范、教化和傳播手段的中華文化傳承體系;(3)遵照優(yōu)秀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為統(tǒng)領(lǐng)的原則,找出傳承方式,從而全面解決文化傳承中“傳承什么”和“如何傳承”的兩大根本問題;(4)運(yùn)用科學(xué)技術(shù)建構(gòu)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體系,即利用科技產(chǎn)品使文化典籍、文物遺產(chǎn)數(shù)字化,讓數(shù)字化產(chǎn)品成為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傳承載體;利用科技平臺展現(xiàn)傳統(tǒng)文化形象,發(fā)揮國民教育的基礎(chǔ)作用和展覽平臺的實(shí)際效果;利用科技媒介實(shí)現(xiàn)宣傳手段多樣化,讓傳統(tǒng)民風(fēng)民俗走向社會、融入生活;利用科技手段挖掘傳統(tǒng)文化的科學(xué)價(jià)值,并促其創(chuàng)新,以實(shí)現(xiàn)傳統(tǒng)文化可持續(xù)發(fā)展。
二、評析
我國民族文化傳承經(jīng)歷了30余年的研究與實(shí)踐,成果豐厚,形成了較為完備的理論體系,但也存在著諸多有待完善之處。
(一)跨學(xué)科交叉研究,持續(xù)拓展了民族文化傳承的研究視野,但沒有形成嚴(yán)謹(jǐn)?shù)睦碚擉w系。文化的多樣性決定了其所涉學(xué)科的廣泛性,社會學(xué)、人類學(xué)、民族學(xué)、經(jīng)濟(jì)學(xué)、文化學(xué)、藝術(shù)學(xué)、美學(xué)、法學(xué)等學(xué)科都從不同角度切入研究,涵蓋了文化傳承的內(nèi)涵、傳承主體、傳承手段、傳承場域、保障措施等多方面的內(nèi)容,尤其在傳承主體、傳承場域、傳承機(jī)制方面取得了豐碩的學(xué)術(shù)成果。然而,跨學(xué)科的交叉研究難以形成統(tǒng)一的專業(yè)研究范式。由于研究者多來自其他學(xué)科的邊緣學(xué)者,受自身學(xué)科背景的影響,往往是某一方面的專題研究做得較深入,而各個(gè)專題研究之間缺乏緊密的關(guān)聯(lián)度,因而研究成果呈現(xiàn)雜亂無章的狀態(tài),沒有從整體上建構(gòu)一個(gè)結(jié)構(gòu)嚴(yán)謹(jǐn)?shù)木哂胁僮餍缘膫鞒畜w系。
(二)延續(xù)“經(jīng)世致用”為主導(dǎo)的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研究范式,即“強(qiáng)調(diào)關(guān)注社會現(xiàn)實(shí),勇于面對社會問題,致力于達(dá)到濟(jì)世安民的目的”,這種范式講求功利、尚實(shí)務(wù)實(shí)。雖然人們自改革開放以來日益富裕,卻不能安“富”樂道,最根本的原因源自民族傳統(tǒng)文化在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陷入了傳承困境,造成了社會歸屬感危機(jī),生活幸福感下降。面對現(xiàn)代化對傳統(tǒng)文化的負(fù)面影響,學(xué)術(shù)界進(jìn)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既喚起了全社會保護(hù)和傳承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自覺和自信,又能隨時(shí)發(fā)現(xiàn)傳統(tǒng)文化所面臨的新問題。當(dāng)然,傳承民族文化需要解決兩個(gè)最根本的問題,即“傳承什么”和“如何傳承”,實(shí)質(zhì)上是一個(gè)問題的兩個(gè)方面,即針對文化本體設(shè)計(jì)傳承機(jī)制。因此,要立足于文化本體研究,才能找出適于文化傳承的科學(xué)路徑。目前,針對文化本體的學(xué)術(shù)研究非常薄弱,沒有從文化哲學(xué)的高度來挖掘文化傳承的內(nèi)在規(guī)律和理論建構(gòu),所設(shè)計(jì)的文化傳承機(jī)制難以發(fā)揮預(yù)期的良好效果。
(三)研究方法上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田野調(diào)查缺失較嚴(yán)重。在研究范式上,沿著“現(xiàn)象關(guān)注一問題分析一對策設(shè)計(jì)”的邏輯展開,有利于發(fā)現(xiàn)問題和解決問題,對于傳統(tǒng)文化的保護(hù)、傳承和開發(fā)起到了較好的引導(dǎo)和促進(jìn)作用。通過定性研究,對民族文化傳承的內(nèi)涵、特征及主要內(nèi)容等進(jìn)行了翔實(shí)的描述,累積了一定的理論基礎(chǔ)。當(dāng)然,做好定性分析的前提是進(jìn)行科學(xué)的定量研究,并深入田野進(jìn)行長期、細(xì)致的調(diào)查,這也是民族傳統(tǒng)文化鄉(xiāng)土性所決定的,而這些恰恰是文化傳承領(lǐng)域?qū)W術(shù)研究的不足之處。很多學(xué)者的田野工作是“短平快”,導(dǎo)致收集的第一手資料不夠翔實(shí),又缺乏真實(shí)性,所做的定量分析不充分;部分學(xué)者甚至只在書齋中進(jìn)行文獻(xiàn)整理和挖掘,欠缺定量分析。如此一來,定性研究所得出的結(jié)論難免帶有主觀隨意性,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日益嚴(yán)重的民族文化傳承難題。
三、展望
30余年的研究涉及了文化傳承的方方面面,取得了豐碩的學(xué)術(shù)成果。不過,國內(nèi)的民族文化傳承研究側(cè)重于微觀的專題探討,沒有立足于文化本體及其發(fā)展規(guī)律來進(jìn)行歷時(shí)性的深度研究,缺乏理論原創(chuàng),對國外的文化傳承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的研究與借鑒也不夠,這與我國豐厚的民族傳統(tǒng)文化資源是不相匹配的。因此,今后的民族文化傳承研究需要嘗試如下努力。
(一)拓展研究領(lǐng)域,關(guān)注民族文化的教育傳承。人是文化的創(chuàng)造者、持有者,人的素質(zhì)高低直接影響到文化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只有實(shí)現(xiàn)“人的發(fā)展”才能從根本上實(shí)現(xiàn)民族文化的有效傳承。文化傳承實(shí)質(zhì)上是作為文化主體的人對民族文化的選擇性繼承和合理創(chuàng)新,也就是培養(yǎng)人們對文化的判斷、選擇和創(chuàng)新的能力,以淘汰落后文化、繼承并發(fā)展優(yōu)秀文化,而教育是培養(yǎng)人的能力的重要手段。因此,我們應(yīng)當(dāng)將民族文化傳承研究視野拓展到教育領(lǐng)域,既要探討民族文化教育傳承機(jī)制,又要研究“人的發(fā)展”的教育哲學(xué),通過教育實(shí)現(xiàn)“人的發(fā)展”來解決文化傳承的根本問題。
(二)轉(zhuǎn)變研究范式,關(guān)注民族文化的整體性研究。過去的文化傳承研究要么側(cè)重于某一文化事象的個(gè)案討論,即單個(gè)、局部的田野調(diào)查式研究;要么脫離文化本體,就文化生態(tài)、傳承方式、傳承主體等文化外部傳承條件進(jìn)行研究。然而,民族文化是復(fù)雜多樣又交叉共生的,難以對其進(jìn)行準(zhǔn)確的切割分類,這就顯示了既往研究范式的局限性。不過,民族文化有諸如家庭、村落、市場、學(xué)校、節(jié)日等眾多生存空間,每個(gè)文化空間都有一個(gè)讓人感知的模糊邊界,每個(gè)空間中生存的文化的種類和形態(tài)也不盡相同。因此,以文化空間為研究單位,立足于文化本體,來探討不同文化空間中的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及其運(yùn)行規(guī)律,揭示其中的文化傳承實(shí)踐邏輯,設(shè)計(jì)文化傳承機(jī)制。這就避免了文化本體在外力影響下發(fā)生存在空間置換后而陷入無所適從的生存困境,保證了文化本體在新的文化空間內(nèi)部運(yùn)行機(jī)制作用下得以傳承。如此一來,我們可以一個(gè)個(gè)文化空間為變量,來建構(gòu)民族文化傳承體系。
(三)學(xué)術(shù)研究與社會實(shí)踐相統(tǒng)一。一方面,文化研究者要務(wù)實(shí)做好田野調(diào)查工作,即選擇合適的具有代表性的田野點(diǎn),分別從客位、主位的視角,進(jìn)行長期的觀察、訪談、實(shí)驗(yàn),發(fā)現(xiàn)民族文化生存的深層危機(jī),在全面掌握第一手資料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學(xué)術(shù)研究。另一方面,與學(xué)術(shù)研究相呼應(yīng),強(qiáng)化文化傳承的社會實(shí)踐工作,也就是說對學(xué)術(shù)研究成果進(jìn)行實(shí)踐證明試驗(yàn)。田豐、尹紹亭、陳哲等學(xué)者曾經(jīng)做了諸如民族文化村、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區(qū)等個(gè)案的實(shí)證研究,可以說是文化傳承實(shí)踐活動的成功嘗試,擴(kuò)大實(shí)證研究是今后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另外,吸引相關(guān)的社會企業(yè)投入這方面的研究,這是實(shí)現(xiàn)民族文化生產(chǎn)性傳承的有效途徑之一。如此一來,通過“積極創(chuàng)設(shè)‘研究在實(shí)踐中、‘實(shí)踐在研究中的情境,打破傳統(tǒng)民族學(xué)研究中欲保持‘他者的原生性僅關(guān)注‘找事與‘說事而對‘做事有意無意回避的現(xiàn)象。”
[責(zé)任編輯: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