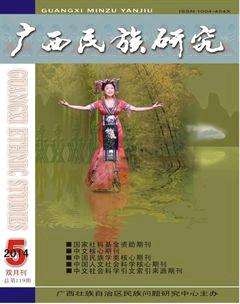本土化的理論創新與現實的社會關懷:中國民族生態學研究的兩個基本取向
管彥波
在歐美,民族生態學作為一門兼跨民族學、生態學、植物學等學科領域的交叉學科,它已有100多年的發展歷史。在中國,自20世紀初以來,隨著西方人類學相關理論被譯介過來,并與中國民族學的學科發展相結合,已有不少學人開始采借域外民族生態學的相關理論致力于中國民族地區的生態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中國的民族生態學這門學科也正處于快速發展之中。
但如果我們對百余年來學界對中國民族地區生態研究實踐進行梳理,依然會發現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一是民族學、地理學、生態學等相關學科的研究明顯有自己不同的取向,民族學長期關注的民族傳統社會中的生態智慧與生態知識,重于具有民族元素的生態價值的揭示,更多地呈現族群的生態文化;而地理學或生態學重點在于某個區域范圍內自然地理環境要素彼此關聯性的分析,對于區域內人群活動與地理環境的互動關系關注不夠。這是學科研究傳統使然。如何超越學科限閾,打破學科壁壘,開展既見地又見人或者人地互見的研究,可能是將來中國民族生態學研究中應該追尋的一個方向。二是本土化的理論創新和如何更好地服務于國家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中國的民族地區是自然資源比較富集的地區,也是重要的生態功能區和生態環境十分脆弱的地區。自實施西部大開發以來,國家一直倡導和始終堅持資源開發與生態治理并舉的戰略方針,并將實現生態功能修復的退耕(牧)還林(草)、防沙固沙工程作為整個西部大開發的重點任務,投入了大量財政資金進行生態建設。可從實際效果來看,雖然局部生態得以改善,環境惡化速度相對減緩,但整體功能退化的趨勢并未得到根本遏制,民族地區在將來很長一個時期依然將面臨自然資源大規模開發與西部少數民族群眾因改善生存條件、提高生活水平而對脆弱生態環境破壞加劇的雙重壓力。在民族地區生態系統對經濟社會發展承載能力不斷減弱,經濟發展與生態建設兩難抉擇的背景下,大力加強民族地區生態文明建設,不僅關系到該地區的可持續發展,而且關系到整個中國的生態安全和永續發展。
翻檢近幾年民族生態研究的相關成果,我們欣然發現,已有不少學人對上述兩個問題進行了反思,并在各自的研究實踐中有所呈現,其中廣華博士就是我認識的學人中做得甚為出色的一位。最早結識廣華緣于2012年參加他的博士論文答辯。他的博士論文從環境人類學的視角,考察了一個南嶺山村——龍脊古壯寨生態退化與重建的歷史進程,為我們詳細地解析了中國鄉村生態“修復”的一個典型案例。答辯過程中,他給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其對生態人類學理論的熟識與濃濃的現實關懷,這正是我們從事民族生態學研究所追尋的兩個基本目標。后來,博士論文以《生態重建的文化邏輯:基于龍脊古壯寨的環境人類學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3年)為名出版了,當我讀到這部著作的時候,本就想寫篇文章,向學界推介,可就在我尚未成文之際,又讀到了廣華博士新著《壯族地區生態文明建設研究——基于民族生態學的視角》(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39萬字)。較之于博士論文,這是一部更為宏闊的對壯族地區生態文明建設及其面臨的挑戰進行系統研究的厚重翔實之作。
廣華博士是較早關注并對壯族地區的生態文化進行研究的青年學者之一。自2007年,他刊發《關于開展壯學生態研究的設想》(《廣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以來,圍繞著民族生態學和壯族地區生態文明建設的主題,幾乎每年都能夠讀到其相關的研究論文。學術著作的推出,一般是在長期積累和專題研究的基礎上,總結匯聚的結果。正是秉承多年的學術積累和對同一主題的研究,廣華博士呈現給我們的確實是一部理論與實證研究結合甚佳的上乘之作。我們先談該書的理論與寫作特色。
學術研究并不是一開始就要建立多么宏大的理論體系,而踏實可行的研究大多是在一定學科發展基礎上展開的,在學理上注重的是對過往理論和相關研究成果的全面了解與洞察。該著作在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方面,緊扣“生態文明”這個核心概念,對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進行了簡單的回溯,然后圍繞著“區域生態研究總論”、“循環經濟研究”、“區域生態修復研究”、“區域環境保護研究”、“生態文明城市研究”等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進行了全面的評述,同時關注了壯族地區的生態研究和壯學的生態研究兩個大的領域。在研究的理論準備與路徑選擇方面,如同該書的副標題所昭示的那樣,作者的研究是基于民族生態學的視角。那么,何謂民族生態學呢?國外尤其是美國民族生態學所具備的學科特征又如何呢?民族生態學在中國的發展歷程以及中國學者的研究重點在什么地方呢?作者基于對中西方民族生態學的界定、理論預設以及學科特征的歸納與梳理,并且與誕生于蘇聯的另一種民族生態學進行了學術淵源、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比較分析,再結合本土民族生態學的實踐,提出了旨在指導其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即在堅持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基本范疇的基礎上,吸收、借鑒來自蘇聯/俄羅斯的民族生態學傳統,注重宏觀、中觀、微觀和點、線、面的結合,以民族志田野調查方法為主,輔之以文獻研究和個案分析,開展壯族地區生態文明建設的研究。
找尋到開展研究的理論分析方法,如何把相關理論貫穿到具體的研究實踐中是一個頗費思量的過程。該著作在謀篇布局和核心內容的呈現中,采取的是“總一分一總”的寫法,即先概括性地引出研究主題,再從民族生態學的視角對典型案例進行深度的分析,最后總結、深化研究主題。這種頗具邏輯環鏈的寫作思路在著作的核心章節即第三、四、五章貫徹得尤為徹底。
各民族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世代積累并傳承下來的有關生存環境的知識和體系,即傳統生態知識是近年來民族生態學關注的一個焦點。在社會轉型、經濟轉軌的當下,考察壯族地區的生態文明建設的實踐,壯族鄉土社會中傳承下來的生態知識是必須充分關注的一筆“文化遺產”。對此內容,作者安排了“傳統生態知識與壯族地區生態文明建設”的專章來討論。在展開討論的過程中,作者先是就“傳統生態知識”的概念、構成、實踐效應進行了充分的討論,從情境性、適應性、族群性、口承性、經驗性、實踐性、分享性、破碎性等8個方面高度概括了傳統生態知識的特點,并分門別類對壯族傳統文化中蘊含的生態知識予以挖掘和梳理。最后揭示了壯族傳統生態知識對生態文明建設的獨特價值:壯族傳統生態知識包含了有效的技術、包括了許多保護生態環境的規約和習俗、蘊含著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思想,分別有利于從物質、制度和精神層面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文明。所以,只有珍惜、繼承和發展壯族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文明因素,才能更好地促進壯族地區的生態文明建設。
相對于傳統的生態知識,在現代性理念支配下的一切科技思想、知識和技藝,亦即現代科學技術,因其具有較強的普適性,常被作為人類社會生產實踐活動的組成部分,參與到區域社會的資源開發、環境改造和生態文明建設中。近幾十年來,隨著壯族地區現代化步伐的加快,資源開發力度的加強,一些現代科學技術在政界、商界和農業科技界的推動下,被引入壯族地區,壯族社會普遍經歷了“綠色革命”的“洗禮”:雜交水稻、玉米大面積推廣;化肥、農藥大量使用;農業機械化進程正在加速;傳統作物品種和生產技術快速消逝,等等。可以說,對于以農耕為主的壯族社會而言,“綠色革命”在現代農業科技中有著非常集中的體現,它既給壯族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帶來了極大的改變,也隱含了一些潛在的生態災變因素。同時,在壯族地區的社會生活實踐中,諸如沼氣的廣泛推廣與使用,在取得良好的經濟效應、社會效益的同時,也給鄉村生態文明建設帶來了一些積極的影響。針對現代科學技術對壯族地區生態文明建設的雙重效用,作者以典型個案材料為主,通過頗具學理性的分析后指出:一方面,作為“現代全球科學”,現代科學技術在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時具備一定的優勢,可以在壯族地區的生態文明建設中發揮推動作用。另一方面,作為外源性知識,現代科學技術具有不服水土性,如果運用不當,很容易產生生態災變,給壯族地區生態文明建設帶來消極影響。所以,在壯族地區生態文明建設的過程中,我們既要充分發揮現代科學技術的推動效用,又要時刻警惕現代科學技術移植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不要試圖夸大現代科學技術的實踐效力,把現代科學技術置于適當的位置,方是正確的抉擇。
如同其他大多數民族地區一樣,目前廣大的壯族地區正面臨著經濟發展、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的多重壓力,如何保持生態環境與經濟社會的良性互動,協調好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關系,是一個關乎可持續發展的大問題。在生態文明建設場景下壯族地區的環境保護問題作為該書的一個核心章節之一,作者首先從民族生態學的視角,透視了環境保護的多重面相,指出環境保護作為在現代性場景下應對環境惡果的一種策略,作為反思現代化工業文明的一種文化理念,只有在充分考慮目標地區和目標群體的需要和愿望的情況下,才可能實現其預期的目標。接著通過對兩個典型的環境沖突案例的深度剖析,對壯族地區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因環境保護而引發的環境沖突、環境保護與生態文明建設的互動關系等論題提出了其獨到的見解:壯族地區生態文明建設必然地要求環境保護,環境保護是壯族地區生態文明建設的根本性措施之一;生態環境與整個現代政治經濟體系密切相關,壯族地區環境保護只有在生態文明建設時代才可能得到最大的體現;因環境保護而產生的環境沖突并不必然阻礙壯族地區的生態文明建設,甚至可能會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圍繞著傳統生態知識、現代科學技術、環境保護與環境沖突等三個主要的命題,作者在壯族地區生態文明建設歷史場景中,全面檢視了西方起源的民族生態學理論框架的有效性,向從事生態文明研究的學者發出了來自民族學人類學界的聲音。這種聲音立足田野、立足實證、立足于典型個案的深度調研。在該書所呈現的諸多個案中,我們看到:
——石疊屯是一個300多人的壯族村寨,該村寨所屬的區域在20世紀50年代末的“大煉鋼鐵”運動中,大量森林植被被砍伐,山成了“光頭山”,石疊屯周邊石山林立,石漠化嚴重,但經過幾十年的治理,村寨所在的石山生態系統恢復了良性循環。在石疊屯治理石漠化的過程中,當地壯民傳統中所擁有的生態知識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因梯田而聞名的龍脊壯寨,在20世紀80~90年代曾發生嚴重的干旱災害,人畜飲水困難。在應對氣候災變的過程中,當地壯族民眾所采取的復合型取食策略、獨特的水資源管理方法和鄉規民約對村寨環境的保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地傳統生態知識應對氣候變化的獨特價值。
——位于武鳴縣南部的下淥壯寨,在推廣沼氣以前,主要以柴草為主要能源,村后的山林被砍伐得所剩無幾,農民燒柴要到很遠的地方去砍。自2000年參與到“沼氣生態家園建設”以來,該村周邊的生態環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以下淥村等村寨為代表的壯族鄉村的沼氣推廣,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農村生活和生產用能,走的是一條從“資源一產品一廢棄物”的單向線性過程的傳統模式向“資源一產品一廢棄物一再生資源”的閉環反饋式循環過程的循環經濟模式。
——德保縣敬德鎮上平屯的“郎卡瑪”石山,作為現存種子植物中最原始的一個類群——蘇鐵的最早發現地,作者通過深入的調查走訪,圍繞蘇鐵的被發現、保護與當地居民生存發展之間的博弈過程,為我們呈現了一個外部世界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努力與當地社區民眾利益訴求之間的矛盾關系的極好個案,進而反思德保蘇鐵保護本身所具有的深刻的全球政治內涵。
——靖西縣新甲鄉凌晚屯鋁土礦開發與環境沖突案例——靖西“7·11”事件前因后果的深入訪談,作者認為正是“政經一體化”所引發的“污染保護主義”才是導致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事件的直接結果是留下了永遠難以解決的土地和水資源污染問題,當地鄉村民眾失去了祖輩賴以生存的家園,最終淪為鄉村貧民或城市中的產業工人。
如上這些鮮活的典型的個案分析,使行文避免了龐雜瑣碎的現象羅列和空泛的議論,使問題的分析直接面對具體的人群和區域,從而使該書立體、飽滿,更具層次感、鄉土性和學術性。
通讀全書,我們還要加以特別指出的是,作者濃濃的鄉土情懷和現實關切。
民族生態學本來就是一門與民眾生活休戚相關的學科,它關注民生、關注民族地區的生態環境、關注民族地區未來的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民族學者,廣華博士長期在壯族地區調研,與基層百姓有多層面的接觸與交流,他關于壯族地區生態文明建設的研究是接地氣的,譬如他在分析壯族地區環境保護如何實現預期目標所指出的那樣,地方民眾關注的是生存和發展的問題,任何在理論上可行的環境保護策略要取得成功,必須關注目標地區人們生活的需要和愿望,必須考慮地方民眾的習俗、規約和價值,只有廣大民眾的積極參與,方能達成對環境的有效保護。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的工作者,廣華博士的研究具有很強的時代性和現實性,他在對壯族地區生態文明建設進行深入考察后,還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總結凝煉出如下幾點對策建議:
一、要摒棄“人類中心主義”的錯誤觀念,堅持可持續發展理念,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思想,從思想意識上推動生態文明建設;
二、要把壯族地區生態文明建設置于整個經濟社會發展大局中考察,深刻認識到其重要性和嚴峻性,切實全面推動生產方式的轉型和生活方式更新;
三、要深刻把握壯族地區生態文明建設的區域性、民族性特征,充分發掘、利用壯族傳統生態知識,推動壯族生態文明示范區建設;
四、要正視現代科學技術對生態文明建設的雙重效用,既要積極發揮其積極作用,又要盡可能地降低其消極影響;
五、要非常重視制度體系建設,加快建立生態補償制度,同時賦予環保部門以更大的權力,加大對環境污染的懲罰力度;
六、要提倡社區基礎的環境保護,強調社區民眾的參與,既要保持好生物多樣性,又能夠實現社區的可持續發展;
七、要加強區域環境管制,切實保障區域民眾的環境權益,減少環境沖突事件的發生。
這些針對壯族地區生態文明建設而提出的頗具學理分析的對策建議,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可能對其他民族地區的生態文明建設亦不無啟發和借鑒意義。
總之,生態文明建設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它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存在著多向的互動關系。我們期待著廣華博士在此研究的基礎上,不斷求索創新,就其下一個目標——“嶺南民族傳統生態知識與生態文明建設互動關系研究”,取得更為豐碩的成果。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資源環境與生態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袁麗紅]